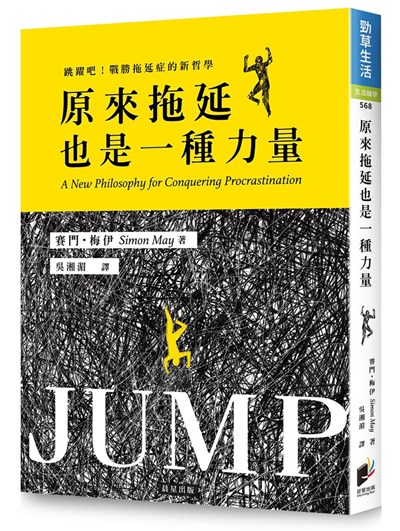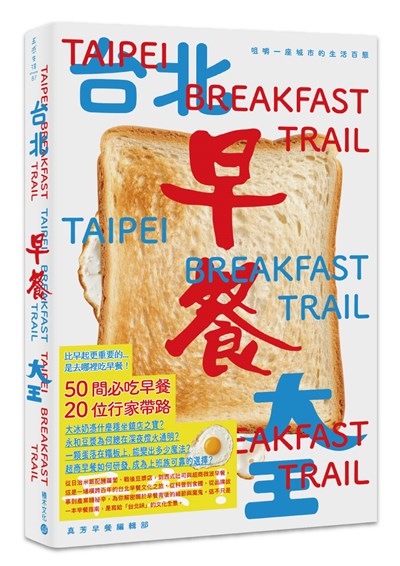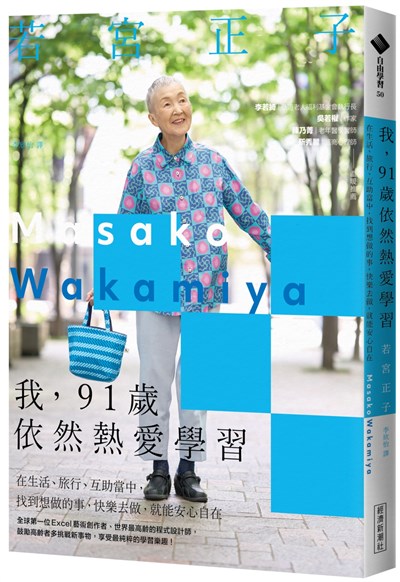台灣城鄉聚落呈現的公共藝術,經由旅人視野,可看見島嶼上每一個動人故事,例如在重洋外思念故鄉台灣的日本人、透過一株稻穗復育文化靈魂的阿美族女子、因為柳丁重新體會土地意涵的農村子弟等。且讓美學帶路,不同角落的情感記憶,將重組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認同,更看到藝術蘊含的生命與文化無限寬廣。
文章節錄
《島嶼行旅:跟著公共藝術.旅行》
郵寄,一段破碎的移民夢
曾經存在於東海岸上的漁村
「鳥踏石仔村」為花蓮港尚未開闢前的老地名,當時,這處花蓮當地人也稱為「東岸街」的聚落。在文獻與耆老的記憶中,源於一百多年前的入墾者,搭著小船行經到此時,看見了一塊有許多海鳥群集的大礁石,而稱此地為「鳥踏石仔」。隨著到此以捕魚維生的居民增多,逐漸形成了一處小漁村聚落,而稱為「鳥踏石仔村」;花蓮溪在此匯入太平洋,海岸與沼澤等自然景觀,均成為了昔日這座村落的環境記憶。日治時期,日人大力開發花蓮,「鳥踏石仔」也在這段建設工程中成為「洄瀾港」,也就是日後的花蓮港的一部份。
「鳥踏石仔村」岸邊有座建於1939年的白燈塔,在老一輩人印象中,那是一座高約十三公尺多的白色圓柱型燈塔,長年以來均是當地漁船入港的重要導引。約於1940年,築港所需大量人力與資源,除日本及琉球人相繼投入外,也陸續吸引了當地的噶瑪蘭族人、宜蘭龜山島的村民,甚至高雄屏東等各地人們集聚於此,不同的族群文化、生活習性及漁業技術,成為鳥踏石仔村多元多樣的地方文化特色。
1979年,政府推展花蓮港第四期拓港工程,「鳥踏石仔」漁村海灘被列為禁區,全村被迫面臨搬遷的命運,在以國家建設為前提的時代價值下,村民無力抵抗既定政策,只能不捨地搬離家園,自此,「鳥踏石仔村」成為了歷史名詞。隨著建設的腳步,隔年,白燈塔在引爆炸藥後,永久消逝於海岸地景上;「當時引爆時,初夏時節的鳥踏石仔海灘,還有許多在此戲水的人,漁民們也如日常般地忙碌於漁業,剎那間,在眾目睽睽下,這座與當地人相處了四十年的白燈塔,「就這樣突然消逝了!」許多老花蓮人每每想起當時的那幕景象,依舊紅著眼眶深感不捨。
藝術裡所述說的老花蓮故事
在缺乏客運,貨運量也逐漸降低的趨勢下,許多港邊的設施逐漸閒置,位於花蓮漁港邊一處閒置多年的1-1倉庫,在藝文與講求舊建築活化的政策推動下,號召藝文團體進駐,計劃轉換為一處城市裡的藝文空間。然而,數年間,一個個懷抱著夢想的單位陸續進駐,又因港區的管制與地點的偏僻而默默地離去。長期在花蓮港經營維納斯藝廊的林滿津,在遷到港區之前,原本在市區租了一棟三層樓的空間,交通便捷,也讓訪客絡繹不絕,然而,一份想追求寧靜的心情,讓她決定由市區搬到這處邊陲地帶的港邊,目前,也是港區藝術空間中少數堅持留下的藝廊經營者。
看見港邊藝文特區的沒落,她計劃了一段以「驛站‧藝讚─花蓮港」為題的藝術介入空間計劃,期能透過一群藝術家、當地村民與孩子們的集體參與,來回顧與講述出關於「鳥踏石仔村」與「洄瀾港」的老故事。倉庫外側牆面上,約有9米高寬約31米的「山海迴旋-白燈塔印記」大型壁畫,當地藝術家以老照片與老人口中的故事為基礎,以馬賽克為素材,帶領孩子們一起完成創作,將老花蓮人印象中的「鳥踏石仔村」勾勒出來。壁畫裡講述著早期的花蓮車站與蒸汽火車的時代;也透過日出、海鳥及白燈塔等老花蓮的環境元素,回味著昔日「鳥踏石」地名時期的生活記憶。另一處結合藝術家牟善珺的紙雕、馮祥生的雕刻工藝及書法家李秀華的書法,以蛇紋石為素材,跨領域地共同創作出一座高約3公尺的「幸福青鳥郵筒」,在港邊締造出一個新的場所意象。這座可以讓旅人投遞信件的藝術郵筒,上方有隻傳說中「東方最喜樂的鳥」,名為「東僖」的青鳥,透過信件的收送,穿梭於天涯海角,為許多人們傳遞著幸福的訊息。
一段談著花蓮老城市記憶的壁畫、一個講著傳遞情感的藝術郵筒,其實勾起的並不僅是在地花蓮人的往事,更蘊藏著更多屬於日本人的生命故事。
隨著情感的訊息,回溯到「移民村」的年代
「移民村」源於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當時,為解決日本內地農村人口的生活經濟及社會問題,日本政府積極鼓勵日本農民移往台灣花蓮定居生產。初期,零星的移民,並未形成以日人為主的大型生活聚落。直到1899年,日本政府由賀田組主導大型的移民村計劃,協助首批來自北海道及四國的移民移墾花東平原,並從事農業實驗計劃,做為前進南洋的軍事後勤資源預備。1909年後「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更大規模的「移民村」計劃,陸續將花蓮區域的無主地收編國有,以「造鎮計劃」的方式,完成了堤防、水圳、學校、醫療院所等公共設施,沿著花東縱谷開闢出多處移民聚落,並引進約一千七百多人的移民,而形成當今的花蓮諸多鄉鎮。
1909年在「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的移民政策下,於花蓮設置荳蘭社移民指導所,「吉野村」(今「吉安鄉」)也成為首座官營移民村。初期,約有六十一戶日本移民到此開墾,其中約有五十戶來自日本德島、北海道、新潟、秋田與千葉等地的移民,四年後,這座移民村的規模已達數百戶。在資源大量投入後,日本政府開始在境內推廣台灣的美麗環境與豐富物產,大力地宣傳移民政策,更提供免費之交通運輸、配給土地與房屋,來鼓勵在日本境內沒有自己的土地、生活趨貧的農民到此開墾。隨著移民人數擴增,原本以公營為主的移民機制也陸續轉為私營,並繼續往南向東部平原擴展。當時舉家搬遷的許多日籍居民,多是變賣家產而到此開墾,其經濟條件並不比在地村民寬裕。發展至1932年,在東部地區的村落陸續形成後,「台灣總督府」也曾擴展到西部平原,於濁水溪、虎尾溪及高屏溪等河床區域大規模開闢「移民村」。
當時擁有豐富社經地位的日本移民,多選擇居住在商業熱絡且較具現代生活的都會城市,而定居於偏鄉聚落的日人,相較於本地居民,僅是在移民政策下,多了政府配給的小塊土地可以耕作、一小棟可以安居的房舍,但與台灣人一樣,都同樣過著辛苦的農耕歲月。移民到花蓮的日籍居民,更陸續遭遇風災、瘟疫等災難,在水土不服與環境衛生條件過差的景況下,客死他鄉的情形時有所聞;而得以存活下來的人,也逐漸在此娶妻生子,安穩地生活了下來。只是,這段大規模以台灣為基地的移民村計劃,隨著二次大戰而終止;1945年,戰後遭遣返的日本移民已高達數萬人之多。在許多艱難的日子中,日本移民與台灣人都是一起走過,也因此,當年在「洄瀾港」邊,一群群待遣返的日人,交雜著原民與漢族居民的人潮,彼此哭泣相擁著,在此起彼落的互道珍重聲中告別,只是這一別,可能就是三、四十年…甚至便是永別;至今,花蓮的移民村裡,還流傳著許多台灣人昔日與日籍居民的動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