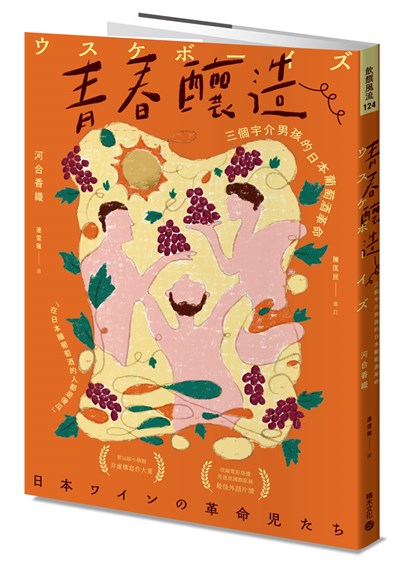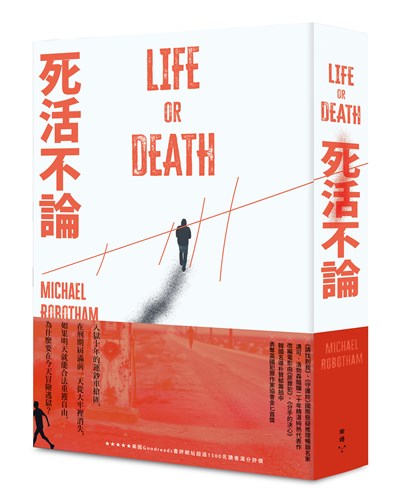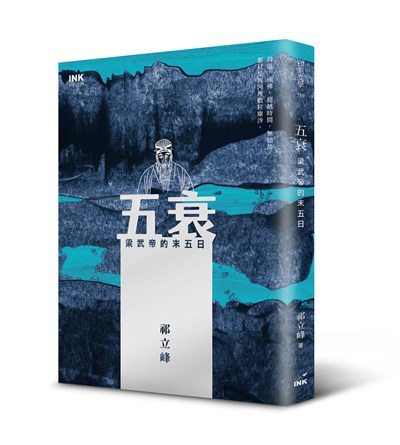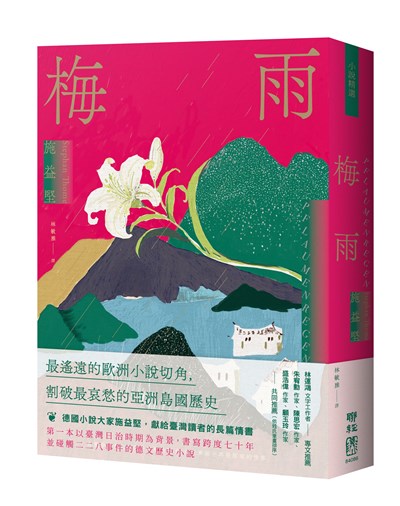光是收拾行李箱,旅行就已經展開:到機場看見返鄉的外國旅客,開始想像自己置身異國──「旅行」是具體的外在行為,然而旅途上湧起的感懷來自當下,也可能追憶往昔,甚至改變了未來的人生。吉田修一兼具寂寞與溫暖的現代感寫作視角,最能闡述此番「旅行的意義」。
文章節錄
《天空的冒險》
台北.台灣
我想有不少人會在旅途中享受閱讀之樂,但是在旅遊異地觀看電影的人,我倒是沒碰過幾個。
因為我經常去旅行的地方看電影。
「你幹嘛特地跑去國外看電影啊?」
「不會聽不懂台詞嗎?」
每次只要說出我的這個興趣,就會招來這般抨擊。
事實上也是,難得花時間花錢去到國外,別看什麼電影,多逛點名勝古蹟應該比較對,而且比方說在台灣看法國電影,即使法語對白附上中文字幕,也像是拿到青江菜跟豆瓣醬,被吩咐「喏,用這些材料做法國料理」,教人混亂。
所以在國外挑選電影時,為了減少混亂,我總是盡可能看該國的電影,不過英語圈姑且不論(我還具備義務教育程度的英語能力),其他國家的話,當然就只能茫茫然不知所以然地看著銀幕。
盯著完全聽不懂在講什麼、演什麼的電影整整兩小時,不無聊嗎?若是這麼問,老實說,我只能歪頭回答:「微妙。」不過譬如說,在巴黎雅致的小巷散步時,如果看到同樣雅致的小電影院,我還是會忍不住晃進去。
當然,即使不是巴黎的精緻電影院,洛杉磯的巨大影城也行,台北的懷舊戲院也可以。總之,在旅行目的地的國家看上一部電影,會讓我感覺奢侈極了。
而且即使看的電影內容教人一頭霧水,還是可以接觸到該國的獨特氛圍。
比如說,有一次我一時興起,走進曼谷的電影院,電影播放前就和日本一樣,會先播放下一檔的預告片。我吃著電影院賣的爆米花,看著一樣聽不懂在說什麼的泰國電影預告。幾部電影預告結束後,出現了類似新聞畫面的影像。
「咦,現在電影院裡還會播新聞啊?」我悠哉地看著,沒想到人還滿多的場內觀眾紛紛站了起來。
「咦?出了什麼事?」
一瞬間我還以為電影播完了。可是電影豈止是沒完,根本就還沒開始播。留意到時,所有的觀眾都起立,盯著銀幕看。入境隨俗,雖然搞不懂是怎麼回事,但我也放下爆米花,急忙站起來。
下一瞬間,銀幕上出現泰國國王的肖像照。接著莊嚴的音樂響徹電影院,不曉得是不是國歌?
國王的照片播放了幾秒鐘,消失之後,觀眾又若無其事地坐下。我也不好一個人傻愣愣地站著,也慌忙坐了下來。
後來我問泰國朋友,簡而言之好像真是我猜的那麼一回事。我知道泰國國王很受國民愛戴,所以聽到原來是向國王致敬,也只覺得:原來如此。
對了,我在不丹也看了電影。
我想去過不丹的人很少,在不丹的電影院看過不丹電影的日本人應該更難得一見。
附帶一提,當時上映的是一部動人的家庭電影,描寫一對和母親過著清貧生活的年幼兄弟。前半場面滑稽逗趣,有一次弟弟的民族服裝「幗」不見了,可是上學的時候一定得穿著幗去才行。兄弟倆絞盡腦汁想辦法,最後上午哥哥穿自己的幗去上課,然後中午跑回家,下午讓弟弟穿哥哥的(鬆垮垮的)幗去上課。
當然,我完全聽不懂台詞,不過大概是這樣的故事。
不丹的觀眾非常會笑,碰到悲傷的場面,也哭得非常入戲。事實上,雖然聽不懂台詞,但最後我也跟著淚眼盈眶了,那應該是一部很棒的電影。
我也在巴黎的電影院目擊過觀眾大吵。
片名我已經忘記了,不過那是一部緊張刺激、高潮迭起的懸疑電影。電影開始三十分鐘左右,前面的觀眾席便傳出類似爭執的聲音。因為是一對男女,我以為大概是情侶在打情罵俏,然而聲音愈來愈大了。
反正我也看不懂電影情節,便望向聲音的方向。結果竟是一個女人在講手機(!),而後面的男人探向前去制止她。
情勢將如何發展?我丟下電影,看起現實世界的真實戲碼。女人不理會男人再三告誡,就是不肯掛手機。她不僅不掛手機,還按住話筒,轉身回罵身後的男人。沒多久,其他地方傳出「吵死啦!閉嘴!」(大概)的罵聲。
比起電影,觀眾席更要緊張刺激多了。男人又抱怨,女人也不服輸地頂嘴。下一瞬間,男人不耐煩地站起來,擠過滿臉困擾的同排觀眾,走出通道。
「他不看電影囉?」
我不禁同情起男人,沒想到幾分鐘後,男人不服輸地把電影院工作人員帶來了。當然,女人一下子就被工作人員請了出去。電影根本沒人看得下去了,觀眾席還不管電影內容,響起零星掌聲。
像這樣寫出在各國電影院碰上的趣事,總覺得在旅行的時候看看電影也不壞。
機會難得,我再提一則趣事好了。
我很喜歡台灣,一年都會去上好幾回,當然偶爾也會在台灣看電影。前年的時候,我在台北看了《海角七號》。這部電影將台灣日據時代發生的日本男子和台灣女子的悲戀,與現代台灣男子和日本女子的愛情重疊在一起描寫,在台灣的票房收入似乎僅次於《鐵達尼號》。
這部電影的對白使用台語和中文,偶爾穿插日語。電影最後,台灣人與日本人在舞台上合唱〈野玫瑰〉,這個場面與四十年前的悲戀結局重疊在一起,當我看到這個場面時,淚水不住地往下流。當然我只聽得懂日語,然而卻看得淚如雨下,連自己都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