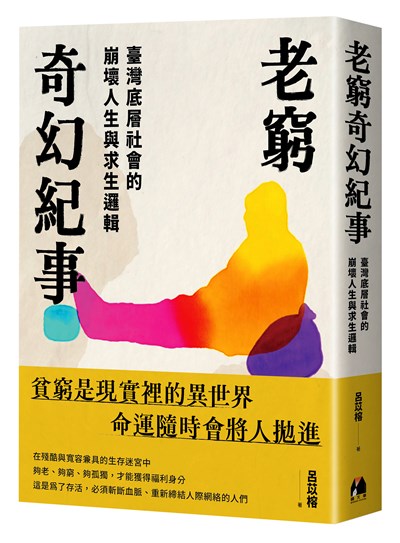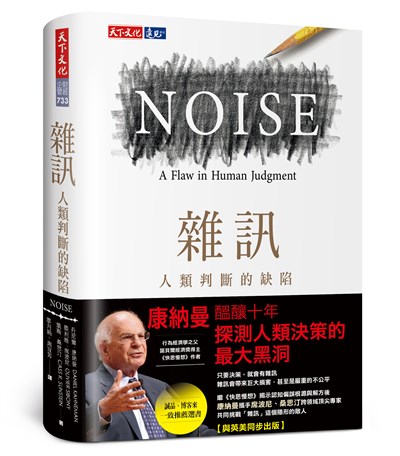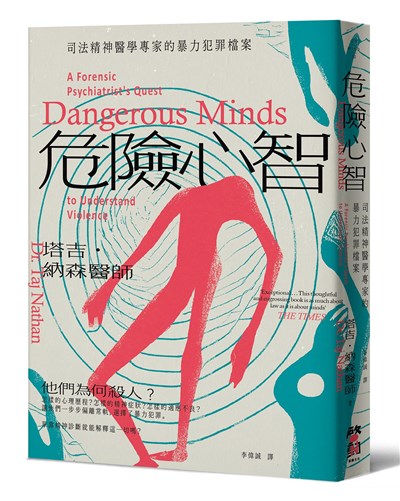作者藤原新也在東京藝術大學就讀時,決定離開校園,度過了十多年流浪歐亞各國的生活。回國之初,他驚覺日本社會有巨大改變,已不是記憶中的故鄉:社會發生一連串的冷血逆倫刑案與無差別殺人事件;人們寧可低頭使用手機分享在哪邊打卡、拍美照,卻不願抬頭聽人說話;電視螢幕比例變成16比9,各家電視台以空洞的華麗填滿畫面…他心中的那隻野狗仍透過拍照與寫作看著每一角落,他無意朝大眾狂吠,只是靜靜地記錄這一切。
文章節錄
《新版 東京漂流》
6 行善潮流
基因
失憶症患者經過繁複沉重的復健,最後恢復自我與記憶的瞬間,將陷入一種比失去記憶時更深沉的不幸,這類的案件時有所聞。
我一方面看出八○年代的人景的接點所在,另一方面也抱持著自己是否能與都市合為一體的焦慮,才會覺得自己應該一直這樣當一個旅人,保持自己的失憶狀態,對我來說甚至像種誘惑。
但在同時,我還有一種想法。
難道,失憶症這種病名,終究是為我這樣的天涯旅人而存在嗎?再怎麼仔細去想,都覺得事實並非如此。反而是我時時覺得,所有在八○年代日本都市中熙來攘往的日本人,看來都像是離失憶症患者很近的存在。
自從明治(一八六八~一九一二)維新以來,日本人在各種層面上,都逐漸喪失關於「日本」的記憶,但是如同前面所說,六○年代所謂高度經濟成長期,就是為了優先擴大生產與效率,而試圖瓦解日本的居住、土地與文化記憶的巨大能量,以及為了阻止美好過去流失而發光發熱之反抗所交織而成的時間帶。然後,巨大的能量壓倒了一切的反抗,我們來到了七○年代。
那寧靜與優雅的十年,也是日本人最後的血與記憶,如一朵剛摘下的鮮豔玫瑰花,慢慢失去色澤與香氣而凋謝一般,慢慢喪失慢慢發出腐臭。許多日本人在那十年間,為了要彌補失去記憶的痛苦,紛紛選擇了自發性服從制約下的小小幸福。
在這十年的管理社會下,如同貓咪被撫摸到熟睡般安詳的眾生相之間,以及戰後靜謐的街頭巷尾之間,都漸漸地瀰漫著一股無形巨大管理機構的制約氣息。
日本於六○年代中的改頭換面,是一個價值的過渡時期,透過層出不窮的抵抗,在我們這一代心中留下了許多印象;對我來說,在寧靜中度過的七○年代。比過去的十年對日本帶來的改變,毋寧說是速度更快,而且影響層面更廣。
七○年代的人們,對於侵入的消費文化,可說毫無反抗地照單全收。如果六○年代是男性的年代,那麼七○年代便可說是迎接屬於女性的八○年代的過渡期,也就是半陰半陽的時代。管理社會的繩結,從四面八方綑綁著這些不設防的身體。
從亞洲之旅回來,想著我的國家在現代的急遽轉變,我腦海同時也浮現了一個單純的疑問:
為什麼日本這樣的現代社會架構,對人與物品的管理會到這樣的程度?
這種問題就像「為什麼人會有一種活下來的性向,而這樣的性向又有什麼樣的目的?」之類的問題一樣,雖然單純,卻幾乎無解。
有一些絕頂聰明的人會說,人的求生能量源自於遺傳基因。也就是說,做為生命體,周期有限的人類不過是遺傳基因過境的歇腳處,所以存在三億年的人類,並非單一的個體,而是遺傳基因的集合。也就是說,推動人類求生意志的能量,不過是歸順於遺傳基因生存目的下的附庸,這種論點對我來說,是一個有趣的詭辯。
照這種詭辯的思維,我便可說日本人民的遺傳基因,是從六○年代高度成長期開始變樣的。
在各方齊唱高度成長的環境下,日本民族發生了突變,人人都開始帶有激烈工作的基因。在各方齊唱所得加倍高度成長的環境下,社會上開始以「提高生產力」至上、「效率主義」至上、「進出與擴大」至上,並鼓吹消費的美德。
在此我無意完全否定這種時代的思考邏輯。說不定在貧窮的時代,追求富裕的思想會自然而然地占上風,並且成為時代的正確論點。但是現在看到那些結果,我們又會發現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我們都變成了不得不承擔各種悲劇的存在。
其中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是人與事物的被管理。
現代社會為求人事管理化,而開始具有排除異物的傾向,可說與現代式商業手法同時誕生。
在以生產、效率與擴大做為最高價值的現代商業手法體系中,如前所說,人與人的生活都成為生產所需的兩種功能性零件。這種現象與家庭從過去可以讓人像人一樣營生的空間,變成為了生產與擴大存在的場所。
透過將人當成一個個零件看待,或是將人變成一組組符號管理與操作,提高生產的效率,是生產力的邏輯。再者,為求生產與效率的擴大,必須排除妨礙生產力的七情六慾或行為。接著,日本生活文化中特有的前近代人際關係與社會結構,也顯得沒有意義。與其在家中放神龕佛壇,讓住家中洋溢一股有別於人間現實的往生、解脫或四度空間價值觀,深耕日本人的贖罪意識,不如讓家家戶戶正中央都放著一台電視機,讓電視裡的人喊著「戰鬥!」,讓大家為了得手電視中不斷出現、並撩動他們物慾的「東西」,甚至不惜斷絕家人間的關係,更能裨益於社會、生產、效率與擴大等需求。
換個角度想剛才的問題,便可以理解日本現代社會的結構之所以帶有管理人事與事物的傾向,都是為了提升生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