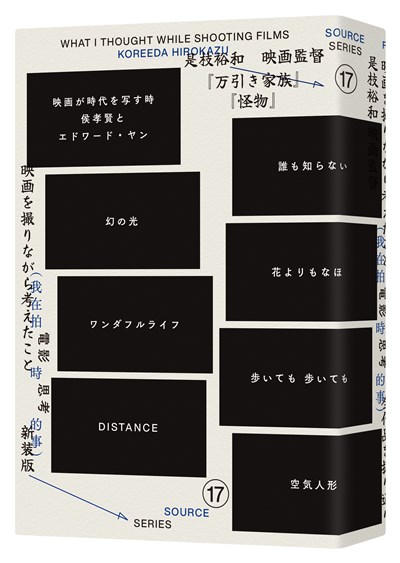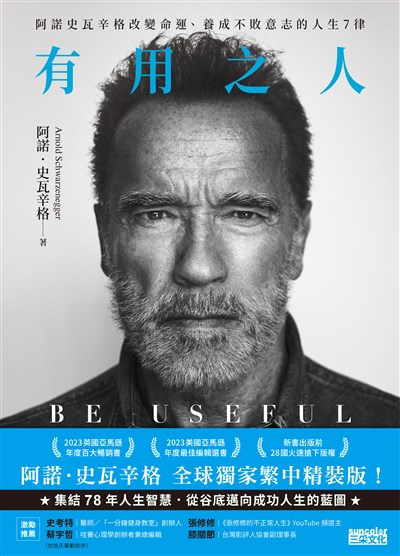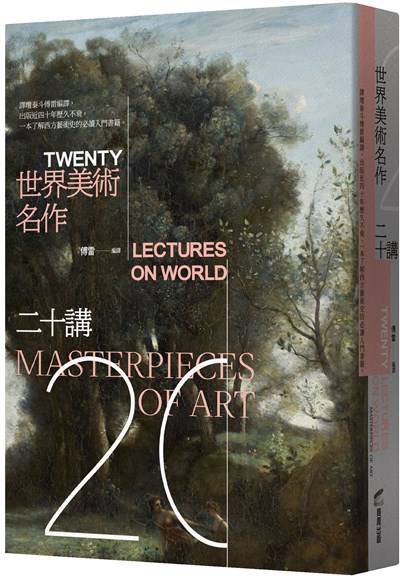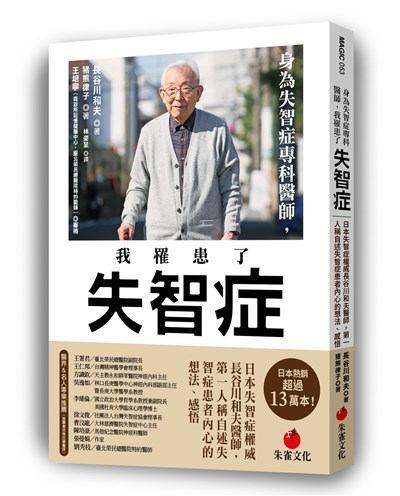大竹伸朗以鮮明強烈風格出道,在業界造成震撼,成為日本新繪畫(New Painting)的旗手。這本書展現蒐羅了他從追憶少年到「全景1955-2006」展創作軌跡全記錄,可以看出他是位匠心獨具藝術家,對於拼貼、印刷術與字型學都有著特殊的感性執著,一篇篇閱讀,感受其創作理念與內心自剖與生活反思的獨白,甚有韻味。
文章節錄
《看不見的聲音,聽不到的畫》
看不見的畫
去年十一月,我造訪北海道野付郡別海町,和別海高中美術社一起舉辦營隊活動。
從企畫定案的去年春天開始,我就想了各種不同的主題,最後,決定做「蒙眼拼貼」,這是一種從頭到尾、完全不看畫面做出拼貼作品的試驗。
在過去幾次的營隊活動中,我曾試過請參加者帶著傳單和不要的雜誌等印刷品,在限定時間內做出一本書來。
這次,因為對象是高中生,我不斷思考能否再深入一點?有沒有辦法藉這個機會,將過去自己抱持疑問的元素活用在這次的營隊中呢?也因為自己在別海的牧場工作時,正值高中剛畢業時,只要一待在美術室裡,我就會有一種錯覺,彷彿過去的自己也混在在當地出生、生活的同年紀年輕人當中,一起坐在裡頭。
通常,畫都是看著來畫,一般來說是不會想要蒙上眼睛作畫。
我記得自己正式開始畫畫時,曾經被嘮叨要「看清楚所畫的目標」。事實上,開始在紙張或畫布上作畫之後,也很理所當然地被告知要「看」清楚構圖,或是要常常遠離對象或畫作,一邊看著他們,一邊繼續畫。
在什麼都不看的狀態下所畫的東西是不是畫呢?人類的看這麼值得信任嗎?人是憑藉著什麼作畫呢?當我針對這個疑問思考時,各式各樣的想法漫無邊際地在我腦海中浮現。
在營隊中,我希望別海高中同學挑戰的是,將全副精神集中在「貼」這動作的「剪貼簿」製作。
和過去一樣,大家帶來不要的印刷品,「仔細看過」之後,將以各自的標準選出來的剪貼素材放入已經準備好的盒子當中,從那個時間點開始到畫作完成的兩天內,共計三個多小時的時間,要把眼睛蒙起來,製作A2大小的畫作。
即使是自己看著、剪下的素材,在蒙上眼睛之後,就完全不知所拿的是正面,還是反面,當然也無所謂顏色的搭配。然後,一邊只憑指尖判斷,一邊將判斷為背面的部分沾上木工用接著劑,進行作業。
看到蒙著眼睛坐在教室內的學生,不知為何,我跳出「音」這個字,就好像鍊子捲上這個字一樣,用以做為本書書名「看不見的聲音,聽不到的畫」的這句話纏繞了上來。
眼前的他們現在不就正憑藉著看不見的聲音,進行聽不到的畫的製作嗎?這個想法模糊出現在我的腦海中。那副光景的確是「聽覺性」的。
營隊的活動內容,事前完全沒有讓學生知道。我以為他們會對我的要求感到很疑惑,作業也無法按照預期進行,但學生們卻表現出強烈的興趣,開心地蒙著眼睛,快速地將素材貼在畫面上。
第一天的蒙眼作業開始後,過了一個小時,動作快的學生的畫面上,已經開始貼上印刷品素材。觀察他們的模樣,我發現他們並不是隨意亂貼,而是已經感受到宛如「在不用眼睛看的狀態下來貼」這個姿態之共通「秩序」。說不定,會出現什麼意想不到的東西。
一九七○年左右,我記得自己曾在高中時期看的美國雜誌《LIFE》裡,看過有關大猩猩畫畫的特輯報導。
特輯扉頁上大大刊載著大猩猩所畫的畫,報導上說,根據拍攝顯示,這幅畫確實為大猩猩所畫。看到那幅畫的瞬間我感到相當疑惑,同時也感受到一股「明確的強度」。
那是一幅色彩鮮艷的抽象畫,無法輕易判斷為「動物畫的畫」的「氣勢」所製造出的顏色和線條,覆蓋著畫面。我突然發現,這裡面一定有「某種東西」。
因為只看了插圖,我不記得詳細的報導內容,然而,與其說是藝術報導,看起來還比較像是學者的實驗記錄。
經過好長一段時間之後,我認為,當時之所以對它不怎麼感興趣,應該是因為自己心中的某個角落帶著「畫是人類所畫的」這種潛意識的偏見濾鏡。
這十幾年來,不知是否是心理作用,我覺得自己看到許多大猩猩所拍照片和所畫的畫,以及大象用銅鑼創作音樂和繪畫的相關情報。
其中,當然有不少案例被當成是才藝表演,但偶爾也會碰到足以讓人毛骨悚然的踏入未知領域的畫和聲音。那個當下,我總是無法視若無睹。
幾年前,我偶然在雜誌上看到全盲者所畫水墨畫的訊息,這讓我想起了過去在《LIFE》上看到的報導。
當然,我不是要草率地說盲人所畫的畫或書,就像動物所畫的畫一樣,或是,這和不看畫來作畫完全無關,也不是要說蒙著眼睛所做的拼貼作品和動物所創作的畫和音樂屬於同一個範疇。相反的,我想說的是,這些乍看之下感覺毫無關係、讓人無意駐足的行為之間,其實連結著針對某種東西的感覺。
「人看著東西來作畫」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人無條件相信的看和畫之間,到底有著什麼東西?
我發現,對於模糊持續存在於自己心中的畫作所抱持的想法,和動物或全盲者的創作之間,不是應該有著超越看和不看的無趣本質嗎?
在別海高中美術社所舉行的營隊成果,遠遠超越預期。完全將訊息隔絕在眼睛之外所畫出的畫面,不得不變成「加法式」的結果,不管是哪位學生的作品,都從「看得見」這件事所得到的各種訊息被解放了。
在那裡,在毫不猶豫地踏入「過剩」地帶的境界難得碰到的「令人覺得清爽的強大力量」,浮現在所有的作品畫面上。相較於中途放棄而以看來進行描繪的畫作,徹底不看所完成的作品,更能觸摸到某種東西,我感覺預測已經接近確定。
我想起了約二十年前所出版的,以夢日記為題材所創作的畫集《Dreams》。
作品中那句「眼瞼就是做夢時的螢幕」突然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人類盲目相信的看與不看這種以一張眼瞼為界線的行為。
不斷重複開關的薄皮膜背面,每天晚上都在放映不需要光源的夢中世界的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