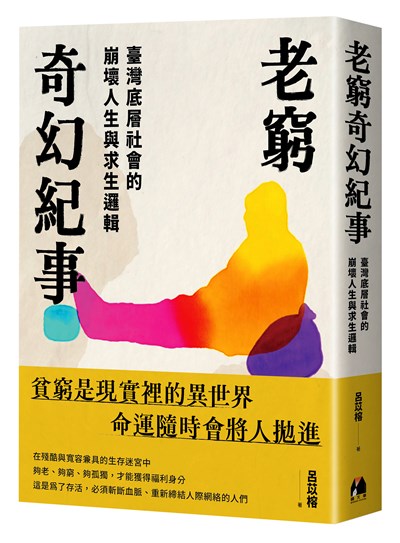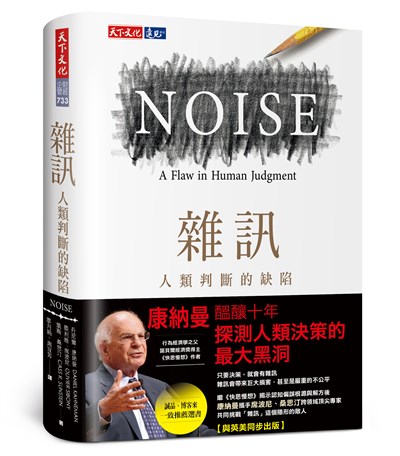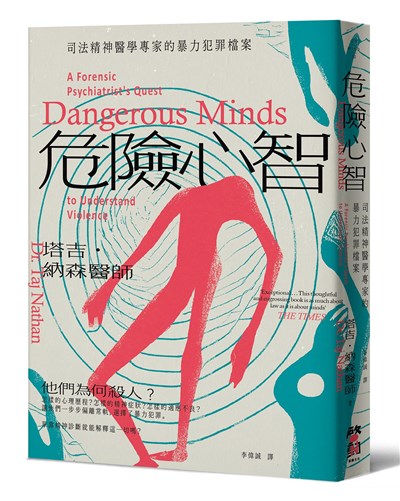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同盟國盟軍開始在歐洲反攻,登陸諾曼地時,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戰地攝影師羅伯‧卡帕跟隨部隊前進。在敵軍子彈一直射來的情況下,他邊跑邊拍照,拍下一系列戰爭照片,卻都是模糊的,因此,本書集結他的戰地手記與照片,書名就叫《失焦》。鏡頭不得不失焦,反映戰爭的殘酷。
羅伯‧卡帕出生於1913年,攝影術才剛開始發展。當時照片必須經過複雜的沖洗過程,戰地拍照不見得馬上可看到照片。羅伯‧卡帕拍下戰時無數珍貴的畫面,底片都先藏起來,再陸續沖洗出來。
1939年西班牙內戰時,他拍到許多經典畫面,其中一張是一名士兵正好被子彈射中,鮮血一滴滴快速濺出來。要拍到一瞬間的畫面多麼困難,這張照片也顯示攝影師當時與士兵距離非常近,那時他已不是攝影記者,而是戰爭的一部分。羅伯留下一句名言:「如果你照的不夠好,那是你靠得不夠近」。
羅伯有一些最棒的照片,卻未見底片,他的說法是「放底片的手提箱後來不見了」。因此他過世後,除了很多紀念活動,也有人懷疑他的照片造假,但另有些人指出,現代的照片容易造假,然而當時有造假的可能性嗎?
去年傳聞有人在南美找到羅伯‧卡帕的戰地底片手提箱,後來卻不了了之。有人認為雖說攝影要真實,但掌控在人的取景與拍攝角度、速度,使攝影有時也不很真實。羅伯‧卡帕的戰地攝影,如今看來仍很震撼且超然,背後想要傳達戰爭殘酷的意圖已經成功,真實性也不那麼重要了。
文章節錄
第十章
【前情提要】一九四四年八月,巴黎光復的前夕,羅伯‧卡帕與海明威一起隨軍朝著巴黎挺進……
我還在格蘭福的時候,海明威送了個訊息給我。自從反攻法國開始,他就一直跟著第四步兵師,他說我軍和敵方大打了一場,對攝影師來說再好不過了;他還叫我不要再跟著一堆戰車後面混日子了。海明威還派了一輛才剛剛從德國人手中奪來的豪華賓士車來接我。我不甘不願地爬上車,被載到他的戰場去。
在英國縫的那四十八針並沒在老爹的頭上留下明顯的痕跡,他也把他那難看的鬍子給剃了,一臉清爽的迎接我。他成了第四師的榮譽成員,全師上下都很尊敬他,因為他不但有著高超的寫作才能,還有異常的勇氣與軍事知識。他在第四師裡擁有一支他專屬的迷你部隊,是指揮官巴特恩將軍指派給他的,他的迷你部隊成員包含新聞官史蒂文森中尉(原本擔任泰迪‧羅斯福將軍的副官)、一位廚師、一名駕駛,以及一名充當攝影師的前摩托車賽冠軍得主。他甚至還有自己的威士忌配額。
這一群迷你軍隊成員的正式身分,叫做新聞公關人員,但是在老爹的影響之下,他們成了一群嗜血的印地安人。海明威身為戰地記者,照理不可以配備武器,但是他率領的這支特遣部隊攜帶了各種各樣想像得到的武器,德製的美製的皆有。他們甚至還有自己的交通工具。除了那輛賓士之外,他們另外徵用了一輛配有邊車的摩托車。
老爹說幾哩外有場不錯的戰役正在進行,他認為我們應該前往探個究竟。我們帶了些威士忌、幾把機關槍,還在摩托車的邊車裡放了手榴彈,接著就往進攻的大致方向出發。
按照計畫,第四步兵師的第八團這時候應該要重新奪回一個小鎮,老爹對狀況全都一清二楚。第八團正在進攻,一小時前已經從村莊的左側突進,老爹確信我們可以從右側抄捷徑進入,不會遇到太大的困難。
他拿出地圖,指給我看這條路線會有多簡單,可是我不太喜歡他這個從右側抄捷徑的提議。老爹有點不耐煩的看著我說,要不然我可以待在原地沒關係。這下讓我別無選擇,只能跟著他,反正我已經很明確地對這次行動表示過反對意見了。我告訴他,我們匈牙利人喜愛的策略是跟在一群士兵後面走,永遠不要單獨走捷徑進入兩軍交戰的中間地帶。
我們踏上通往這個小鎮的路,老爹、他的紅髮司機和攝影師三個人坐上機車往前衝,而史蒂文森中尉和我則距離他們五碼,跟在他們後頭。我們小心翼翼地前進,不時查看地圖,最後抵達了一個大轉彎,繞過去之後就是鎮上了。小鎮那裡並沒有傳出任何槍響,可是我開始覺得非常不自在。老爹不屑的朝我呸了幾聲,我則擺出更嚴正的抗議姿態,跟在他後面。他才剛抵達那個轉彎處,就出現了一種更具威力的、不屑的「呸」響聲——一枚砲彈爆炸了。海明威老爹被震到半空中,整個人跌進了壕溝裡,而他的紅髮司機和攝影師迅速拋下摩托車撤退。我們四個人因為道路的彎曲提供了保護而毫髮無傷,但是老爹就不一樣了。此外,他掉進去的那個壕溝很淺,他的半邊屁股就暴露在外面。德軍曳光彈就打在他頭頂的泥土地上,鎮上入口處的輕型德軍戰車不斷發射砲彈,毫不留情地炸個不停。老爹被困在那裡長達兩個小時,直到第八步兵團姍姍來遲,德軍轉而對付這個更重要的目標為止。
老爹抓緊機會逃命,連爬帶滾到了我們這邊會合。他氣炸了。與其說是對德軍火大,不如說是對我個人發脾氣,他指控我站在一旁袖手旁觀,等著想拍到知名作家死於戰火的獨家照片。
傍晚的時候,海明威這位會寫作的戰略家,和我這個會拍照的匈牙利軍事專家之間的關係,顯得緊張了起來。
通往巴黎的道路正在呼喚我們。第三軍團抵達了巴黎城外約六十哩的拉瓦爾,我急著要追上他們的腳步。沿途偶有槍戰,還遇到一群累壞了的德軍戰俘,經過了另一個戰事公報上出現的光復城鎮,最後抵達了宏布耶。這是我們到巴黎前的最後一站,而我們之所以在此停留,純粹是政治因素。
巴黎人民已經奮起對抗德軍,盟國的最高指揮官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戴高樂新軍的菁英法國第二裝甲師(當然配有完善的美式裝備)進入巴黎,是一件非常恰當的事情,由他們來擔任解放部隊的開路先鋒。
法國的軍力在宏布耶集合,為了這最後一擊做準備。來自四面八方的打字機也聚集在宏布耶附近,每一位獲得採訪許可的戰地記者互相爭奪著、計畫著要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的記者,想要在這個充滿歷史光輝的偉大城市裡,紀錄下歷史的新頁。
早在自由法國軍隊與新聞媒體大軍殺到宏布耶之前,海明威老爹就已經抵達此地了。他的私人四人軍隊已經從法國反抗運動當中召集了一批熱血沸騰的年輕小伙子,人數暴增為十五人。這支雜牌軍和老爹很相像,成員們把老爹熊一般的走路樣子學得徹底,以各自的母語從嘴角呸出簡短的句子。他們所攜帶的手榴彈和白蘭地,比一整個師還多。每天晚上他們都會出動襲擾宏布耶與巴黎之間還僅存的小股德軍,而且老爹的軍隊裡,再也沒有留給匈牙利軍事專家的位置了。所以我又重返我的上司、《時代雜誌》的查爾斯.渥廷貝克的身旁,他有自己的吉普車可以直奔巴黎。
八月二十四日,法軍的戰車準備出發上陣。二十五日晚間,我們在一個路牌下野宿,上頭寫著:巴黎地鐵──六公里。在所有露宿路牌下的經驗當中,這次是最棒的了。
早晨時太陽匆匆升起,我們沒閒工夫刷牙,戰車已經在馬路上隆隆作響。在那個令人雀躍的早晨,當我們出發的時候,甚至連我們的駕駛、陸軍一等兵史崔藍都忘了他的維吉尼亞老家禮儀,反而三不五時就用手戳一下我那位優秀上司的肋旁。
距離巴黎城外兩哩的地方,我們的吉普車被一輛隸屬於法國第二裝甲師的戰車給攔了下來。我們獲知不能再繼續前進了。法軍的雷克勒將軍下令,除了法國第二裝甲師的士兵之外,嚴禁他人進入巴黎。這老傢伙這樣搞,肯定會弄得天怒人怨。我跳下吉普車,跟戰車裡的人爭論,他們說的法文帶著西班牙文的腔調,接著我注意到這輛戰車的名字,砲塔上漆著的字是「特魯埃爾」。
一九三七年冬天,我和西班牙共和黨在一起拍攝內戰的時候,曾經和他們一起經歷了最盛大的勝利之一,特魯埃爾之役。我對坐在戰車裡的人說:「少給我來禁令這一套,你無權阻止我,我也是你們的一份子──我親自參加過那場殘忍的戰役。」
「如果你說的是真的,」他們回道:「你講的若是實話,那麼你就是我們的一份子,你就必須跟我們一起走,搭著這輛貨真價實的特魯埃爾號前進巴黎!」
我爬上了戰車,優秀上司查理和駕駛兵史崔藍開著吉普車跟上。
通往巴黎的路開了,所有法國人都在街上,伸手想撫摸第一輛進城的戰車,親吻第一個進城的士兵,高聲歌唱與忘情痛哭。從來沒有這麼多人,在這麼早的早晨,是這麼的開心。
我覺得這次進入巴黎,簡直就是替我個人量身打造的場合。我坐在一輛美製戰車裡(美軍早已接納了我),跟隨著一群我曾在多前年一起對抗法西斯黨的西班牙共和主義者;而我正在返回巴黎的路上,回到這個我學會品嚐美食、欣賞美酒、付出真愛的美麗城市。
我相機取景器裡出現的成千上萬張臉孔,變得越來越模糊;取景器非常非常濕。我們開過了我曾住了六年的街坊,經過了我在貝爾福獅子像旁的房子。我的公寓管理員正揮舞著手帕,我從這輛不斷前進的戰車上向她大喊:「C’est moi, c’est moi!」(是我,是我啊!)。
我們停下的第一站是蒙帕拿斯的多摩咖啡館。我最喜歡的座位是空著的。穿著淺色花樣洋裝的女孩爬上了我們的戰車,人工的口紅立刻覆滿了我們的臉。這些西班牙士兵裡長得最帥的一個,簡直被親吻到滿臉一蹋糊塗,沒想到他喃喃自語道:「我寧願被馬德里最醜的老太婆親吻,也不願被巴黎美麗的女孩們親吻。」
在議院外圍,爆發了戰事,鮮血覆蓋掉了一些口紅的痕跡。當天傍晚,巴黎自由了。
我想在巴黎最好的地點度過第一晚──麗池大飯店。可惜麗池飯店早已經被另一路人馬給解放了。海明威的雜牌軍從另一條路進入巴黎,在巴黎度過了短暫而愉快的夜晚後,又征服了他們的主要目標,從德國佬手中解放了麗池大飯店。瑞德站在門口負責守衛,開心的笑著,展露出掉落的門牙。他模仿海明威的說話方式告訴我:「老爹拿到了好飯店。酒窖裡有不少好東西。你快上樓。」
說得沒錯。老爹與我言歸於好,替我辦了個派對,還給了我飯店裡最好的那間房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