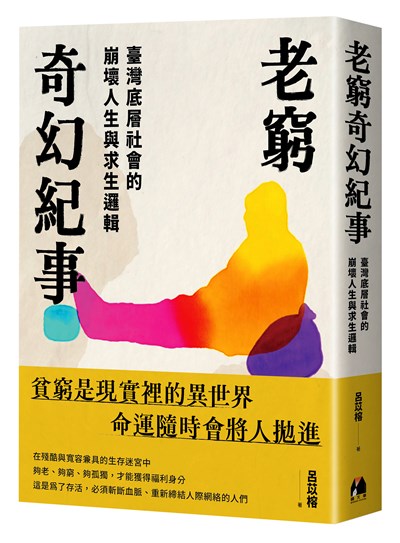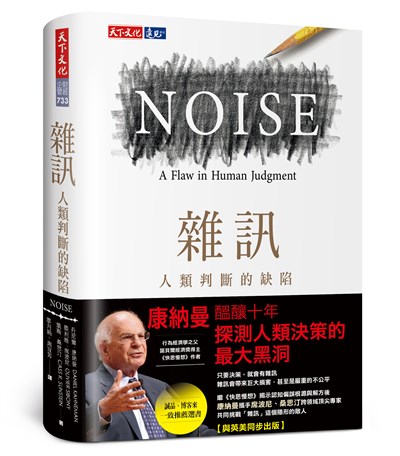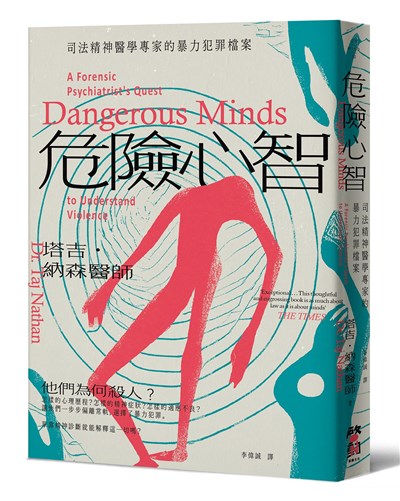以色列和巴基斯坦的衝突,是「冤冤相報何時了」的明顯例子,但臺灣過去受西方觀點影響,難免對以巴地區那個伊斯蘭(回教)世界有著隔閡的偏見與誤解,東方主義學者愛德華‧薩依德的著作《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最後一片天空消失之後的巴勒斯坦》,有助認識伊斯蘭世界與以巴衝突。
兩年前過世的薩伊德是巴勒斯坦人,在埃及長大,在這本書裡,他寫自己成長的過程與巴勒斯坦人流亡的經過,並回顧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衝突,包括加薩走廊如何割讓給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如何被驅趕遷出耶路撒冷,類似個人回憶錄的書寫,相當能呈現伊斯蘭世界各種族身分認同的複雜性。
其實,以色列(猶太)與巴勒斯坦的民族、宗教信仰不同,從聖經時代就種下衝突的根源,最早有猶太人出埃及,後來猶太復國建立以色列,而要趕走巴勒斯坦人,因此,爭執的土地屬於誰?實在是歷史的難題。但猶太人在美國擁有影響力,所以美國支持以色列,因而與巴勒斯坦有很大衝突,甚至牽動國際局勢。
包括波斯灣戰爭、恐怖主義與恐怖戰爭如美國「九一一」慘劇,都是根源於此,近年印尼巴里島的恐怖爆炸事件,顯示印尼伊斯蘭教和西方資本主義的道德觀衝突激烈,也是西方殖民對回教徒壓抑排斥的後果,因而成為世界衝突的主要源頭之一。
薩伊德後來到美國接受西方教育,並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成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化評論學者。看待以巴問題,他能針對殖民後留下的種種課題,如民族、文化認同產生問題,人口遷移的複雜衝突性,以客觀多元而周延的角度,研究後殖民理論,而這本非理論的回憶錄,穿插攝影圖片,令一般讀者覺得有趣而容易閱讀。
文章節錄
1國家STATES
在一個土褐色阿拉伯城市的外圍,在一個難民營的旁邊,在接二連三災難暫一停歇的空檔,一支迎親隊伍被照相機拍個正著。他們顯得驚訝、不快和有一點點不自在。他們是巴勒斯坦人(從他們的姿態和他們的混雜風格可清楚看出),住在黎巴嫩北部的的黎波里附近。這照片拍攝的幾個月後,他們的難民營便受到巴勒斯坦人的內部戰鬥所蹂躪。斜停在小路前方的是一輛無處不見的賓士轎車,車尾箱上那個自豪的D字母(表示「德國」)表明它是原裝貨。賓士轎車在西方是奢侈品,卻是黎凡特地區(Levant)最普遍的代步工具,幾乎一律是走私進口的二手貨。它取代了馬匹、騾子和駱駝的工作,又被賦予了更多其他任務。除了通常作為計程車以外,它還象徵著現代科技的本土化,象徵著西方生活方式對傳統生活方式的入侵,象徵著非法買賣。更重要的是,賓士轎車在這地區已成了一種萬用的工具,可以派上各種用場:喪禮、婚禮、生小孩、炫耀、上班、下班、維修、偷竊、轉售、跑路、躲藏。但因為巴勒斯坦人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可以庇護他們,於是,來源和目的地都不明的賓士轎車遂顯得是個入侵者,代表著那些既打亂他們生活節奏又團團包圍著他們的力量。「大地在我們面前闔上,驅趕我們走上最後一程。」詩人戴爾維什(Mahmoud Darwish)如是說。
機動性與不安全感的弔詭。不管我們巴勒斯坦人身在何處,都不會是身在巴勒斯坦,因為巴勒斯坦已不復存在。不管你是從阿拉伯世界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是在歐洲、非洲、美洲還是澳洲旅行,你都找得到像你一樣的巴勒斯坦人,找得到像你一樣受特殊法令、特殊身分限制、帶著被施暴印記的巴勒斯坦人。除了在外地流亡以外,我們還在自己的家園流亡,因為繼續有巴勒斯坦人住在從前那片叫巴勒斯坦的土地(如今由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帶構成)。但不管是流亡哪裡,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間皆已悲慘地大受壓縮。他們要麼被稱為「朱迪亞和撒馬利亞的阿拉伯人」(the Arabs of Judea and Samaria),要麼被稱為「非猶太人」(non-Jews)。他們有些還被稱為「在場的缺席者」(present absentee)。在除約旦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國家,他們拿到的都是特殊的識別證,上面把他們的身分標示為「巴勒斯坦難民」,所以,即使從事的是工程師、教師、生意人和技術人員等體面職業,但在地主國眼中,他們始終是異類。無可避免地,今日凡是以巴勒斯坦人為主題的照片都會包含這個事實,使得它昭然若揭。
記憶讓巴勒斯坦人的流放生活更加滿懷愁緒。巴勒斯坦位居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猶太教三大文化的中心,而東方和西方都一直把它說成是一片神奇地域。沒有人敢忘記它,沒有人敢忽視它。世界新聞常常滿是有關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區的報導,包括最新一場的中東危機或最近一次的巴勒斯坦人英勇抵抗行動。巴勒斯坦的景點、物品和紀念碑是商業、戰爭、朝聖、膜拜的對象,是文學、藝術、歌曲和奇想的主題。不管是東方或西方,是高級文化或商業文化,都曾向巴勒斯坦吸取靈感資源。照片中一對新人穿著不太合身的西方結婚禮服,但他們周遭親友卻是穿戴本土衣著飾物,顯得自自然然。這場合的歡樂氣氛與他們無處可去的難民身分格格不入,而在旁邊玩耍的小孩也跟四周毫不吸引人的環境形成觸目對比。新郎有一雙工人的大手,新娘則手指纖細、朦朧白皙,二者很不協調。每當我們從巴勒斯坦流亡到其他地方,即使我們在新環境過得體面,舊日的一切仍會如影隨形逼近,像記憶一樣既具體又不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