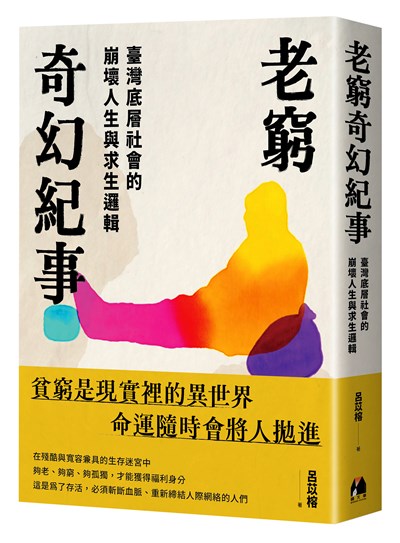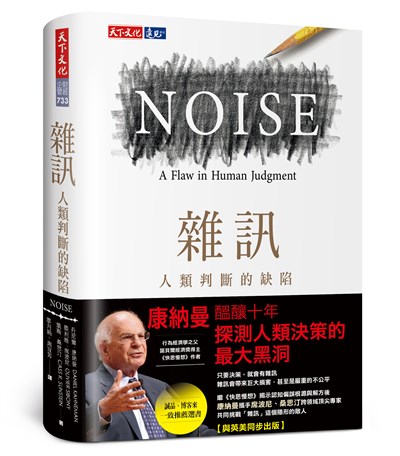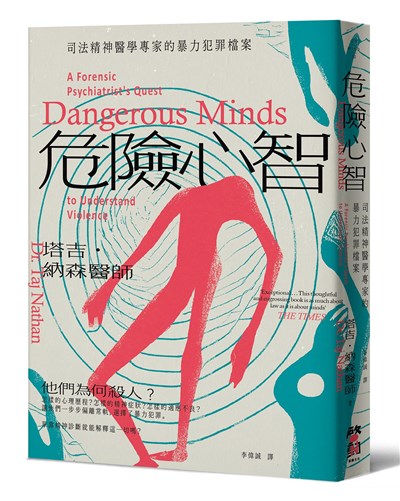在那個錢淹腳目的時代,每吹一支玻璃就像吹出一張紙鈔,是人們擠破頭的行業,如今,老師傅們做一天是一天,等待退休…台灣曾經有非常輝煌的玻璃產業,不過目前仍存在的傳統八卦窯手工燒製玻璃工廠僅不過四家,是即將消失的產業。介於生產自動化與精緻工藝化之間,《透明的記憶》透過最後一批玻璃老職人的生命故事與精彩影像完整呈現「窯口玻璃」的製作方式,並採訪當今活用玻璃材質的設計品牌,讓經驗再分享,延續產業的可能性。
文章節錄
《透明的記憶:感受日常玻璃的溫度》
記憶,走過臺灣窯口玻璃百年
「窯」是傳統玻璃製程中最重要的特徵,在一千五百度以上的窯爐裡,放入陶製耐高溫的坩堝,就是一個可以作業的窯爐。一個八卦窯,會有許多個窯口,玻璃師傅用工具從坩堝裡挖出玻璃膏,接著利用各種技法,將它製成玻璃用品,我們統稱經過這樣製程的產品為「窯口玻璃」。
以八卦窯爐作為主要生產工具的玻璃工廠,每日最大的成本就是保持二十四小時燃燒。在臺灣玻璃產業鼎盛時期,每個窯口都有人在生產玻璃。到如今,大部分的玻璃廠都已經關閉,甚至有些窯爐要等訂單收夠了再開爐生產,能持續燃燒的玻璃廠已經寥寥可數。玻璃產業在臺灣沒落,部分是因為替代品塑膠的崛起,部分是因為更便宜的勞動力在中國大陸出現。玻璃留在臺灣剩下兩種極端,一是以數十萬件起跳的全自動化大量生產,一是藝術化的個人工作室。
介於兩者之間:沒有顯赫名聲的老師傅,也無法日日萬件的生產;可他們整日守著高溫窯爐,用雙手悉心照料每個物件。他們的玻璃,折射出生活在臺灣你我的日常。
過去的痕跡
在新竹及苗栗這一帶,曾因豐富的矽砂與天然氣,讓臺灣的玻璃產業蓬勃發展,當時可是許多人嚮往的行業。許多像利詮玻璃老闆邱文虎一樣的人,國小一畢業便進入產業,從學徒做到老闆,與臺灣一同經歷了那個錢淹腳目的時代,再走過大陸開闢設廠,然後又返回這塊土地。在他的身上,我們可以讀到一代人的臺灣經歷;他們製作出來的玻璃,都是臺灣過去的生活光景。
火燒出來的工廠─邱文虎
家無恆產的赤貧之子,國小畢業後認份的進入玻璃工廠學藝,熬過三年四個月的學徒生涯,通過傳統師徒制的測試,成為日薪一百五十元的年輕小師傅。十八歲破紀錄當上最年輕的廠長,卻管不動資歷比他深的工人,工作時間不減反增,過著每天工作超過十六小時的日子。
「結果我變成這一行中學的最全面的。」邱文虎掩不住得意的說,他不僅會全套的玻璃製程, 對內會蓋鍋爐、退火爐、各種配料,對外懂得談生意、做業務。後來,他將新婚妻子的嫁妝拿去變現,加上標會湊足七萬元,與六位師兄弟合資開工廠,那年他才二十三歲。
「臺灣的玻璃工業,主要有兩個系統,一是日本人轉移過來的技術,以儀器類為主,技術難度比較高;另一個是國民政府從上海帶來的,以瓶罐製作為主。我學的是日本這一派,也是早年玻璃產業比較賺錢的。」
邱文虎回憶說,當時正逢十大建設陸續啟動,工業替代農業、客廳即工廠的口號喊得震天響,臺灣的玻璃產業也直線上升,「單是竹南地區就有多達兩百多家玻璃廠。」而他也在全家人以廠為家,以生力麵果腹的日子中慢慢站穩腳步。
「剛開始都是身上帶著十塊錢,騎摩托車出差。」他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大碗的陽春麵三元,加上台北來回油錢,「如果遇上車子壞掉修理就不夠錢。」因此,當時父親送他的一隻錶,常被作為抵押品,「後來我還去最常抵押的加油站,想謝謝他們,可惜已經拆除。」
就在這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卻讓他歸零重來。當時人在外地收帳的他,接到股東通知,等回到工廠看到一片火海,「整個人都呆了,股東在哭,倉庫裡價值兩百多萬的成品全都付之一炬。」三十幾年後提起,仍歷歷在目。
幸而生產設備神奇的毫髮無損,工人情義相挺下,在空地搭起棚架權充倉庫,災後第三天便復工。「火災前,我們一天大概可以生產一百多個燈罩,但重新開工後到第三天就衝到一天三百多個,最高峰曾經衝到一天生產一千多個。」他笑說,後來發現銀行催跑三點半的電話不再響起,反倒是存摺金額不斷增加,讓他有著做夢般的不真實感。
「我最感謝一位父執輩的派出所警察所長。」當年這位所長不僅協助他處理災後事宜,還因緣際會幫他訂了一塊地,因此在工廠開始賺錢後,邱文虎便斷然決定新建廠房,員工也由原來的六七十人擴增到兩三百人,兩個廠一個月可以生產六千多個燈罩。「真是冥冥中有神明保佑,憑著一股傻勁,卻不斷遇到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