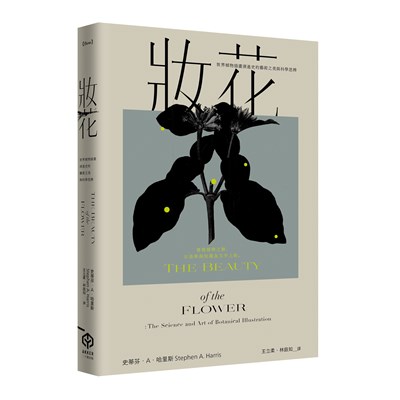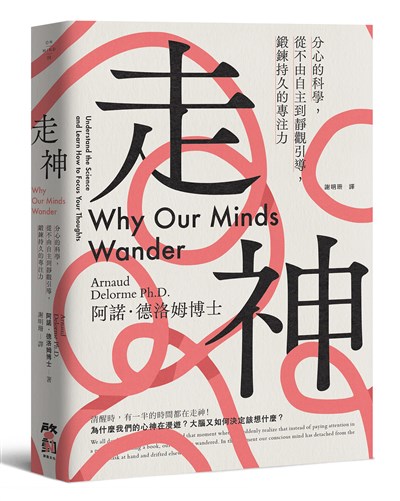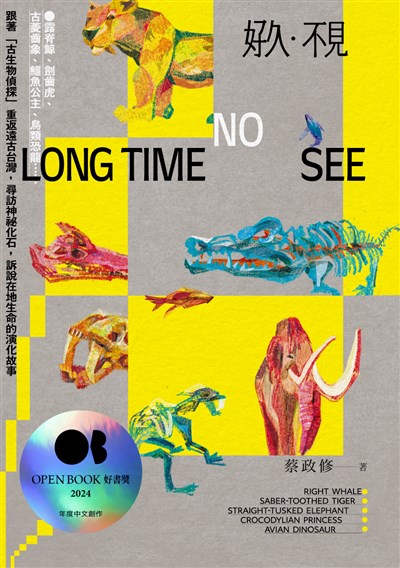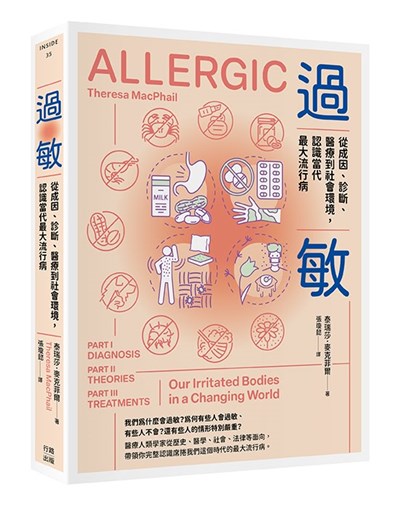歷史學者西奧多.羅斯札克在九○年代倡導「生態心理學」,引領生態與心理學界聯手面對人類與環境逐漸崩壞的關係,並彙編這本經典之作,收錄20多篇舉足輕重的先行者經驗,對一般讀者或心理學與環運相關人士,都將是不可錯過的作品。
文章節錄
《生態心理學:復育地球,療癒心靈》
魔法之生態學/大衛.亞伯蘭(David Abram)
「魔法」在當代社會裏,主要是以喜慶表演或兒童文學的型態殘存著。但就像大衛.亞伯蘭發現的,在傳統社會中,魔法師同時也具有生態學家的功能。亞伯蘭身為生態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業餘的戲法表演家,他發現自己對峇里島(Bali)薩滿巫師的研究,強烈地改變了他和「人類以外」世界之間的關係,直到他又回到所謂的「文明」裏面。他在這篇文章中提醒我們,生態心理學可以從古代泛靈式的感受能力中學到許多事情,只要我們願意帶著耐心與尊重去探索它。
★ ★ ★
……和大眾對薩滿學是一項個人超越工具的普遍認知一樣,流傳於美國非主流文化圈中對「魔法」最精微的定義是:「能隨心所欲地轉變個人意識的能力或力量。」當中對為何要轉換個人意識狀態,並未提及任何理由。在部落文化中,我們所謂的「魔法」所隱含的意義乃基於一項事實,即在原民口傳的文化脈絡中,人們體驗到自己的智能只是多種覺識型態中的一種。傳統的魔法師培養出能從平常的意識狀態中脫出的能力,就是為了要以其他物種本身的方式與之接觸。薩滿只有在暫時卸去文化中既定的知覺邏輯時,才能與賦予當地地景生命能量的諸多非人感應力產生連結。也可以說薩滿的定義是:一項為了接觸大地中的其他力量並向之學習,而可隨時跳出其特定文化知覺界限的能力,這些界限在社會規範、文化禁忌,尤其在日常對談或語言中受到強化。薩滿的魔法正是他所擁有的超高接受力,用以接收週遭廣大的非人世界中,充滿意義的歌聲、鳴唱與姿態等引領訊息。
在我前往印尼研究魔法在醫療上的運用當時,魔法師與非人自然世界的關係其實並不是我立意探討的目標,我是後來才漸漸察覺到當地魔法師的技能中這個較細膩的面向。我第一次改變成見,是發生在峇里島內陸一位年輕巴里安(balian),也就是魔法修習者,的家中留宿數日時。他們從家族屋群(峇里島上大部份的住宅是在一塊圈圍起來的土地上,由幾間分立的小屋一起組成)給我一間只有一個房間的獨立住所,裏頭只有一張簡潔的床鋪。每天早上,那位巴里安法師的妻子會過來給我一盤美味的水果,我則獨自靜靜地坐在屋外的地上用餐,背靠著我住的屋子,看著太陽慢慢地從婆娑的棕櫚葉隙間昇起。
我注意到這位女主人給我水果的時候,同時還端了一個大托盤,裏頭還有好幾個船型的綠色小淺碟,每個都是用一段新鮮的棕櫚葉巧編而成。這些小碟子大概有兩、三英吋長,每一碟裏頭盛著一小坨白米飯。女主人給我早餐後,就托著盤子消失在其他屋後,幾分鐘後,她回來收我空盤時,她的托盤裏也是空的。
第二天早上,當我看到那排盛飯的小碟子時,我問女主人它們的用途。她很有耐心地向我解釋,這些是準備給家中神靈的供品。當我細問峇里語中她說的那些「神靈」時,她重複地用印尼語向我解釋,說明這些是準備給家族屋群中神靈的禮物,我想我對她的意思的理解應該正確。她給了我一盤切好的木瓜和芒果後,又走到屋子轉角處離開。我思考了一會兒,放下碗,走到我小屋側邊,在樹縫間探視。我看到她在另一間房子的角落旁彎身下去,小心翼翼地擺放著我想應該就是供品的東西。然後她起身端起托盤,走回另一個屋角,又擺上另一份供品。我則回去把我早餐碗裏的水果吃完。
那天下午,當大家各自忙著其他家事時,我走到屋子後面看到她擺放供品的地方。在屋子後頭那兩個屋角,確實安穩地擺著綠色的小碟子。但裏頭的白米飯卻已經不見了。
第二天早上我吃完切好的水果,等女主人過來把我的空碗收走後,我便靜靜地走到房子後頭去。兩個棕櫚葉小碟盛著的供品,就放在前幾天其他供品擺放的位置上。碟子裏盛著米飯。我正在注意其中一個碗時忽然嚇了一跳,發現裏頭的米粒正在移動。直到我跪下來靠近看清楚,才看出有一小列黑色的螞蟻正在土壤中蜿蜒地朝這片棕櫚葉走去。再更靠近點看,我看到兩隻螞蟻已經爬到供品上頭,正用力要搬走最上層的那粒米飯;我看到其中一隻將一粒米飯拖下棕櫚葉,沿著原先螞蟻部隊的路線搬回家。第二隻螞蟻搬走另一粒米,爬下飯堆,又拖又推的,結果摔到葉子外頭去;第三隻螞蟻又跟著爬上供品。這一整列螞蟻是從附近一株棕櫚樹旁濃密的草叢中爬出來的。我走到另一份供品處,發現另一排小螞蟻也正在搬動米粒。在我屋子後面的地上還有另一份供品,同樣有一排近乎一模一樣的螞蟻隊伍。我走回自己的房間咯咯竊笑。那位巴里安和他的妻子每天大費周章準備用來安祭居家神靈的供禮,徒然被那些細小的六腳小賊給偷光光了。多麼浪費啊!但,突然間,有個奇怪的念頭在我內心湧現。如果這些螞蟻本身就是供品所要供養的居家神靈呢?
這個想法我越想越不奇怪。這個家族屋群就和其他位在這個熱帶島嶼上的屋群一樣,蓋在好幾個螞蟻窩之間。既然家中眾多的烹調工作都在屋子裏進行,又有精心為各種儀式慶典準備的食物供品,這塊地和這些房子很容易就會被螞蟻侵入築巢。這種入侵可能小從偶發性的騷擾,到定期性的出沒,大至持續性的圍攻都有可能。每天用棕櫚葉提供的供品,很顯然是在排除這些環繞著(或潛藏於)家族土地的自然力量的攻擊。每天用白米做為供禮讓螞蟻群有事可做,想必也讓牠們感到滿足。這些供品每天規律地放在屋群各處不同屋角的同樣位置,似乎在人類和螞蟻社群間建立了固定的邊界;人類透過祭禮來尊顯邊界,顯然希望勸服這些昆蟲也尊重邊界的設定,不要進入建築物中。
但我仍對女主人宣稱這些供禮是「給神靈的」感到困惑。很明確的是我們西方對「神靈」(通常是相對於物質的或「有血有肉」之物)的概念,和部落或原民文化中敬重的神秘存在之間,總是有著某種程度的混淆。早期西方學習各種語言風俗的學者們,有許多是基督教傳教士,他們習慣在部落居民只是單純對當地的風表示敬重時,將之視為神秘無形的鬼怪。對西方人而言,「神靈」的概念大多具有人形化或與人有關的聯想,我遇到這些螞蟻的經驗是我第一次發現,原民文化中的「神靈」主要是指不具人形的智能或覺知型態,爾後仍有許多次經驗提醒我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