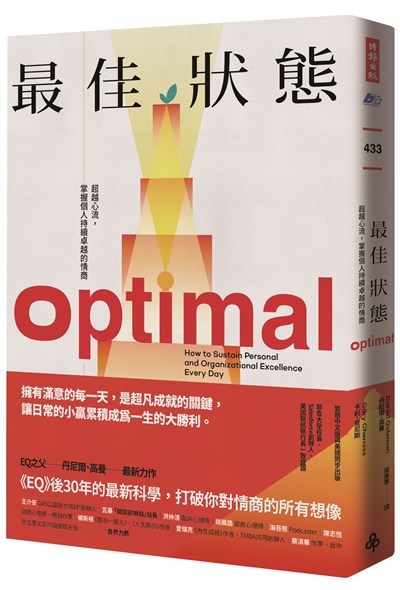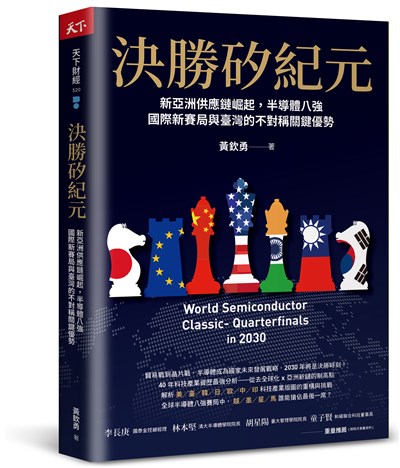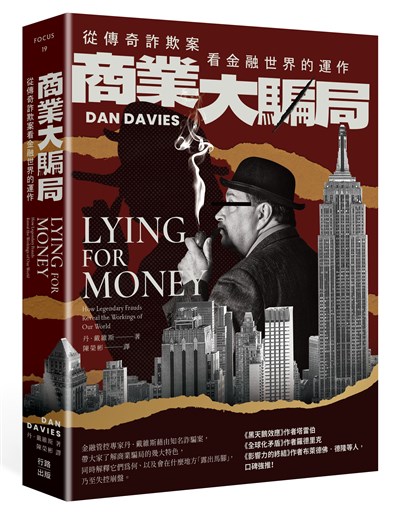歷來談論馬克思、共產主義,多從社會、歷史、文化等角度探討,《資本的空間》一書則從地理學的空間角度探討左派論述,也點出當代如貧富不均等很多深刻的問題。在當前左派、右派思想仍在較勁拉鋸的情勢中,讀者也不妨從地理學的面向重新思考,或許可以獲得一些截然不同的省思與推論。
這本書蒐集很多學術性、批判性的文章,主編大衛‧哈維就是地理學者,他認為傳統的地理學充斥種族主義和族群中心主義,西方地理學家往往會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解釋地理學上的資料。所以,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一樣,看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結果。也就是說,很多人認為地理學是一門很客觀的知識,其實正好相反。
本書論述表示,東西方不均衡的地理擴張帶來空間重組,使全球資本朝向不公平的方向累積,產生西方資本家與無產階級,而資本累積就是地理事件。如果沒有十四世紀以後一波波西方國家地理性的擴張,就不會有資本主義後來形成貧富不均問題的樣貌。
本書的學術批判性,令一般讀者不太容易切入,有興趣的人不妨從前面兩章讀起,應能慢慢進入「從地理學角度看左派世界」的空間。例如第一篇與哈維的訪談,主題是地理學如何看待當前資本市場面臨的問題;口語對談方式使讀者較易了解地理學如何影響資本主義,也能驗證從地理學看事情,確實能看出不一樣的內涵。
文章節錄
地理學者對公共政治形成能否提供成功、重大且有效的貢獻?
皮諾契將軍(General Pinochet)是一位受過正規訓練的地理學家,他也成功的將地理學應用於公共政策。皮諾契以軍人集團首腦身分,1973年9月11日推翻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領導的智利民選政府,成立軍事政府。他反對類似社會學、政治學,甚至哲學等具「顛覆性」的學科思想,要求所有智利學校和大學都必須教授「愛國思想課程」,他大力提倡地理課程,也是眾所周知——據他說,這種科目最適合用於教導智利人民愛國思想,向人民傳達他們真正的歷史命運感。由於軍隊完全控制了大學,並嚴密監督學校教學,地理學必將成為智利教育系統中的重要學科。
皮諾契將軍也積極改變智利的人文地理。這裡有個恰當的範例。智利的健康照護系統有段時間曾包含三個不同部分:富人依據「自由市場」準則來支付醫療服務;中產階級利用民營保險計畫資助的醫院系統;低階層及窮人(約佔人口的60%)則透過國家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體系支持的社區健康中心,接受免費醫療照護(Navarro 1974)。前述三個部門中,第三個部門向來資金不足,備受忽略,但是在阿葉德執政期間,資源逐漸由前兩個部門移轉至社區健康服務。健康照護體系的地理,開始從一種迎合中上階級需求,由供應者掌控、以醫院為中心的集中式系統,轉化為由社區掌控的分散式免費健康照護系統,以符合下層階級與窮人的需求。這種轉型並非全無抗拒——醫院系統供應者發動示威,力求保持舊有的健康照護的社會地理,反對新地理的興起。然而,社區健康中心在阿葉德在位期間蓬勃發展。此外,透過成立社區健康委員會來達成社區控制,對政治影響甚鉅,生活的諸多面向也開始環繞著社區健康中心組織起來。健康照護的重心也由治療醫學(擁有令人目眩神移的昂貴裝備)轉變為預防醫學,將醫療照護視為整體環境議題(供水、汙水處理等等)不可或缺的一環。社會接觸、政治權力及分配的人文地理,因而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下層階級和窮人開始了解他們控制自身所處社會狀況的潛力。
但軍事力量和皮諾契將軍改變了這一切。社區健康委員會解散了,許多參與者也遭囚禁或處決。社區健康中心的運作受到嚴重限制。醫療體系的管理大權重回醫藥供應者手中,回復至一種以醫院為中心、符合中上階級需求的集中式系統。治療醫學又成為常規,少數人的開心手術取代多數人的衛生環境改善,成為醫療保健的主要目標。舊地理捲土重來,新地理則遭廢棄。因此,地理學家(皮諾契將軍)的介入,成為智利健康照護體系之人文地理的決定性力量。
智利似乎與英國相去甚遠。然而,我之所以引用這個例子,並非要同英國比較,尋求相似之處(儘管這裡不得不指出,一個在1939至1945年間堅決反抗法西斯主義的國家,卻在皮諾契將軍當權後急切地伸出友誼之手。不但如此,1973年夏天,英國國家健康服務重組,移除所有社區控制的痕跡,將健康照護的提供牢牢交在偏好集中式醫院健康照護系統的供應者手中)。我的關切是要利用這個地理學成功介入公共政策的範例,指出將地理學應用於任何公共政策之前,必須提出的兩個非常基本的問題:「哪一種地理學?」及「用於哪一種公共政策?」
這些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也許比較好的方式是先探問:我們一開始為什麼會覺得有必要將任何類型的地理學應用於任何類型的公共政策。如果我們認真思考我們的動機,會發現這種急迫感源於個人抱負、學科帝國主義、社會需求和道德義務形成的奇特混合。某些人受各種因素影響(或自認為受影響)的程度可能不一,但毫無疑問的,沒有人能聲稱自己完全不受任何影響。
個人抱負是個重要因素,因為我們都成長於一個內蘊了個人主義和競爭性的經濟和社會體系。由於社會裡的權力(包括經濟和政治)大致集中於公共領域,學者便自然而然被吸引到權力之所在。個人野心大概是解釋個人行為的動機因素中,最重要的一項,卻無法充分解釋地理學者的行為不同於其他學科人士之處,而且至少在英國,一個野心勃勃的學者是否會在學科階序分明的學術界中,選擇一個明顯劣勢的基地〔譯按,指地理學〕為出發點,恐怕不無疑問。
就某種程度而言,學科的聲譽和地位是一種以群體意識為仲介的個人抱負。學門無可避免地將個人予以社會化,使個人以「地理學」、「經濟學」、「生物學」等詞彙來定位自己的認同。我們常在他人問起「你是誰?」時,回答「我是地理學家(或經濟學家、生物學家等)。」學科的重要性在於它能讓我們了解自己的角色,進而提供安全感。然而,地理學是諸多學科的一支,必須與其他學科爭取公眾眼中的地位和特權。各學科也會競爭公共經費。因此,那些自稱「地理學家」者的保障,大致取決於地理學相對於其他學科的地位。於是,我們就認為「對地理學有利者必對我有利」,進而認知到「對地理學的威脅就是對我的威脅」。發揚地理學就是彰顯自己,我們也藉由保衛地理學來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