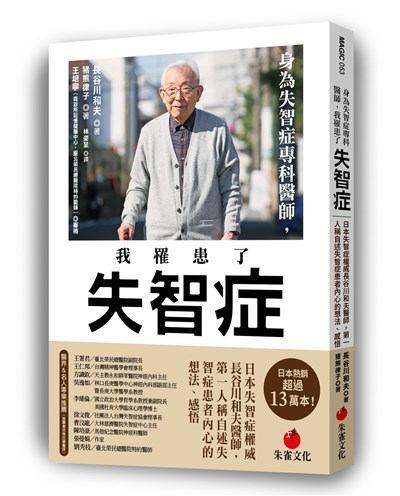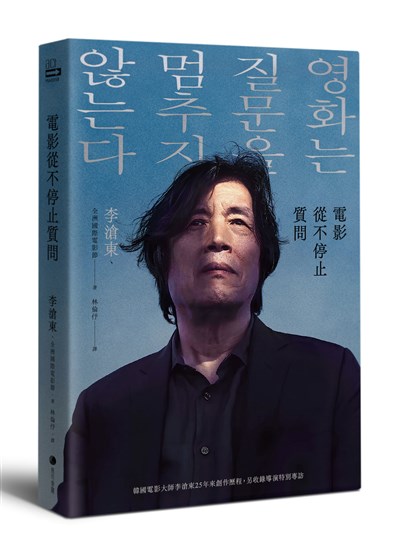本書不是第一世界國家醫師以救世主的姿態,站在高而遠的位置俯就飽受摧折的非洲;更非一名掌握知識與生殺大權者的豐功偉業之書。作者馬斯卡利克醫師以筆記散文形式書寫急診室所見證的傷痛、貧病、哀悼、歡笑、悲劇與希望,可謂急救醫學邊緣地帶的來信、跨越國界與文化藩籬的現代醫學省思錄。
文章節錄
《我在一樓急診室的人生:現代醫學的邊境來信,一位人道救援醫師的自白與生命省思》
前言
我在友人的小屋,走到船塢盡頭,縮起腳趾。那是二〇〇七年的初夏,水和天空一樣灰灰冷冷。我打算跳入水中,睪丸拚命往骨盆縮。咿,冷得發抖。手機在我皺巴巴的衣服旁響起。我彎腰接電話,心想會是很長的一通電話。是多倫多大學急診部主任。
「詹姆士,是我,邁克。歡迎從蘇丹回來。我聽說有一份工作是前往衣索比亞。」說不、說不、說不,我在腦海中重複道,接下來又想到,就在蘇丹旁。 風越來越強。
「詹姆士?」
我步出飛機,在入境海關前排隊,手上拿著衣索比亞簽證。有個人手上拿著標誌:「詹姆士醫生——多倫多。」陽光燦爛,空氣聞起來有家的味道。
雅克里路領我進入一處鐵皮屋,地上有人坐著或躺著。幾個學生靠在牆邊。檢傷分類站沒有護理師。
「我們明年就可以開始了。」畢魯克與蘇菲亞就著學習中心的黯淡燈光,上下摸索對方的喉嚨,學習若有人無法呼吸時,該從哪裡切開。娜桑寧與雪柔站在附近,點點頭或移動學生的手指。
「對,就是那邊,很好。」我回到多倫多市中心的急診室。有個人褲腳拉到膝蓋,因為他在雪地上睡著,雙腳凍傷發黑。一名女子在擔架床上,痛得翻來覆去。醫生從一處布簾後的病床走出,在燈光下舉著裝著脊髓液的透明小瓶。
我在城市間匆忙奔波,沒日沒夜,幾乎無暇反省或寫作。祖母已過世,祖父孤單一人。
我來到亞伯達省(Alberta)北部,坐在祖父廚房的桌邊,望向窗外。大雪紛飛,在這片宛如電視雪花雜訊的景色中,只能勉強看出森林。空蕩蕩的紅色蜂鳥餵食器在掛鉤上晃。松鼠經過餵食器,在歐洲酸櫻桃之間的枝枒間蹦跳,掀起的白色雲狀物飄落到地上。
隔壁房間傳來洗牌、豎起牌堆的聲音。他在玩接龍。暖爐隆隆作響,暖風吹到我頸背。聲音淹沒了他的遊戲。
他今年九十歲,慶祝過結婚六十七週年,也哀悼過妻子逝去。我來到他位於湖畔的家。他雖然身體日漸衰弱,仍努力維持這房子。我來到這裡照料他,同時向他學習,學著如何在埋葬了妻兒之後的人生盡頭自處。他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有智慧的一個。
我來到這裡,寫關於急診醫學,以及急診醫學的「理由」。我們竭盡所能,替陌生人再多爭取一分鐘、一天、一年。若我們從事這些事情時的背後法則是自然的,為什麼阿迪斯阿貝巴與多倫多會看起來如此不同?
昨天,祖父與我開車前往「陷阱之路」(trapline,註:設置陷阱的人放置陷阱的路線),那是他在七十年前,這塊土地初次立契轉讓時設立的。車子隆隆駛過攔畜溝柵,從空蕩蕩的碎石路彎進積滿雪的林間空地。他想檢查設陷阱者小屋,確保這裡的門沒被熊破壞闖入,並檢查陷阱。他設了三個,前兩個是空的,第三個則抓到漁貂,那是種類似狼獾的動物。牠皺著一張怪臉,身體在寒冷中變得僵硬。我把牠扔到卡車後方時,發出沉悶聲響。之後,祖父會將牠的皮剝下。
你生命和大地最接近的時候,是因為掉入陷阱、站在槍枝的錯誤方向,或躺在病床上慢慢消耗,總之是因為某種情況而了解到,你不必尋找死亡。死亡已在路上。
我常覺得自己接近死亡,因為我在急診室工作。我見過的死亡,都是在一樓急診室發生。布簾後的病床是生命最容易流進流出的地方,對病況最嚴重的人來說,有時一分鐘就攸關生死。
一、兩個月前,有個來自德國的學生前來急診室,學習急診醫療實務。他覺得這裡沒什麼好學。在值班前半段,他只為兩個病人看診。雖然急診室很忙,他卻在護理站後面看電郵。
我拍拍他肩膀,指著救護人員推過去的一個人。她很脆弱,床上的身軀弓成一個角度,幾個月來都沒離開那張床。她的呼吸又急又淺,雙眼緊閉。兩名救護員在彼此間拉開一張橘色毯子,把和氣球差不多輕的她移到空床上。護理師來到檢傷處,跟我說她的資訊。不接呼吸器、不要CPR,只要舒適治療(Comfort measures only)。
「看見六床的女士嗎?」
他點點頭。
「我想她很快就會死了,」我說。「你之前見過這情況嗎?」他搖頭。
「你該看看。」
他別開視線,把手機放進口袋。「我該去看看新進病患,」他說著就一堆病歷上拿走一份,走向另一張病床。
我讓他走。我應該更努力鼓勵他的。我想讓他看的,不光是她的故事在即將畫下句點時身體所出現的變化,心電圖從快而窄變得慢而寬,呼吸從淺的變成粗嘎,拉高,然後停止。這樣他未來才能認出需要他幫助的人最後發出的喘息。我還希望在她吐出最後半口氣之後的那一刻,他能在場,看看所有器官仍在——腎臟、 大腦、血液、甲狀腺素含量正常、溶鹽量也能精準測出。只不過,生命已經消失。
「那是什麼?」我會問。我會說,我也不知道,但這就是你來到這裡的原因。幫助它,無論那是什麼。之後我會教他我所知道的東西。先是呼吸道,接下來是呼吸。醫學就是能照顧自己的生命。對我來說,這是最了不起的故事。
「我什麼都做不好,」祖父今天早上跟我說。他在車門邊蹣跚行走,又揮掉我的手,搖搖晃晃在冰上行走。你明白,這就是他對「價值」的想法——有用。
此刻屋裡安安靜靜,只有背後時鐘的秒針傳來移動聲。沒有玩牌聲。我想,他應該和我一樣在看著雪,在等待。學不會這一點,就當不了優秀的獵人。
他話不多。我不確定何時會問他,接近人生終點時是怎麼回事。但沒有關係,他已在教我了。那和其他任何時間一樣。你在早上醒來,準備度過到來的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