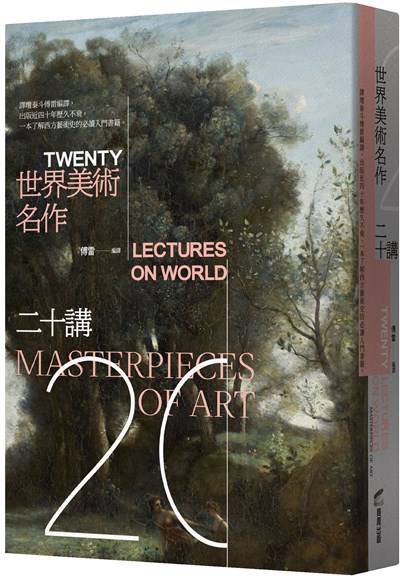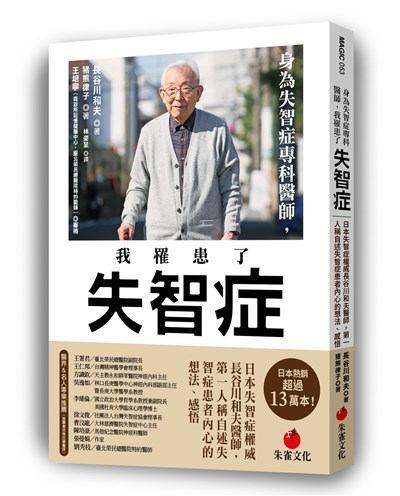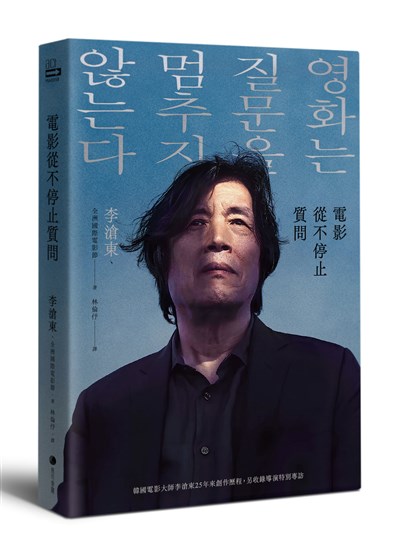阮義忠是四、五十年來台灣非常有名的攝影大師,《人與土地》、《台北謠言》是他二十幾年前為自己作品出版的兩本攝影文集,近年他重返這些照片至少二十五年前的拍攝地點,回想當年拍攝書中照片的背後故事,並撰寫專文,應邀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方都市報〉刊載,如今再出書,圖文相輔,影像更能震撼人心。
大約1970年代是台灣第二次鄉土文學發軔時期,文學創作透過文字重新找回台灣島嶼的內涵與本質,文化層面也有重視本土的傾向。但小說寫的再好,對現代年輕人卻缺乏影像感,攝影集就沒有這個問題。這兩本攝影集內的商店招牌、月台、天橋、上班族女性,現在看來很古老,當年卻是很前衛,年輕人看到會很有感受。
再如1988年台北東區一對情侶的照片,拍攝地點隔年即出現「錢櫃」KTV最老那一家店,1980年拍攝剛開幕兩年的芝麻百貨,後來變成中興百貨;讀者看到這裡,會明白攝影不需要文字,就可令人感受到時間流轉的傷感。國父紀念館佔有許多人的記憶一席之地,大家看到作者1974年二十幾歲時拍攝的國父紀念館照片,一定會牽引出自己的回憶,這就是《台北謠言》懷舊的魅力。
《人與土地》是作者走出台北拍攝的鄉土照,在1980年代還是荒山野嶺的台東、南澳、花蓮,他拍的老農、旗津沙灘酬神戲台、蘭嶼頭髮舞,已成為那個時代重要的人文記錄;1980年在嘉義梅山拍攝的出殯送葬隊伍,四個人用粗大的竹竿抬著木頭棺材,送上山的隊伍很長,他問是什麼山?對方竟答長白山,讀來別有氣味。作者這些年持續拍照,這兩本書的照片已成經典,加上專文解讀,更有價值了。
文章節錄
《人與土地+台北謠言攝影文集》
《人與土地 MAN AND LAND 1974-1986》
農婦的雕像
童年經歷如影隨形地伴隨著我成長,且往往突如其來地橫現眼前,甩也甩不掉。那天走在恆春鎮郊的龍泉里,沿途都聞到一股熟悉的味道。閉著眼也能分辨,那是被烈日烤得暖呼呼的地瓜葉、被地瓜汁液摻和的泥土。恍惚之間,我又成了九歲的小孩,打著赤腳走在老家通往菜園的小路上,心不甘情不願地想像著此時此刻同伴們正在看漫畫書、打彈子或是海邊戲耍的情景。若是在下個轉彎就看見當年那永遠不變的街景和面孔,我也不會吃驚。
路邊的矮樹叢後果然有片地瓜田,一位農婦獨自重複著同樣的動作:剷土、拔地瓜、抖泥土、割葉藤。每個步驟都是再熟悉不過的;我心裡有數,好照片正等著我去把它定影。
攝影有時不光是記錄,還是期待與等候,期待氣氛出現、等候事件發生。人物入鏡後,要沈住氣,凝神守候最佳動作與表情出現。完美狀況存在於不完美的隙縫之中,只對心有祈求的人發出召喚。類似的場景、一模一樣的農事,現在的我卻已是遠離家鄉的攝影工作者。埋怨與抗拒已被理解與敬佩取代;在平凡人身上捕捉不凡的氣質,也成為我百拍不膩的題材。
這位體型結實,樣貌樸素的農婦是否能拍成令人景仰的雕像呢?我用仰角拍,盡可能地降低身體高度,直到不得不趴在地上,才框取到了理想的畫面。一位天地之間的勞動母親在我的相機裡曝了光。而沾了一身泥土與葉汁的我,也踏踏實實地貼近了土地。
澳花的三代同洗
三代同洗,可能會被認為是筆誤,但我實在找不到更恰當的詞了。婆婆、媳婦、孫子,三人在清冷的冬晨來到溪澗洗衣洗澡。家裡的男人酒醉未歸或宿醉未醒,沒人在意也無人追究,酗酒一直是原住民無法戒除,也不想抗拒的陋習。
澳花村原是宜蘭縣南澳鄉的七個村子中,人口最密集的。早年蘇花公路以此為中繼站,形成市集,吸引了不少人口。後來路基經常崩塌,公路改道後,就幾乎沒外人造訪了。
我執意來此,是因為其他六村都陸續造訪過了,唯獨澳花躲在雲深不知處。問過幾位鄉民,都是這麼回答:「很遠啦,我也好久沒去了。去那裡幹嘛?沒人做生意,吃住都成問題,路況又差,很容易把車子搞壞!」直到一位在鄉公所任職的友人告訴我:「阿將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食宿都會替你安排。他是澳花的奇人,不但會武功,還會畫畫、棋術、古箏、吹簫⋯⋯連我也搞不清他到底會多少玩意兒!」
果然,在相處的那兩天,阿將隨時都有新把戲。一會兒摘下一片樹葉,湊在唇邊吹流行歌;一會兒替我排八字、算命。妙的是,他根本不是泰雅族人,而是從小就隨家人移居至此的平地人,和山地孩子一起打滾長大。多才多藝的他儼然成了偏僻小村的領袖人物,村民們喝酒打架,頭一個就是找他調解。熱心過頭的阿將,幾乎也要變成我的領導了,頻頻暗示什麼才比較值得採訪,我只有盡量找機會自行外出蹓躂。這三代同洗的畫面,就是我第二天起個大早,趁阿將還在鼾聲大作時出外找到的寶。
雖是剛入冬,深山的朝露已讓我凍得直打哆嗦。溪水寒到刺骨,這一家三代的泰雅族老小卻在湍湍急流中洗衣兼洗澡,自由自在地與大自然合而為一。澳花多奇人嗎?在他們看來,說不定奇的倒是我了。
《台北謠言 TAIPEI RUMOR 1975-1988》
囚禁不住的夢
這是為一篇文章配圖的意外所得。任職於《家庭月刊》時,有位同仁作了篇關於公園老人樂隊的報導,我負責拍照。有趣的是,這些年紀都上八旬的鄉親,天天聚會的場所卻叫「青年公園」。年輕人只愛往時髦場所跑,為新生代設想的這片綠地,倒反而盡是蒼蒼白髮。依稀記得,拉二胡的那位長者造詣頗精,另外一位吹笛、品簫、奏把烏都能來兩下,彈中阮和琵琶的則是位老太太,其他人就記不得了。
老人樂隊的團員來自本島各鄉鎮,其中兩位還是原籍大陸的退伍老兵。寄居在水泥叢林中的他們雖都離開了家鄉,卻能藉著音樂相聚,合奏出一闋闋「思鄉曲」。
樂音暫歇,天才全白,大多數的市民還在夢鄉。不遠處的兒童遊樂場,一個腳趿拖鞋的中年人以四十五度角的姿勢斜躺在溜滑筒中,衣著並不邋遢,也許只是喝醉了不想回家。然而,沈睡場所的奇特,也使他看起來好似自我囚禁,毫無席地而眠、露天而宿的瀟灑自在。
人無論在何處,會被困住的只是身軀,夢是囚禁不住的。只不過,心門一關,天地無光,即使有家也無歸處。他的睡相令我格外珍惜前一刻所見。那些精神奕奕的樂團老人,雖然歷盡滄桑,卻個個依然有夢,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心的歸宿。
八又二分之一和一又二分之一
費里尼的電影《八又二分之一》像部天書,看不懂的人也不敢批評,大家都被大導演天馬行空的敘述給迷惑了。主角不折不扣是費里尼本人的投影,希望在現實人生和夢境世界的混沌交界找到出路。看這部片子時我剛讀高一,羅東鎮上的小戲院聲光效果不好,看得我一頭霧水,只覺得過去、現在、未來全給攪混了。
儘管如此,很多畫面依舊深印在腦海裡,彷彿是往事的一部分。我在二十歲前寫過五篇短篇小說,處女作取名〈一又二分之一〉正是借自費大師。主角A君和B君先後出現在看似獨立、實則串連的兩個故事當中。A君在每天必走的路上發現了一些祕密:路的長度、紅綠燈的轉換、步伐的跨距、擦身而過的路人、店舖所放的音樂⋯⋯都似乎與自己有某種關聯。總之,一個無名小卒漸漸認為自己是個負有特殊使命的非凡人物,只是沒人明白而已。
剛到台北上班時,除了《幼獅文藝》的辦公室之外,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西寧南路一條巷子裡的「天琴廳」。只要一杯茶資就可占用一組舒適的沙發與茶几,從開門混到打烊,在人進人出、聲音吵雜的環境裡享受自己才懂的寂靜,畫了無數插圖,也完成了那篇處女作。
接觸攝影之後,我不再畫畫和寫小說,「天琴廳」也被行醫的屋主收回當診所。我在原址外頭所拍的這幕人流景象,就像是〈一又二分之一〉的插圖,雖然另外那位主角B君的遭遇,我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