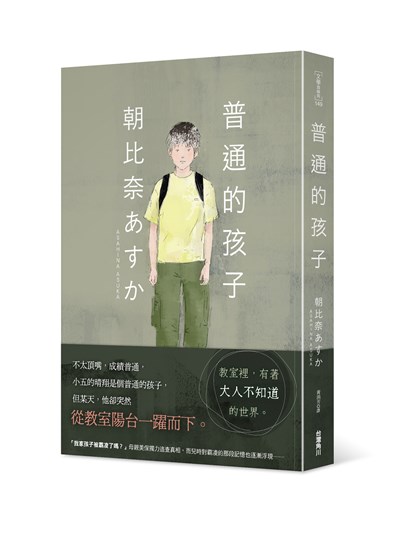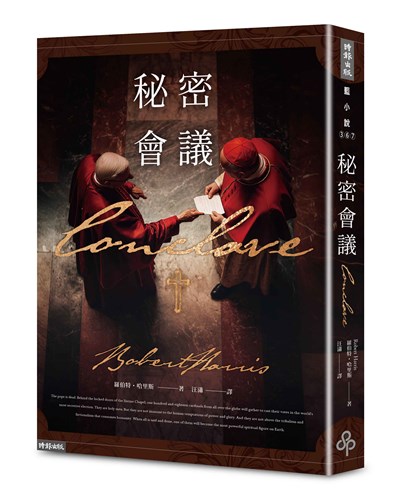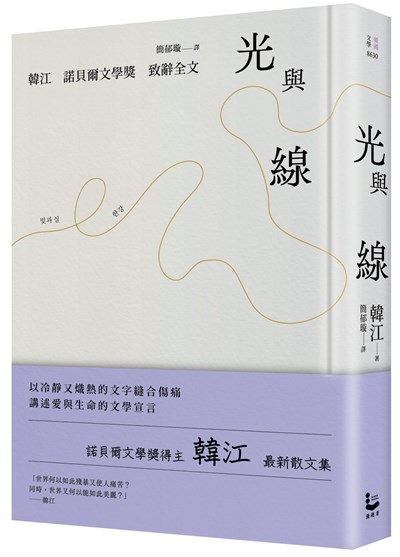被譽為「龐克教母」與「龐克搖滾桂冠詩人」的女歌手佩蒂‧史密斯,與已故攝影家羅柏‧梅普索普曾是情人,後來成為終生好友。羅柏1989年去世前,她承諾要寫書紀念,但痛失摯友,使她難以下筆,直到2000年才動筆,歷經十年寫成《只是孩子》一書,記錄兩位藝術家攜手走向創作巔峰的故事。
羅柏原想當畫家,後來成為攝影家,作品廣被全球美術館收藏。佩蒂想當詩人,卻變成知名搖滾歌手與畫家,獲得法國文化部頒授藝術終生成就獎,也名列百位搖滾重要人物名單與搖滾名人堂。兩人的藝術成就很高。佩蒂本質為詩人,文筆極佳,這本回憶錄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殊榮。
兩人二十歲時認識,之後二十餘年為藝術奮鬥,面對主流社會的不友善而跌跌撞撞,但未被打倒,終獲肯定。羅柏的男男黑白情色照片在國家畫廊展出時,引起爭議,美國國會還大肆批評,佩蒂則把爭議背後、羅柏內心最柔軟的部分寫了出來。
兩人曾在紐約街頭嘻鬧,一旁的老人看到他們說「Just Kids!」(只是孩子)選為書名,呼應兩人從未長大。羅柏的成長故事,兩位藝術家經歷的挑戰、挫折的磨練,仍然能夠不長大,實屬難得,也紀念這份值得珍惜的情感。
文章節錄
羅柏向我保證他會把這裡弄成一個像樣的家,他說到做到,辛苦地改造著房子。第一件事,就是用鋼刷刷洗結了硬塊的烤箱。然後打蠟,擦窗玻璃,還把牆也刷白了。
我們不多的財產悉數堆在未來臥室的中央,我們穿著外衣睡覺。到了撿破爛之夜,就上街搜尋需要的東西,神奇的是竟然都能找到。在路燈下,我們找到一張廢棄床墊、一個小書架、修一修就能用的燈、陶碗、裝在破裂卻華美相框裡的耶穌和聖母像;一塊破舊的小波斯地毯,正好搭配我的那一角小天地。
我拿烹飪用的蘇打粉擦洗床墊。羅柏幫燈具重新裝上電線,扣上羊皮紙燈罩,還在上面畫了他自己設計的圖樣。他的手很巧,畢竟是為媽媽做過首飾的孩子。他花了幾天時間新串了一副珠簾,把它掛在臥室入口處。一開始我對這珠簾還抱持懷疑,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東西,不過它最終與我的吉普賽元素相得益彰。
我回南澤西一趟,把我的書和衣服都帶了回來。我不在的時候,羅柏掛起他的素描,還用印度布料遮住牆壁。他用宗教手工藝品、蠟燭和亡靈節的紀念品布置了壁爐臺,把它們擺得就像祭壇上的聖物。最後他用一張小工作臺和毛邊的神奇毯子為我布置了一個讀書區。
我們把各自的物品收在一起,我僅有的幾張唱片和他的一起放進木箱,我冬天穿的大衣掛在他的羊皮背心旁。
弟弟幫我們的唱機換了一枚新唱針,母親做了肉餅三明治包在錫鉑紙裡。我們一邊吃,一邊開心地聽著爵士歌手提姆.哈定(Tim Hardin)的歌聲,他的歌變成了我們的歌,好像唱頌著我們年輕的愛情。母親還寄來一個包裹,裡面有床單和枕頭套。好熟悉好柔軟,散發著一種使用了多年的光澤。它們使我想念起她,想念她站在院子裡,滿意地看著洗淨的衣服晾在繩子上、在陽光下飄舞的樣子。
我的寶貝收藏跟待洗衣物混在一堆。我的工作區亂堆著手稿、散發著黴味的古典文學、破玩具和護身符。我把韓波、巴布.狄倫、洛特.蘭雅(Lotte Lenya)、皮雅芙(Edith Piaf)、惹內(Jean Genet)和約翰.藍儂的圖片釘在一張臨時小桌上,上面還擺著羽毛筆、墨水瓶和筆記本—我清貧的雜亂。
來紐約的時候,我帶了些彩色鉛筆和一塊用來畫畫的木框畫板。我畫過一個坐在桌邊的女孩,面對著一副攤開的紙牌,正在體悟她的人生。這是我唯一想讓羅柏看的畫,他非常喜歡。他想讓我體會用好的紙和筆作畫,讓我分享他的畫具。我們能並肩畫上幾個小時,兩人都很全神貫注。
我們沒什麼錢,但過得很開心。羅柏兼差之外還負責整理房子。我洗衣、做飯,飯吃得很拮据。我們經常去韋弗利大道盡頭的一家義大利麵包店,買一條隔夜麵包,或者四分之一磅因不夠新鮮而半價賣的餅乾。羅柏愛吃甜的,所以獲選的常常是餅乾。有時候櫃臺的女士會多給我們一些,餅乾塞滿了邊緣有著黃綠兩色彩焰的牛皮紙袋,她還會搖著頭,喃喃地對我們表達善意的不滿;她大概猜得到這就是我們的晚飯了。我們還會外帶咖啡和一紙盒牛奶。羅柏最喜歡巧克力牛奶,但那個更貴,對於要不要多花那十分錢,我們會考慮再三。
我們擁有作品,我們擁有彼此。我們沒錢去聽音樂會、看電影或買新唱片,但會把已有的唱片聽上一遍又一遍。我們聽了我的《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艾蓮諾.斯蒂伯(Eleanor Steber)唱的,還有《至高無上的愛》、滾石合唱團的專輯《按鈕之間》(Between the Buttons)、瓊.拜雅(Joan Baez)和巴布.狄倫的專輯《金髮疊金髮》(Blònde On Bloned)。羅柏也把他最喜歡的香草軟糖樂團(Vanilla Fudge)、提姆.巴克利(Tim Buckley)和提姆.哈定介紹給我,還有他的《摩城紀事》(History of Motown)也成為了我們快樂共用的夜晚背景音樂。
一個乾燥溫暖的秋日,我們穿上了自己最得意的行頭:我的是垮掉派涼鞋和破披巾,羅柏戴著他最愛的珠串,穿著羊皮背心。我們坐地鐵到第4街西,在華盛頓廣場待了一個下午。一起喝著保溫瓶裡的咖啡,看著如織的遊客、癮君子和民謠歌手。激動的革命者散發著反戰傳單,下西洋棋的人也有他們自己的觀眾。語言的衝突、手鼓的敲擊和狗吠聲交織出持續的嗡嗡聲,大家都融合在這一時地裡。
我們朝噴泉走去,那邊是熱鬧的中心,一對老夫婦停下腳步,毫不掩飾地盯著我們。羅柏很高興有人注意他,深情地握緊了我的手。
「哦!把他們拍下來。」女人對一臉不解的丈夫說:「我覺得這兩個人是藝術家。」
「哦!算了吧,」丈夫聳了聳肩:「他們只是孩子。」
樹葉轉成深紅和金黃的季節。柯林頓大道上,棕色磚房的門廊前擺著刻出花樣的南瓜頭。
我們在夜裡散步。有時能看到天上的金星,它是牧羊人之星,也是愛之星。羅柏稱它為「我們的藍星」。他練習簽名時把「羅柏」的字母t寫成一顆星星的形狀,且特別用藍色筆,這樣我就能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