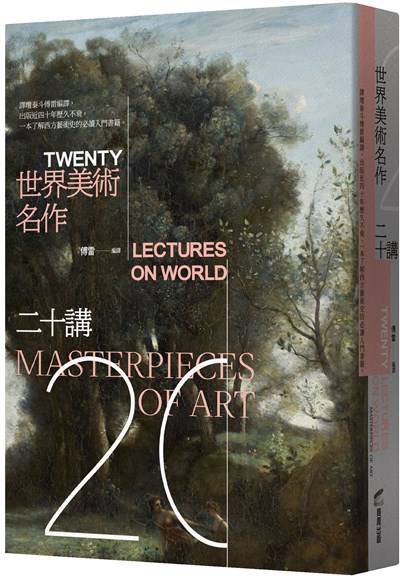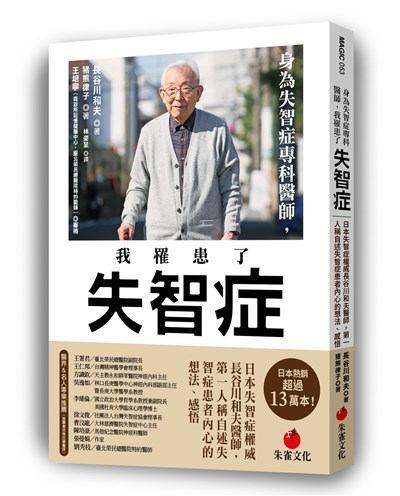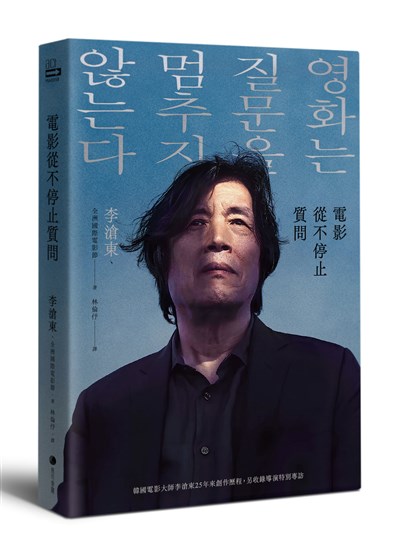薩依德運用對西方文學的理解,卻建構了尖銳嚴厲批判西方帝國主義的「東方主義論」,他成為80年代多元文化陣營的標竿旗手,然而同時他又是個純西方式古典音樂的熱愛者。他當然沒有採取粗魯的身份論、立場論來看待古典音樂,將古典音樂視為貴族文化或資產階級文化的代表。但他也不可能採取天真、單純,「就音樂論音樂」的樂評態度,在老牌左派刊物上寫古典音樂。薩依德找出的一條中間、超越的觀念路線,是去解釋、辨認古典音樂內部的真與假、核心與邊緣。
《音樂的極境》書中的文章,是在薩依德去世後才收集的,薩依德本人來不及進行真正的整理工作,因而各篇之間有許多重複的地方。不過透過這些重複,我們可以更清楚看出薩依德與音樂之間的個人關係與偏見偏好。
任何一個愛樂者都不可能全盤同意薩依德的偏好偏見,然而,通讀全書,至少有一件事是明顯明確的,那就是薩依德堅持:即使在資本、商業體系層層包圍箝制下,古典音樂仍然有其可以拿來表達生命真情的空間,音樂家必須努力尋求呈現不被體制異化、不淪為人云亦云的音樂思考的方式,唯有如此的音樂,才能真正與聽者溝通,也才能贏得尊重。
這樣的價值態度,和薩依德對於音樂內在精神的細膩認真挖掘緊密相連。這是薩依德最珍貴的生命教訓,也是這本書能夠給讀者帶來最多思考與感情判斷的關鍵素質。
文章節錄
瑪麗安.薩
在他第一本以音樂為主題的著作《音樂的闡釋》(Musical Elaborations)的導論裡,愛德華說,他「[在音樂上]的首要興趣是,將西方古典音樂視為對[他]作為文學批評家、作為音樂家都有重大意義的文化領域」。我自己呢,視他這個興趣和他對音樂的關係為一個生生不息、變動不居的現象,其起源有強烈的個人因素。
在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裡,愛德華描述他對音樂的感受。對他,「一方面,音樂是令我非常不滿意又無聊的鋼琴練習……另一方面,音樂對我是一個極為豐富,由輝煌的聲音與物象隨機組織而成的世界」。愛德華經由他雙親收藏的大量唱片,以及每星期六晚上收聽BBC電台廣播的《歌劇之夜》(Nights at the Opera),發現這個世界。
西方古典音樂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愛德華工作時聽音樂,休息或需要鬆弛身心時彈鋼琴;他的休閒閱讀包括大量音樂方面的論著。他音樂知識淵博,兼有一圈密友,若非像他一樣熱愛音樂的知識分子,就是音樂迷。他各種著述隨手援引音樂為例或音樂內容為證,但我相信是1982年顧爾德(Glenn Gould)去世,促使愛德華認真為文談音樂。顧爾德英年早逝而結束一位鋼琴奇才的輝煌生涯,愛德華深有所悟而不得已於言,於是深入探索顧爾德的生平音樂成就。他盡情聆聽他拿得到的每一件顧爾德錄音,閱讀所有關於顧爾德的文字,以及顧爾德自己的文章。他看所有關於顧爾德的影片。顧爾德變成愛德華的執念,他放不開他所愛的這位天才。
1983年1月,也就是顧爾德去世後數月,我們的兒子瓦迪發生非常事故,對我們這個家庭,那是很恐怖地和死神擦肩而過。我們得知瓦迪嚴重感染而需要住院那天,我嚇得全身癱瘓。愛德華承受了那個消息,半小時後,說我們既然有當晚音樂會的票,應該準備出門了。我留在家裡,既害怕,又困惑,愛德華去了音樂會。多年後,我才明白,他面對死亡的恐懼時,尋求音樂對他多麼重要。
瓦迪住院期間,愛德華得知他母親診斷罹癌,非手術不可。在他腦子裡,音樂和他母親是連在一起的,因為母子倆有那麼多共通的音樂體驗。在《音樂的闡釋》裡,他寫說「我對音樂的最早興趣,要歸源於我母親美妙的音樂性和對這門藝術的愛」。1983年5月,這本集子的第一篇文章問世,主題是顧爾德。1986年,愛德華成為The Nation雜誌的樂評家,從那時開始,音樂研究和他個人對音樂的熱愛融合為一。他開始大量收集同一首協奏曲、交響曲和同一部歌劇等音樂作品的不同錄音。他不惜時間聆聽這些錄音,並且在大西洋兩岸聽歌劇、獨奏會、音樂會,能聽幾場,就盡量聽幾場。音樂裡變化多端的主題和音樂結構上的複雜性,彷彿與他掙扎面對他母親的疾恙和去世連在一起。這段時期,我們全家開車從紐約前往華府地區探望他母親。愛德華平常在漫長的車程裡堅持聊天,這時卻帶著滿滿一帆布袋的卡式錄音帶,擺在前座我的腳邊。我有異議,他就覺得受傷。華格納的《指環》成為我們五小時車程的旅伴。孩子坐在後座,兩個都戴耳機聽他們的音樂。其情其景簡直超現實。然後,我恍然大悟,愛德華因應母親重病及不久人世之痛的唯一途徑,是把自己淹沒在宏壯美麗的音樂裡──回憶他童年和她的共同體驗。愛德華的母親於1990年辭世。《音樂的闡釋》1991年出版,題獻給她。
愛德華的母親去世一年後,他被診斷得血癌。音樂成為他寸步不離的伴侶。1998年夏天,他必須接受一場嚴酷可怕的實驗治療,當時正值海力克(Christopher Herrick)排定以十四場音樂會演奏巴哈的管風琴作品。愛德華安排治療日錯開那些音樂會。他不但所有十四場都到,還寫了一篇評論,也收在這本書裡。
同時,愛德華探索「晚期風格」論。他判定,作曲家人生尾聲所寫的作品,特徵是「頑固、難懂,以及充滿未解決的矛盾」,這些思維演化成他另一本書《論晚期風格》(On Late Style),全書觸及多位作曲家的晚期作品。在《鄉關何處》記述童年音樂體驗的章節中,愛德華描寫他從這些體驗裡獲得的樂趣,加上他所聆聽的所有作品的細節,以及他的興趣與好奇心如何引領他學習,而對這些作品和演出它們的藝術家所知愈來愈多。他在開羅親見福特萬格勒指揮。在一長段以福特萬格勒為主題的反思之後,愛德華寫了一句「時間似乎永遠跟我作對」,並且由此導出長長一段將音樂和時間連在一起的文字。時間向來令愛德華縈心---它的稍縱即逝、它無情的前進,以及它繼續存在而向你挑戰,看你能不能完成重要的事情。在他心目中,音樂也占據這個世界。這個集子的最後一篇文章,評索羅門(Maynard Solomon)那本談晚期貝多芬的大著,2003年9月刊出,距愛德華去世前兩周,標題「不合時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ions)有如讖語。
2003年6月初,愛德華辭世前三個月,他打電話給他當長老會牧師的表兄弟,請教「時候將到,現在就是了」語出《聖經》何處。問題獲答時,愛德華放下電話,轉臉向我,說擔心我不曉得他喪禮該奏什麼音樂。我吃一驚,片刻才答出話來,因為我恍悟他正在告訴我,這是結束的開始,他要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