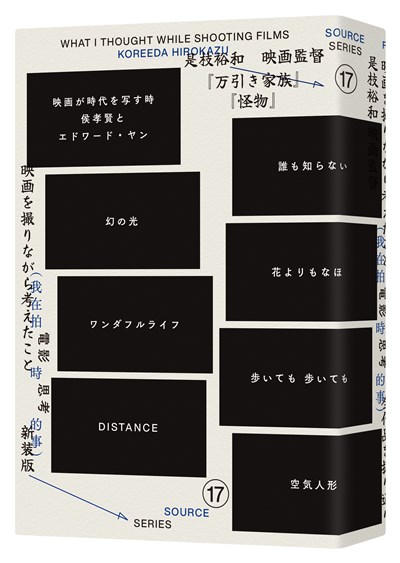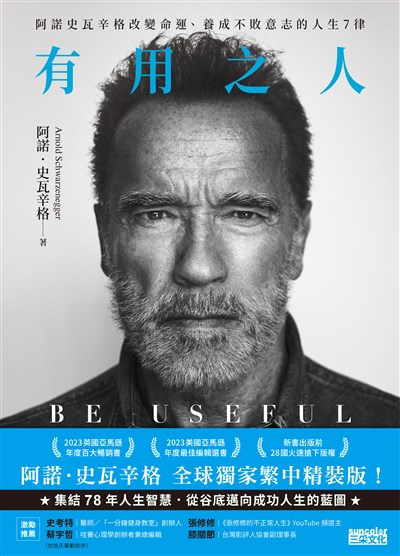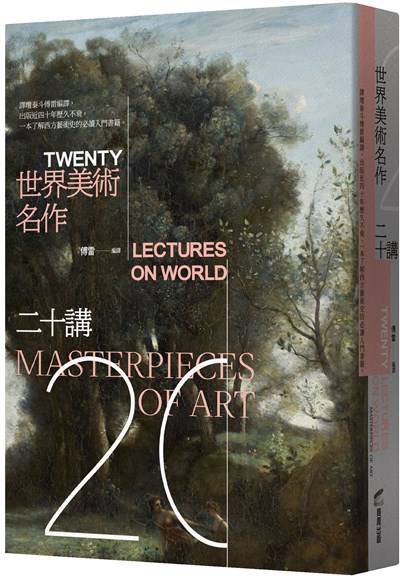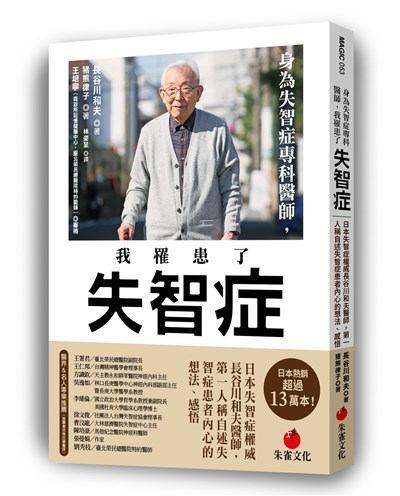瑞士旅行文學傳奇作家尼可拉•布維耶成名傑作,以無窮妙筆搭配風味十足的黑白插圖,於六○年代出版後,便成為半世紀以來代代旅者必定隨身的天涯行腳聖經。書中記錄了作者與繪者兩人從瑞士出發,一路馳騁土耳其高原、遠及阿富汗荒漠大地的不朽壯遊。文采收放有致,精準還原了旅人眼前所見的「即時場景」:人聲物響、氣吁膚觸、事相物徵、風俗儀規、天地光影,分毫畢現,無所遁於筆下,將遊記的散述漫錄之風,昇華至永恆的文學高度。它是繁體書市缺席多年的夢幻逸品,將為慣讀英美旅行文學的讀者開啟一方黃金珍寶般的「遊記新世界」。人在路上,就要懂得「使用」這個世界。而《世界之用》會把竅門送給你。
文章節錄
《世界之用》
【1】
手頭上的錢足夠生活九個禮拜。錢的數目不多,不過要撐的時間相當長。所以我們拒絕享受任何奢侈,只有一個例外,而且是最寶貴的一個:慢活。打開車頂蓬,輕輕拉出手動風門,靠上椅背,一隻腳擱上方向盤,我們以二十公里時速悠哉遊哉地穿行在沿途的風景中(這裡的風景有個好處:它不會無預警地發生變化)。我們也像這樣安靜地馳騁在月圓的夜色中,欣賞精采紛呈的景致:螢火蟲漫天飛舞;養路工人穿著皮拖鞋工作;簡樸的村莊舞會在三棵楊樹下舉行;平靜的河流邊,渡船船夫還在沉睡。在萬籟俱寂的時刻,連按一聲喇叭都會讓自己嚇一跳。然後太陽升起,時間開始變得緩慢。我們抽了太多菸,雖然肚子很餓,不過一路經過的雜貨店都還大門深鎖,我們只好拿一塊從後車廂深處的工具堆裡翻找出來的麵包,細嚼慢嚥地解饞,不敢一下全部吞下肚。八點鐘左右,太陽開始發威,我們經過小村子時,必須睜大眼睛,因為總有些頭上戴著警察那種帽子的老頭被曬得頭昏眼花,在車子快開到他們前面時忽然笨拙地大步一跳,打算就這樣橫越馬路。快到中午時,煞車、引擎和我們的腦袋瓜都已經發燙。所幸無論周遭風景多麼荒涼,總是找得到一小片柳樹林,讓我們把雙手往後腦一枕,好好睡上一覺。
或者找到某處旅店休息。想像一下前廳的情景:凸起的牆壁,扯裂的窗簾,地窖般的陰冷;嗆鼻的洋蔥氣味中,蒼蠅嗡嗡作響,四處亂飛。一整天的旅途在這裡有了繫泊的所在;我們把手肘撐在桌上,盤點先前發生的事,彼此訴說一整個上午的經歷,彷彿各自有過不同的體驗。當天散布在千畝田野、萬頃鄉間的喜怒哀樂,濃縮在我們最先啜飲的幾口美酒、信筆塗鴉的桌布、暢快吐露的話語中。情感宣洩彷彿唾液分泌,與強烈的食欲相伴而生,足以證明在旅行生活中,身體的糧食與精神食糧休戚相關,緊密得難以分辨。大啖美味羊肉,構思奇異旅程;品嘗土耳其咖啡,咀嚼無盡回憶。
一天的時間在寧靜中邁入尾聲。用午餐時,我們已經暢所欲言。在鳴唱的引擎與不斷掠過的風景承載下,旅行的泉流貫穿身心,使思緒益發明晰。某些過去無端留置於腦海的想法離你而去;反之,其他一些想法如同湍流中的滾石,會自然調整、為你整頓成形。完全不需要介入;公路會主動為你效力。我們真希望它就這樣恪盡職守,不斷往前延展;不但延伸到印度的盡頭,還繼續伸向更遠的地方,一路延伸到生命結束。
旅行歸來以後,很多沒有動身旅行的人會來告訴我,只要專注思索、發揮一些想像,他們屁股不必離座,也能暢快旅行。我很樂意相信他們。他們必然是箇中強者,但我不是。我太需要「在空間中移動」這種具體的輔助。而且幸運的是,世界為我這種「弱者」開展廣袤的空間,張臂接納他們。而當這個世界,像某些夜裡馳騁在馬其頓的公路上那樣,月亮垂掛在左手邊,銀光粼粼的摩拉瓦河在右手邊奔流,還有滿心的憧憬催促我們奔向地平線彼方,尋找可供度過往後三個星期的村莊,這時我會不禁慶幸自己離不開這樣的世界。
【2】
還有,為什麼堅持要談這場旅行?跟我現在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完全沒有,而且我已經沒有什麼現在可言了。紙張越積越多,我耗掉一些人家給我的錢,我對我太太來說幾乎是個死人,她到現在還沒丟下鑰匙棄我而去,已經是非常厚道了。我從貧瘠不堪的幻想演變成恐慌,既放不下,又受不了,不肯動手做其他任何事,因為害怕損及這篇急於將我吞噬、但本身卻不見豐美的虛幻敘事,而有些人不時還會向我探聽進度,急切的口吻中逐漸開始顯出幾分嘲諷。要是我能一次就把我所有的血肉給它,讓它當場完成,那該有多好!可是這種輸血是不可能的,而我很清楚,承受和忍耐的能力永遠不可能取代發明的神功。(忍耐力──這玩意我倒多得超乎所需;算是眾仙女賜予的薄禮。)不可能;只能透過循序漸進、積少成多、持之以恆、鑽研因果。於是,必須回到異教徒的城堡,回到那個記憶的黑洞,回到那片黃色黏土山坡──儘管只見它已化成一片晦暗、一陣微弱回音、一堆每當我試著縫綴就立刻鬆散掉落的思想碎布──回到那個辛苦而幸福、讓我感覺生命的走向如此清晰的秋天;找回那些織綴在山丘頂上的法國人──如此活躍而忙碌,如此盛情地歡迎我,讓我發現一個全新世界,用他們的漁獵所獲滋養嗷嗷待哺的我。回到那裡;更重要的是:開挖這層厚得可怕、將我跟那一切隔絕開來的泥土。(這何嘗不是一種考古!每個人都有他的破片和殘跡,但當過去消散時,那永遠是同樣的災難。)設法鑽透這片亟於廢除、毀容、泯滅的漠然,尋回當時的充沛活力、靈動思維、柔軟彈性、細膩層次、生命波光,那些豐饒的偶然,那些墜入耳中的音樂、那種與事物之間的珍貴默契,以及人在其中感受到的那份極致喜樂。
若非如此,就只能屈就於:我的頭腦已經變成的這片荒漠;記憶寂靜無聲的侵蝕;這個無休無止、令我無法對任何其他事物(甚至包括我內心最幽微的那個聲音)付出關注的無謂消遣;這份強加於自身、但卻不過是個謊言的孤獨;這些似有卻無的陪伴;這個已不再是工作的工作;以及這些已從基底開始乾枯的記憶──彷彿某個法力無邊的惡靈已經斬斷它們的根鬚,斬斷我與如此眾多美好事物的連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