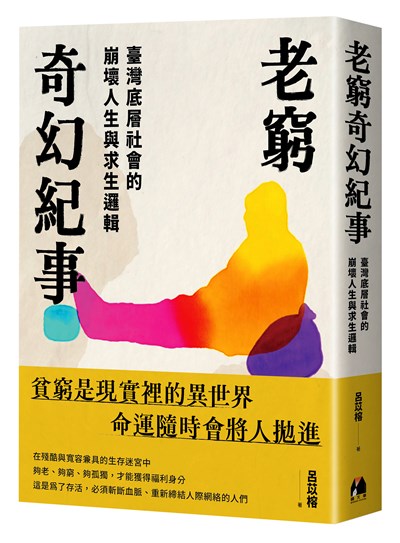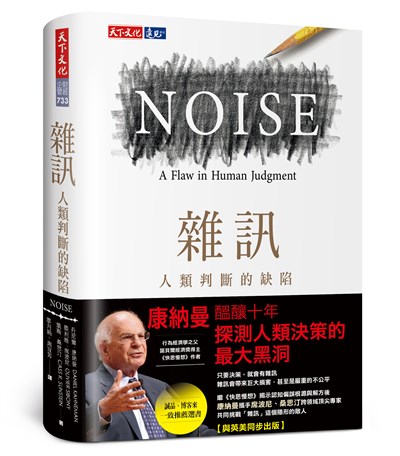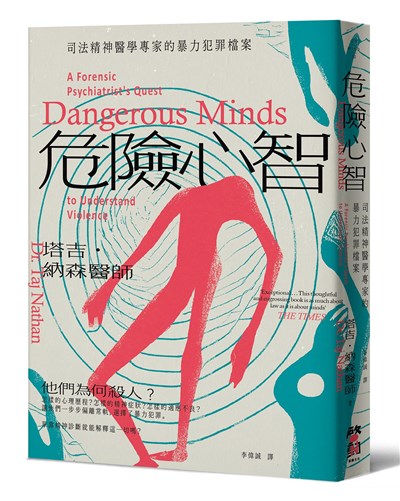一本「新南向政策」的文化人類學背景讀本。在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背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他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他衝破身分與國族的界線,正視存在於我們和它們之間的刻板印象與偏見,讓我們重新認識長久以來被歸類於「外籍」與「陌生」的世界 。本書為2017全新修訂版。
文章節錄
《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
印尼.模糊的他者
如同每個發展中國家的首都樣貌,雅加達有高聳的大樓觀景塔,也有著讓高級轎車能堂而皇之地擺飾在大廳的高級百貨公司,強烈的冷氣宣告這棟大樓正處在赤道帶的「北極」,以至於我們只能捧著熱咖啡抖縮著在星巴克取暖──這是個產咖啡的國家,我們手裡的咖啡卻來自千里之外的非洲大陸,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百貨公司旁的高架橋在日落時分排滿了車,車燈炫出澄黃,此區的豪宅別墅都透著光,聽說那裡大多住著有錢的華人。
這是個魔幻時刻,差點讓我們遺忘早先頂著赤陽,經過城市貧民窟心頭那一凜,也將碼頭的冷清蕭條拋在腦後。雅加達城郊的碼頭,曾經是殖民者運送香料咖啡和資源的出入口,一度熱鬧而喧嘩,如今鏽黃的貨輪無所事事地靠著岸,如同不遠處鐵道上躺著一排的那些工人一般,等候著活兒。「他們如果等到工作,一天可以拿到八十元台幣的收入。」途徑此地時,我們的司機Buddy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在鐵道旁睡了又睡,可能也無法賺到那八十塊。之後,我們在火車經過的鐵道上,看著那些擠身在車廂旁或發呆或吸菸或抱著孩子的臉孔,我不免想起故鄉火車站前那些聚集著的「外勞」,卻記不起他們的表情,此刻,我方能體會不惜離家遠走,到異鄉掙得一份工,是不得不然。
──
「你要小心他們。」婦人將頭從掛滿洗髮粉和料理包的小攤口探出來,朝背包客棧門口的幾個男人比一比,悄聲對我說。我們剛走出萬隆車站,將行李放進背包客棧,便急著出來買香菸,我沒有聽到華語的心裡準備,突然被這句不標準的華語驚嚇到,愣了幾秒,回問她原因,「因為,印尼人很壞。」這個婦人將菸和這個答案遞給我後,取走放在檯上的錢,頭便收回去了。
這個賣香菸的婦人是我在印尼遇到的第一個華人,不知幸或不幸,她也成為第一個傳遞恐懼給我的當地人。她的善意提醒對我來說卻成了困惑:「她難道不也是印尼人嗎?」或許她在對我說華語的那一刻,便把我當成「我們」,而她口裡的印尼人,就是我們之間共同的「他者」。
此時是梅嘉瓦蒂當政末期,離一九九五年發生的排華暴動還不到十年之遠,街頭不時流洩出華語流行歌曲和節目,華語學習熱也當頭,反華氣氛明顯下降,只是,陰影和驚駭仍瀰漫在華人社群之間,我在印尼旅行期間,不論到哪個城市,總有華人店家警告我:「別和印尼人打交道,他們很壞。」
印尼首次排華,起於一九六五年,當時蘇卡諾的親信策動政變,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組織軍隊平息動亂,但也順勢推翻親共的蘇卡諾政權,隨後又展開「反共大清洗」。蘇哈托政權指控華人社群中隱藏著心懷中國的共產黨員,排華運動於是開始。
但距離我們最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暴動」,當時有諸多華裔婦女被凌辱,華人商店被砸毀焚燒,生命財產被威脅。蘇哈托也因此事步下政壇,結束他三十一年的統治。排華,發生在他接掌權力開始,也是讓他走下權力的終途。
蘇哈托的排華,源於政治,終於經濟。在他任內那段「新秩序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九八),給予華人擴展國家經濟和財富的特權,卻也同時將他們推到政治、文化和社會上的邊緣:華人不具公民權,即使擁有公民權,也無法和其他族群享同等待遇,甚至被迫改名換姓,不可組織團體和媒體,不能加入軍隊和公務員之列,連唯一的華文報紙都是印尼軍方控制,華人只能當翻譯。華裔學者雲昌耀便曾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一書中提到:「由於華人擁有薄弱的政治基礎且處於易受傷害的地位,允許他們主宰經濟並不會對軍事統治構成政治上的威脅。」然而,正是因為一小群華人財閥與當權者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金融風暴發生後,蘇哈托政府將責任推給這群華人,所有華人因此共同承受貧富不均的惡果。
印尼人口超過兩億四千萬,族群數量也多於三百個,其中以占約四成多的爪哇為最大族群,華人只占百分之二到三。因為族群數量龐大,這個國家獨立建國之初,便以多元文化原則來統一二十七個省的大小島群,不論先來後到,都被視為是具有本土性的「土著」(印尼語:asli),也被認可為原住民(印尼語pribumi,亦即「土地之子」),但那些即便十七世紀便已移入的華人,卻始終被視為「外來者」(asing)。
華人和原住民之間那條不可抹滅的邊界線,早從荷蘭殖民時期刻下,當時的殖民者在印尼群島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將所有族群分為:屬於上層的歐洲人,位在中層的外來東方人,以及底層的土著。當時華人獨占經營不道德性商業活動的特權,因而造成長久以來印尼其他族群對華人控制經濟的刻板印象。然而,為了扭轉族群結構,一九○○年起,荷蘭人實行「土著改良政策」,向華人抽稅,還限制其居住通行,華人地位因此改變,他們於是認清唯有鞏固自我才能得到「他者」尊重。
不論政治如何變動,印尼華人在歷史洪流中,始終被強綁在一個邊緣位置。「華人是來自印尼邊界外的土地」一直是印尼社會中無法扭轉的印象偏見,在蘇哈托時期便流行著「華人沒有民族觀念」的說法,整個社會都認定華人對祖先土地的忠誠高於國家,於是,當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華人的族群性也就被本質化為共產主義。一直到今天,印尼族群和華人之間的邊界線,仍明顯可見,但這條線對我這個同為華人身分的外來者而言,卻也是困惑:我似乎應該同情印尼華人長期的處境,但聽到他們嘲弄批評「印尼人很懶、很落後」,總讓我也恨不得聽不懂他們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