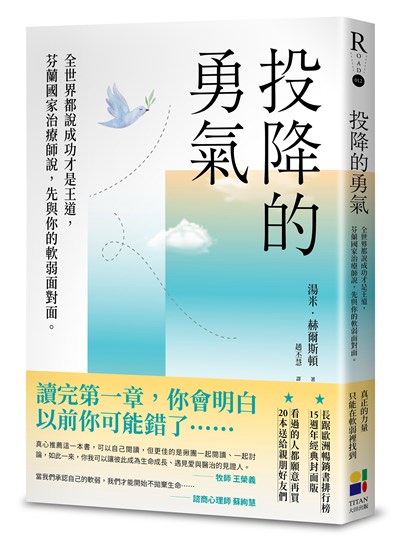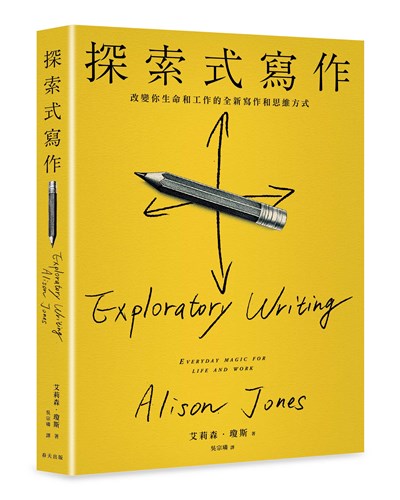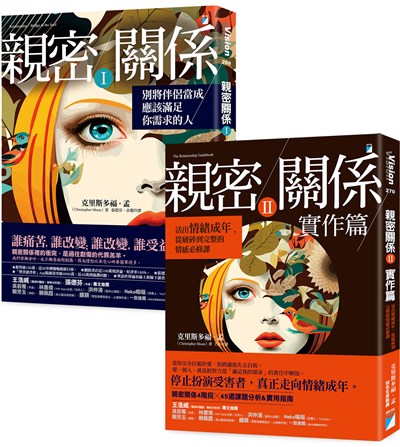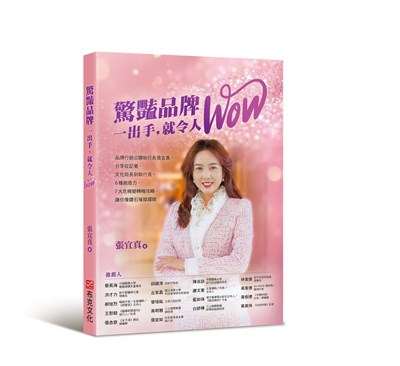王政忠老師在只有六個班的偏鄉小校,以「孩子想去的地方,就是第一志願」的興趣;「讓孩子摸索並且知道自己想要去的,叫做適性」的引導;「讓孩子有能力去到他想去的,叫做揚才」的發展,來實踐以上的教育理念。
文章節錄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除了小海島慣常的濃霧,金門的天氣的確很不錯,包括了那一個晚上。
一早,集合點名後,連長一貫平靜的語氣宣布:
「臺灣中部發生了大地震,各位弟兄可以打個電話回家探詢一下家人的狀況。」
大地震?能有多大?臺灣不是常地震?會怎樣嗎?
弟兄們其實並沒有太驚訝,包括我在內,在打電話之前,我還一派輕鬆開著玩笑:「金門怎麼都沒有搖一下啊?」
直到電話那頭傳來驚恐的語氣,我才略略感到不安。
「倒成一片啊……到處在起火啊……」我爸急促得上氣不接下氣。
「真的嗎?金門都沒有—」我狐疑。
「電斷了,大家都逃到中興大操場了,也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我爸都快哭了。
「那、那—」我不知道該問什麼。
「我們也逃到操場了,我們……嘟嘟嘟……」電話斷了。
直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臺灣之前,我與家裡的聯繫一直是中斷的,這樣的中斷讓我心急如焚,坐上金防部特別安排的返臺專機之前,我所能知道關於地震的訊息只有中視新聞快報兩側的跑馬燈文字說明,因為電視畫面一直停格在阿里山那間起火燃燒的飯店,除此之外,只有無止盡的揣測。
飛機降落在臺北松山,我採買了一整個行軍背包的乾糧和電池,直奔南投。
小巴士往草屯疾駛,沿路我看到彷彿戰場的景象,灰白或濃黑的燃燒火煙不時進入眼簾,斷裂的橋梁、倒塌的建築、聚集的帳篷,不斷告訴我:是真的,很嚴重!
車行進入中興新村,我竟然聞到空氣中摻雜著不算淡的瓦斯味。
中興新村耶,怎會有瓦斯味?
一下車我就狂奔前往大操場,果然滿坑滿谷的帳篷,繞了兩圈,終於找到我的家人。
來不及卸下行囊,所有最可怕、最不可思議的形容詞紛紛出籠,那一晚的驚恐、那一晚的難熬、那一晚的死生契闊,讓我寒毛直豎,冷汗直流。
幸好,家人平安,我稍稍心寬。
當晚,強烈的餘震不斷以各種方式對我強調—我所聽到的、感受到的,不過是那晚的千百分之一!
天亮,被透過帳篷的炙熱陽光晒醒,我起身,晃到簡易四方桌前,咬了一口麵包,我媽隨口嘟囔:
「爽文好像很慘。」
「是嗎?」我的心倏地沉了下去。
「車都開不進去,南投酒廠都燒了!」
「是嗎?」都已經夠窮了,再搖這麼一下,後果……
「國中不知道有沒有怎樣?」
「不知道耶……」我還在掙扎。
「啊你的學生呢?」
「……」
「ㄟ、ㄟ,你要小心!」媽在後面叫著。
我得進去看看。
我騎著機車,沿著我第一次去到爽中的路時停時進,那一年來一直指引著我的雙黃線此刻斷斷續續、高高低低。愈接近,心就愈忐忑,兩旁觸目所及盡是斷垣殘壁,有些堅持不走的人家,就地搭起布棚,多數默然無語。繞過土地公廟,轉進公墓。
我的天哪!
L形的校舍倒成波浪狀,幾乎無一倖免,集合場裂痕四布,瓦礫遍地。蓊鬱的林木或倒或臥,僅存的椰子樹孤伶伶地杵在操場旁不知所措,而籃球場竟然隆起一整個半邊,以後上體育課打籃球,勢必有一方快攻過半場要爬坡了。
學生呢?學生呢?
空盪盪的校園死寂得可怕。
一個老阿婆突然出現,我攔下她直問:
「郎ㄌㄟ?去都位?」
「攏米哩爽文國小啦!」
我油門猛催,再次狂奔。
到了爽文國小,車還未停妥,我的兩個學生觸電似地望見我,拔腿就朝我跑來。
「老師、老師!」幾乎是尖叫的音量,她們放聲開始大哭。
「怎麼啦?怎麼啦?」我一把拉入懷中。
「老師、老師,我家倒了啦……」含糊不清的話語卻清晰得令人心痛。
「那、那、那……」我半晌擠不出一句安慰的話。
「老師,某某某死了,我們班那個某某某死了啦!」我被電流縛住咽喉,張口無言。
「老師、老師……」
「別哭、別哭、別哭啦!」我只能這麼說,從沒有這麼無力過。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啦?哇啊—」
我……,會不會回來?
◎適孩子的性,揚孩子的才
關於適性,我的想法是這樣:
一、當孩子想去,也有能力去的時候
欣賞他的亮點,並鼓勵他培養挫折容忍度及同理關懷心。人外有人,能接受自己不是那麼的完美,真正的熱情不是超越誰誰誰,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證明自己,並能夠同理周遭較為不足的人。成就自己是快樂的,成就他人是一百倍的快樂。因為成就自己是填平自己的不足,是一個minus到zero的過程,而成就他人則是墊高自己的視野,是一個從zero到plus的過程,解決了他人的問題,增加的是自己的能力。
二、當孩子想去,卻沒有能力去的時候
陪伴他做最大的努力及嘗試,並且在陪伴的過程中引導他認清真正的性向。考不上一中美術班沒有關係,社區高中美術班也可以;考不上臺中高工汽車修護科沒關係,草屯商工汽車修護科也可以。重點不是一中或高工,重點是美術及汽車修護,讓孩子發光發亮的不是明星高中職,讓孩子發光發亮的是天賦得以適性。
三、當孩子有能力去,卻不想去的時候
尊重他的選擇及興趣,支持他在喜歡的領域敬業、付出且投入。因為敬業就會專業,因為付出就會傑出,因為投入就會深入,不要強迫每個孩子都到學術領域成為愛因斯坦,而是尊重及支持孩子在不同領域成為那個領域的愛因斯坦。
四、當孩子沒有能力去,也不想去的時候
欣賞孩子在學科或技職兩條路以外的天賦,陪伴他繼續探索還未發掘的興趣。如國中還沒探索出來,就於高中職再探索;如在體制內還沒探索出來,就在體制外繼續探索。引導孩子在探索的路上明白一件事:學習可以慢,但不能算了。
關於揚才,我是這樣想的:
所有的孩子都必須是也應該是學習的主人,這四年近三百場學校演講下來,我的觀察是:
愈是偏鄉愈是弱勢的孩子愈需要老師引導,引導他們成為學習的主人,偏偏愈是偏鄉愈是弱勢的地區,教學活化得愈少,翻轉得更少。都市的孩子在家庭支持及文化刺激之下,學習的起點較早較高,加上都市地區師資及教學資源較為充裕,早早就開始進行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教學活化及翻轉,但偏鄉地區仍大部分重複著以教學者為主體的課堂模式。
爽文國中在四年前開始,首先從國文領域嘗試活化及翻轉,接著在其他領域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跟進,經過會考的成績顯示,我們的孩子在各分科拿到A的比例都達全國平均值,甚至在國文及英文的部分還超過全國平均值,英聽全對的比例達二四%,錯兩題以內達四四%。雖然每一科拿到C的個別比例也超過全國平均值,但五科都C的比例只有二七%。
我的分析結果如下:
一、我們的翻轉活化讓四分之一的孩子有能力拿到A。
二、拿到C的孩子根據答對題數顯示,大部分都接近B,而他們的國一入學測驗離B很遙遠。
三、原本外界預期英聽會出現的城鄉差距,在本校似乎狀況不嚴重。
四、五科都C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但應該是全臺灣偏鄉最少的。
不得不說:我們努力翻轉活化了!
但還是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孩子拿到五個C,我們能不繼續翻轉嗎?
還沒有翻轉活化的偏鄉學校,能不開始嗎?
最需要翻轉的是偏鄉,但偏偏翻轉最少的是偏鄉;最需要翻轉的是國中小,但偏偏翻轉最少的是國中小。
偏鄉國小最需要翻轉的是學習態度,翻轉了嗎?
偏鄉國中最需要翻轉的是學習方式,翻轉了嗎?
如果家長不甘不願「適」孩子的「性」,如果老師無心無力「揚」孩子的「才」,制度如何?志願序如何?作文比重如何?都不會是影響教育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