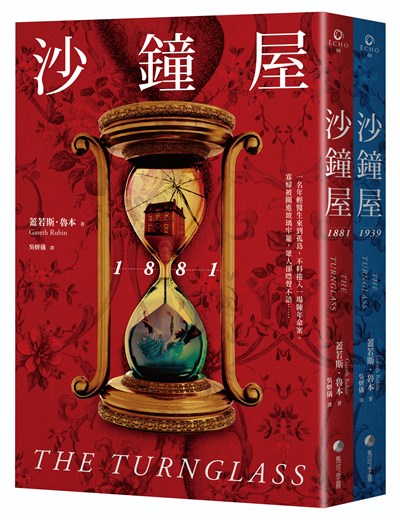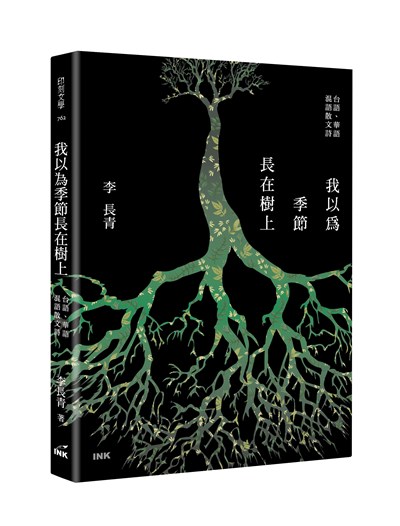日本小說家吉田修一出道20周年,推出重量之作《國寶》,以少見的日本傳統藝術歌舞伎為題材,描寫出身懸殊卻被命運帶上同一條學藝之路的兩位主角──喜久雄(黑道大哥的獨生子)與俊介(歌舞伎世家第二代)兩人亦敵亦友、追尋世間極致之美的一生。
文章節錄
《國寶》
「俊寶,你在幹什麼?就要開幕了!」
看見因宿醉而醜態畢露的俊介爬也似的來到後台,正在變身成《雙人道成寺》白拍子花子的喜久雄目瞪口呆。
說他正在變身,是因為才換裝到一半,身穿羽二重,臉塗白,眉下淡淡掃紅,披著燦爛奪目綴金箔的黑底枝垂櫻大振袖。
以這身模樣罵人,簡直像是演員還沒上台就從俏姑娘露出真面目,變成了大蛇。
「好了好了,喜寶也別罵了。少爺到底是來了。好,快準備!大家動作快!」
源吉一如往常地包庇俊介。
「又這樣寵他……」
喜久雄不以為然。但這時候計較這些,舞台布幕也不會等人。
「松藏哥,去提桶水來!」
喜久雄一喊,黑衣松藏立刻準備一桶水,抓住酒還沒醒的俊介脖子,把他的頭推出窗外:
「要潑囉!」
一桶水直潑下去。
「啊!」
俊介的慘叫聲響徹四國琴平寧靜的早晨。此刻他們正隨著劇團,以花井半二郎為招牌,向西巡演。
淋了水,俊介似乎酒醒了,撲到鏡台前,像懲罰遲到的自己一般,拿起大刷子往臉上猛塗白粉。
「我們把整個飯店都找遍,你跑去哪裡了?」
旁邊的喜久雄也幫他準備胭脂。
「我醒來的時候,不知道是在哪家酒店的地上,嚇了我一大跳。」
「還說得那麼悠哉。」
據俊介說,昨晚和喜久雄他們分開後,又一個人晃去琴平的鬧區。
「不過昨天那樣一喝,我整個人心情好多了。」
俊介熟練地畫起眉毛,呼氣中還帶著酒臭味。
散發酒臭的道成寺白拍子確實令人倒胃,但化好妝後就變得人模人樣,實在不可思議。
「跟那個愛甲會的辻村先生在一起實在太痛快了,沒有人像他那樣。昨天他叫來全琴平的藝伎大辦宴席。喜久真好,從小身邊都是那樣的人,光是這樣人生好像就比別人加倍有趣。」
俊介一邊說,雙手也反射性地動著,穿上羽二重、戲服,準備上台的進度漸漸趕上喜久雄。
這次演出,也由於是人數較少的巡演,特別改編,由年輕的喜久雄與俊介兩人來跳有女形舞巔峰之稱的《京鹿子娘道成寺》。
各位看官久等了。話說,這匆促中開始的第五章,距離德次去北海道追夢的第四章,已經過了將近四個年頭。
此時,世紀慶典「大阪萬博」剛於上個月開幕,從每天的入場人次、月球石,乃至於全自動洗澡機裡發現迷路的外國人等等,全日本每個角落的話題都被萬博綁架了。
順帶一提,這四年內,喜久雄與養母阿松商量後,正式成為半二郎的部屋子。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也就是十七歲那年,他於京都南座的公演上襲名為「花井東一郎」,在《伽羅先代萩》中以婢女這個小配角首次登台。
只不過,這可喜可賀的初次登台日,喜久雄可以說根本不記得。
那天,阿松從故鄉長崎趕來看戲,彷彿她本人要上台似的,在擁擠混雜的休息室這兒晃晃、那兒轉轉,她的緊張也影響了喜久雄。
雖說終於獲得角色初次登台,但也只是跟著榮御前出場的婢女之一,簇擁著御前,提著燈籠從花道走上舞台之後,當然沒有台詞,在舞台左方坐了十五分鐘左右就直接退場。
然而,從鳥屋37來到花道那一瞬間無可言喻的氣氛,他倒是記得很清楚,宛如騰雲駕霧。如果硬要用言語形容,或許可說是幸福吧。
但之後就完全沒有記憶了。長達十五分鐘的時間,他應該是在舞台上看著半二郎飾演的八汐與政岡對答,然後坐在舞台左方、離開舞台、走過走廊回到休息室、面向鏡台,他才終於回過神來。
於是,自己剛才所在的舞台地板觸感,清清楚楚看見的每個觀眾面孔,還有最令他印象深刻的,舞台上甜蜜的芬芳,全都復甦了。喜久雄忍不住想隱身於一旁的屏風之後。因為,有如夢遺後羞於見人的那種恍惚感此時突然襲來。
同樣是初次登台,御曹司俊介的經驗就與喜久雄完全不同。據說,俊介初次登台是四歲的時候,半二郎當然在場,還請來關西歌舞伎的另一名門生田庄左衛門,向觀眾宣布襲名。
儘管如此,聽俊介說起時,他顯然沒有體會到這種恍惚感。那麼,自己初次登台的經驗絕對比較好──喜久雄不是嫉妒,他真心這麼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