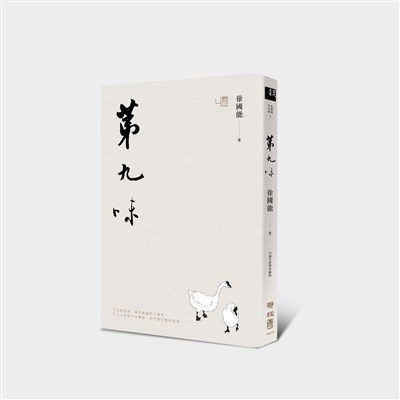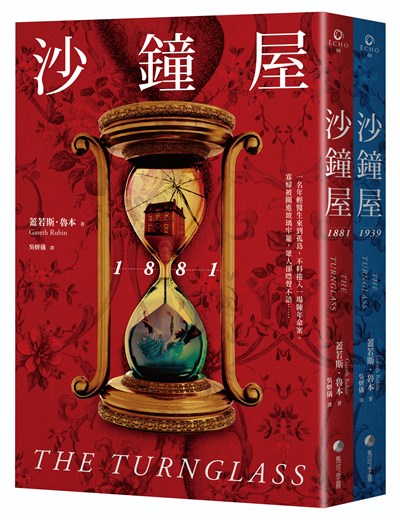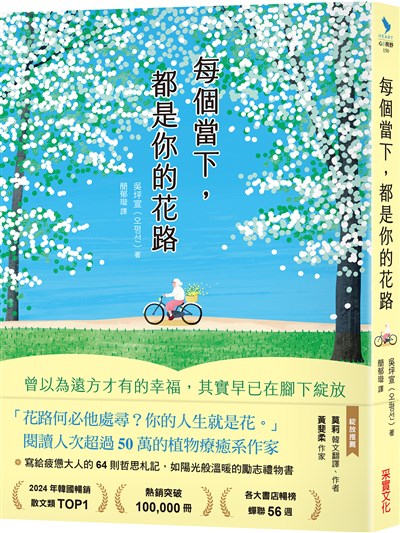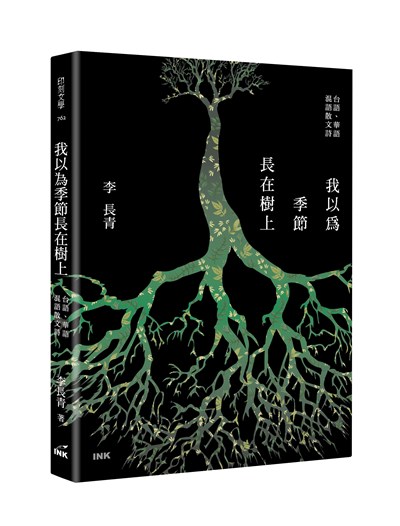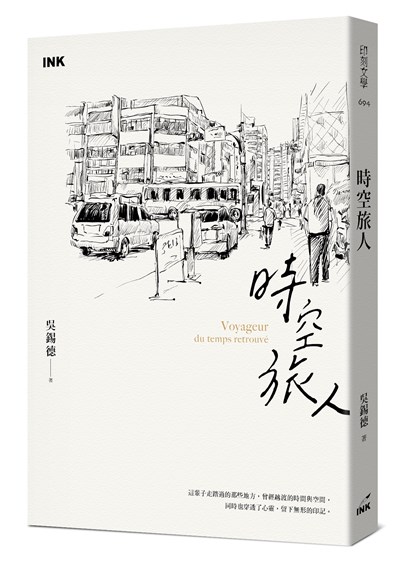
看似悠悠的人生長河裡,每一次的旅程其實都是一期一會;即便同一條河,人們也無法再一次踏進相同的河水。如果我們願意珍視每一次的旅行,或許可以在未來的生命中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吳錫德的《時空旅人》書寫、掇拾了個人生命中的多許旅行和精彩片段,也透過文字追記,讓那些旅程浮現出各自的意義。然後累積出「人生」這一段旅程的種種深情與深刻內涵,為其心靈和精神留下無形去永恆的印記。
文章節錄
《時空旅人》
台北隨想
做為一個老台北人真的很悲哀,每年只能在農曆春節五、六天假期,當眾多新台北人轟然出城歸鄉團聚淨空之後,我才感覺到一種舒暢,一種台北人的尊嚴……
我家世居台北盆地(昔稱「大佳臘」,「凱達格蘭」之略語,意為「沼澤地」),在台北舊城東郊,今復興南路、瑞安街口。這一帶昔稱「大灣」,想必有過一條河川(即瑠公圳運河)在此拐了個大彎,後來改為雅音「大安」(即大安區)。記得小時候曾問過祖父 :我們住的地方為何叫「大安」?阿公語帶神祕地回我:「就是二個小孩『大冤』(「大打出手」之意,閩南語諧音),三個大人拉不開。」。其間除出國念書外,一直棲息在南台北,四十多年來心中絕少有過所謂的「台北人」意識。直到有一回搭計程車與司機閒扯,這位運將是個年過半百的新台北人,倚老賣老地吹噓某某攤子的鯊魚煙有多好吃!我順口回他:隔壁巷底的那家更道地。他心底認同,瞧我這副年輕模樣,問我怎會知曉?我洋洋得意回說:我是台北人呀!司機悶了半晌,不等我收起得意笑靨,便頂我一句:「真是稀有動物!」接著他還一本正經地說,他做運將拉客也有二、三十年,已經很少能載到「正港」台北人!
曾幾何時,台北人已淪為故鄉的異客!「台北人」成了一個既抽象又罕見的族群。首先,因為他們被稀釋了。當今,以台北為新故鄉的新台北人早已超過生於斯長於斯的老台北人。其次,除老舊社區的台北人仍依然守著破舊的經濟生活圈外,大部分都給快速的都市規畫搞得四處離散,尤其被居高不下的房價給趕出台北。再者,有錢的台北人,或台北「田僑」(靠高價出售祖產致富者)不是遷往郊區華宅,就是移民美利堅去了。這種情形像極了我所熟悉的巴黎,它就像是每個國際都市的宿命一樣,大都會通常只能容納最富有和最貧窮的兩種人,而所有的人都身不由己地不以它為故鄉!
發現童年的老台北
唯有親眼見識過都市蛻變的人,才夠資格談論這座城市。小時候,學校「家庭經濟狀況」欄裡皆不假思索地填上「小康」兩個字。除了為拚選舉找到「三級貧戶」外,幾乎沒有哪個孩子願意在這個節骨眼輸給別人。但那絕對是一種善意的謊言,在那個時代幾乎是找不到不貧窮的人!小時印象裡,有好一陣子早餐飯桌上只有菜脯米(醃曬過的白蘿蔔乾)和稀得不能再稀的粥。台北況且如此,鄉下更不消多說了。
那時的窮是遍及全台的一種普遍現象。至於白先勇筆下《台北人》那種生活,簡直活像一部「域外小說」,描寫一批流亡台灣的大陸人,自動住進台北「隔都」的生活。一群我所不熟悉的台北人面孔!那種感覺像在觀賞六○年代史蒂夫麥昆主演的那部好萊塢黑白名片《聖保羅砲艇》。背景是你再熟悉不過的自個家(淡水鎮),上演的是與你毫不相干別人的故事。那種有點兒親切,又很疏離的感受。或許白先生在開時空錯置的玩笑吧!直到現在我還認為他「僭用」了「台北人」這個字眼。只有極少數國民黨高官權貴和避難來台的上海殷商能過那樣的台北生活!
想我小時住眷村的同學,原籍江蘇的劉子傑住建國南路邊的大安新村,在美軍顧問團第二營區(之前台北信義路三段美國在台協會)正後方。不過,他都是從安東街三三八巷進出。所以我們倆乃志同道合的小兄弟!一路同道的小湖南人熊允中,他住和平東路上的成功新村,也都一貧如洗地過活。尤記得小時因家中無人伴讀(不是不識丁、就是得出門打工),放學後最愛到子傑家一起做功課。因為他母親極為親切,和一位小姊姊可就近請教。他們家雖住二層樓,但一層的面積恐怕也只有十來坪上下。我們的書桌就是他們的飯桌。一邊寫功課還一邊聞得到與我家口味完全不相同的飯菜香。至於新生南路那一端,我的母校龍安國小對面,住日本宿舍的外省籍同學家,因動線不同、交情不夠,也就無緣窺視。本來統治階層(不管日本人或外省人)的居住空間自然會有所區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