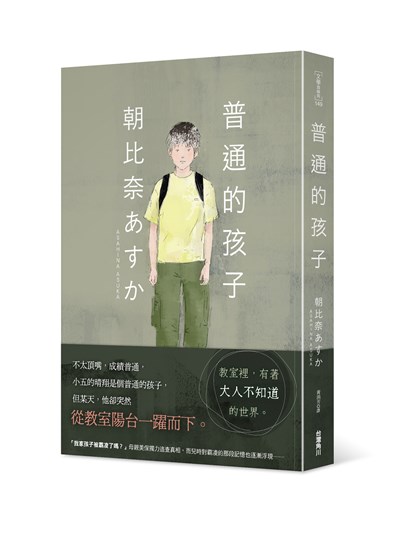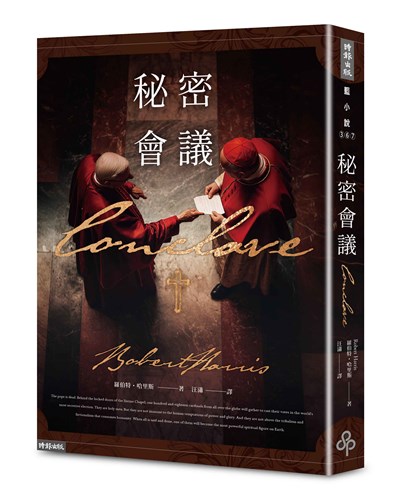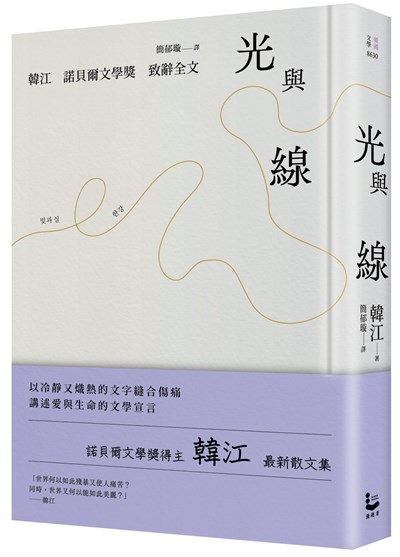雨煙是熱帶燥動焦急的雨幕,雪鹽是北美怎麼也暖和不起來的漫長冬季,在詭譎世局與多舛命運之前,唯有書寫能完成自己。他在無數極端之間擺盪,於「暗世煙濛」中見人心不屈的高貴,耕耘重生的春谷又遭逢「淚愁闌干」的坍塌;在「神聖殿堂」識破「流亡度假村」與「養士」的荒謬,心中有無限感嘆;「鄉村醒來」記述耗費心神的遷居之後,妻子傅莉漸漸在憂鬱的晚春甦醒,許多當年不敢說的,得以出口。「墾荒列傳」描繪總是在天使與魔鬼間拔河的異議人士,那是六四之後,他所見一整代中國流亡者的悲劇。最末「靈動難眠」回望「河殤」、「六四」,仍有說不盡的迷思。
內容節錄
《雨煙雪鹽》
小路 佛教 暗世
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
一直通向迷茫的遠方……
我則依舊迷戀老歌,因其調子抑鬱而茫然,還是俄羅斯的,雖然那裡正戰火紛飛,烏克蘭不甘被俄羅斯併吞。
我再一次唱《小路》,那裡沒有雪,沒法在「雪裡顛簸」,而是在溫暖乾燥的冬季曼谷,但是在場的男女青年維權者們,無人知道坐在輪椅上的傅莉,就是從前面那首《小路》的迷茫雪地中推過來的,只有李曉蓉落淚,她知道這三十年我們的經歷,她在靠近中國的曼谷辦培訓班,便於受訓人員抵達,結業晚會上眾人要我唱歌,我又跌進雪裡……。
見過達賴喇嘛兩個月後,二○一四年伊始,我從北美飛到南亞,像二○一一年秋去日內瓦一樣,去趕一個人權培訓班,不過這次我帶上了傅莉。當時曼谷正發生反政府抗議者「封鎖曼谷」行動,交通阻斷,旅遊業重挫,我們飛到曼谷是深夜,卻因時差,我五點鐘就醒在酒店裡,天色朦朧,下樓找櫃檯換點泰銖,那個泰國小夥子說你的美鈔太破舊了。我又去隔壁大商場買點瓶裝水和日用品,拎著東西返回酒店房間,見傅莉已一團驚慌,懷疑我扔下她跑了,自己趕緊去找護照,發現一信封袋現鈔才安心,可是我一聽非常傷心,覺得她毫無安全感怎麼辦?說了她幾句,她說:「你一走燈就滅了,屋子裡一片漆黑……」我這才發現,原來我出門拔走門卡,就切斷了房間電源,早晨連窗簾尚未拉開,可不是一團漆黑嘛,她乍一出來,飛到千里之外,怎會不害怕?傅莉真無辜,我趕緊向她道歉、示好,想各種法子讓她放鬆下來、愉快起來,午飯後她就好起來了。
曼谷此行,再次結識一批國內的「人權捍衛者」,其中有個剛烈女子,給我印象深刻,她的姓也別致,大家都管她叫「野大姐」,我也跟著叫,其實她五三年生人,比傅莉還小一歲。她被一樁金融詐騙案,即李鵬的小兒子李小勇公司製造的「新國大」事件,洗劫了所有資產,從此走上維權道路,因抗爭又被投入勞教所,活出來「只剩下皮和骨頭」,然後她寫了一本書《不虛此行—勞教紀實》:
我要讓地球人都知道,世上還有比奧斯威辛、比關塔那摩更沒人性的人間地獄—北京市勞教人員調遣處。
……凡是我在調遣處裡只能看著別人吃而自己吃不到的食物、凡是別人吃的時候讓自己饞得心臟要爆炸的食物、凡是自己饞得恨不得要搶過來吃一口的食物,而每當這時候,我卻要強壓住內心的憤怒,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現在,我的思想開始強烈的排斥了……。
野靖環在會上講述她患上的「勞教後遺症」,有兩個細節,真是比小說還要震撼,「餅乾」與「蒙牛包裝盒」:
每頓飯前的一個小時我就感覺餓了,肚子嘰哩咕嚕的叫,腸子不停的動著。儘管菜裡沒有一點兒油水,我還是一分一秒的盼著快點兒開飯。
就在我餓得難受的時候,包夾(用表現好的勞教人員全時段監視控制)我的人也開始餓了。但是她們有各種各樣的食物,幾個人坐在牆角,打開花花綠綠的食品袋子,餅乾的香味、花生的香味、刺激我的腸胃更難受了;雞蛋、糖這些雖然沒有香味,但我看見它們就饞得想流眼淚。
她形容,那些人嚼餅乾的響聲,像刀一樣剜她的心。她在勞教所幹活做「蒙牛吸吸爽」的六棱形包裝盒,出獄後從來不買。她問過很多人:
你知道饞是什麼感覺嗎?如果讓我選擇挨打還是挨饞,我現在一定會選擇挨打。人家無法理解。我不經歷,也不會理解。
我以為,時間會消除痛苦。可是,已經一周年了,我到超市買東西,一路過餅乾、花生米的貨架就趕緊躲開,這一年沒吃一口餅乾、沒吃一粒油炸花生米。
在曼谷機場,又遇到「野大姐」,她過來抱了一下輪椅上的傅莉,然後跟我們告別,臉上是一種堅毅而蒼涼的笑容。
至今,我還能從網路上,經常看到這個笑容,出現在各種民間抗議的場合。
‧
國保不知道從哪裡翻到一張我給蘇曉康先生拍的照片,拿出來問我:「你什麼時候認識他的?」我說:「不記得是在哪碰到的帥哥。我看他挺帥,就合了一張影!」那個國保隊長惡狠狠地說:「把手機密碼交出來!」我說:「絕不給!這是我的隱私。有本事你們把手機砸了,回頭你們賠我新手機。」
這是在曼谷碰到的另一個姑娘,也很剛烈。
向莉是一個七○後,出生在文革結束那年;而九十年代中國的「起飛」,則注定要塞給他們一個「歲月靜好」,雖然她不一定熟悉張愛玲,因為她讀美術史,出來教書和經營畫廊。一個辦畫展的,大概不會是「蟻族」,更不屬於「弱勢群體」,不知為啥藝術卻拴不住她的心,也許網際網路轟毀了她的「洗腦三觀」,也許員警不救被淹死在廣渠門橋下的丁志健驚破了她的平靜,總之她在象牙塔裡醒來,一發不可收拾。她這種人,若生在四十年代,大概會投奔延安,當時稱為「理想主義者」,然而現在他們自稱「人權捍衛者」,在中國是異類,稀罕、危險,卻絕對前衛,她還留著很長的頭髮。
我雖然在曼谷給人權捍衛者們講方勵之八九年在北京被員警圍堵的故事,「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堵截」,我說「荒野的感覺」也會擴展到你們身上,包括國內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但是我完全沒有料到向莉遭遇的情形,她偶然出境遇到我就被打上異議符號,在國內就沒有安全了。
她從雲南的一個邊陲城市,「通過祕密方式跨越中國國境,進入東南亞某國的莽莽叢林裡,由此正式踏上逃亡之路」,但是在泰國她被「告密」而落入移民監獄,她心愛的一頭長髮也險些被獄方強行剪掉,她卻在極壓抑的環境中,靠著信仰的支撐保持快樂和平靜,那頭髮竟然沒有長出一根白髮。他們是坐牢要哼曲寫詩的一代人,她的一首詩結尾寫道:
從洱海到依江
從蒼山到金塔
你說快來吧
這裡的葡萄已經熟透
「七○後」來到我們的流亡群落裡,顯示中國的政治壓制已經蔓延到新一代人,這恰好反映了更多的世代在覺醒。對向莉而言,流亡是新的挑戰,她寫了一本年輕自傳《歲月不靜好》要我作序,我則反用她的詩句,告訴她「這裡的葡萄還是生脆的」,但卻是一個全新的天地,她還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