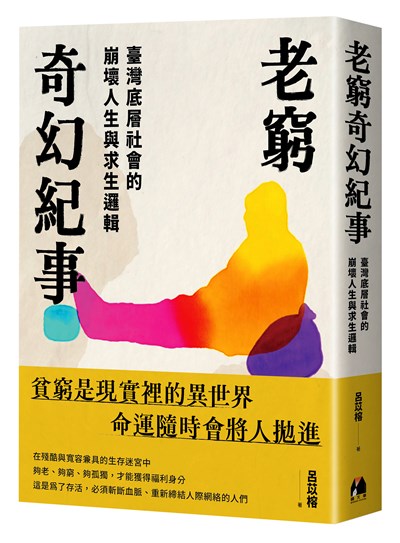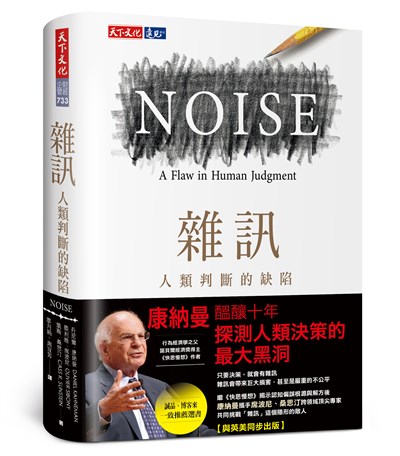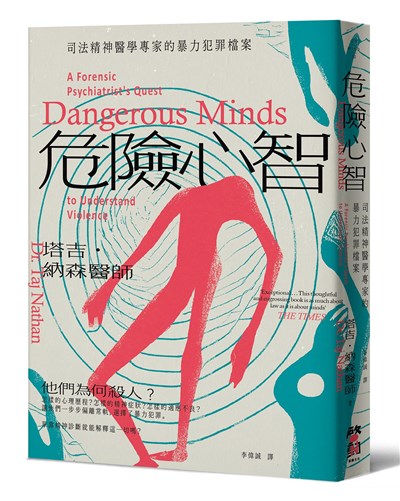儘管文化大革命帶給中國許多破壞而悲痛的記憶,但在文學、文化乃至社會整體的共同記憶裡,仍然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丁學良作為過去的紅衛兵,現在的大學教授,真誠地反思細描了這一場年少經歷,如何地影響了他這一代人乃至好幾代中國人。文革並未遠去,甚至以各種變形深藏在所有中國社會結構的角落。
文章節錄
《革命與反革命追憶》
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報復的革命
一位美國老太太的提問
這大約是在一九八七年的暑假,哈佛大學的幾位資深教授(其中包括在西方名學府首開「中國文化大革命」一課的馬若德先生〔Roderick MacFarquhar〕),應邀赴美國西海岸三藩市地區的哈佛校友會作系列學術演講。此乃哈佛的傳統,在校友集中的北美洲的中心城市,每隔一、兩年舉行圍繞一個大專題提出系列報告,以便於哈佛歷年畢業的校友們有機會更新知識,瞭解他們所關心的那些學科裡正在從事什麼樣的開創性研究。這種知識的聯繫,會引導校友們對母校的捐贈和支持。
那一年哈佛校友會三藩市分會的新任會長是位李姓華裔人士,三藩市地區又是美國華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哈佛大學的教授演講團選取的大主題,因此都是與東亞區域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相關的。我當時剛剛通過博士資格考試,鬆了一大口氣,也被邀請進演講團。馬若德教授要求我以親身經驗為背景,講一講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什麼那場激進得無與倫比的革命,卻導致了共產主義世界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資本主義化革命——鄧小平的市場導向的改革開放?
每個講者只有一小時的時間,一半演講,一半回答聽眾的問題。我以我的初級階段的英語,概略的講了一下我當初為什麼成為紅衛兵中最狂熱激進的一翼的骨幹分子,把本校、本縣、本地區的走資派統統打倒了還不過癮,又殺奔外地,先是到省城去參與打倒省委書記、省長的造反行動,後又不辭辛苦,跑到鄰省的南京去聲援江蘇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他們省裡的頭號、二號、三號走資派的壯舉。我還講了我們怎麼編印紅衛兵戰報——我當年最有成就感的革命傑作之一,便是用十九世紀的老式鋼板、鐵筆、蠟紙,手刻出小報的「原版」,以手推滾筒的技術,每張蠟紙「原版」油印出一千幾百份的紅衛兵小報,與全國各地的紅衛兵組織交流。我還不忘記強調,「文革」是我輩一生的首次、也是一生中最豐富深刻的一次政治訓練。懷存由「文革」學來的經驗教訓,你不但可以在中國政治風暴裡潛下浮上、死裡求生,而且可以在異鄉他國的政治濁流中辯風識潮、進退自保。
我的話音剛落,坐在聽眾席前部第三、四排右邊的一位六十出頭的清瘦高挑的白人老太太站立起來,用緩慢有力、一字一頓的語氣向我發問:「根據我從書籍、報刊上讀到的,從電視、電影上看到的,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使數千萬的人受迫害、數百萬的家庭喪失了親人、無數的學校和文化遺產被毀壞,人類文明史上很少有幾次政治運動,破壞規模能夠比得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我又讀到聽到,所有那些破壞人的尊嚴和生活、搗毀文化和教育的激烈行動,都是由毛澤東的紅衛兵組織當先鋒隊的。令我不理解和驚訝的是,你作為一個紅衛兵參與了那些激進活動,如今已經來到美國,進了我們國家最好的大學讀博士學位,竟然至今你不為你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為感到懺悔。你在談論你們當年從事的造反運動的時候,甚至有自豪的語氣。我真為此感到非常困惑!」
老太太問完,並未立即坐下,立在那兒好幾分鐘,大概是胸中怒氣難消,凝視著我,示意她是在等候我的答覆,頓時全場氣氛凝重。我雖然被她重炮轟擊質問,但她一臉正氣,儼然是為不在場的千千萬萬「文革」的受害者們仗義執言,我也不好把她的嚴詞質問當做是對我的人身攻擊。於是清清嗓子,禮貌地作了應答,大意是「文革」整體雖然是件大壞事,但「文革」中被批鬥衝擊、皮肉受苦的人並不全然是無辜的好人。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無法無天地騎在老百姓頭上稱王稱霸、作威作福,造反派在「文革」中對他們的批鬥體罰,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的藉機復仇洩憤,雖然也不合法,但是有正義性,云云。
我所應答的,確實是我想說明的一個大道理,可是當時就覺得沒能把這個道理說透;沒說透,是因為沒想透。自那以後,每逢與人討論起關於「文革」的評價,我總是想起那位正義凜然的美國老太太,而我也老是不能忘記,當時她顯然並沒有信服了我的解釋。這麼多年來,我時不時地在腦子裡點擊那個問題。我也特別注意到曾經參與「文革」的海外人士中,有兩個同我的觀點很接近——楊小凱與劉國凱;這兩位關於「文革」的主要評論,都列入我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激進學生運動的比較」課程的學生參考讀物中。他們兩位都堅持對「文革」中的一些造反行動的原則性肯定(這一點使人易於誤認為他們是「極左派」立場),他倆同時又堅持對毛澤東「文革路線」的徹底批判(這一點又使他們與所謂的中國「新左派」、「極左派」涇渭分明)。
事過多年,我倘若再面對那位美國老太太的問題,會這樣向她解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各種人報復各種人的亂糟糟的大革命——說它亂糟糟,是因為一個本來就沒什麼法制的巨型社會,又讓一個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毛皇帝把他平時管治民眾的官僚體系跺得稀巴爛——其中有壞人報復好人,有好人報復壞人,有壞人報復壞人,也有好人報復好人(這四類經典分法的出處下文有交代)。當然這四種類型的報復所占的比例不一樣:似乎壞人報復好人的,最終要遠超過好人報復壞人的,而其他兩類報復的比例更小。所以親身經歷過「文革」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它都不同於一般化了的(generalized)「文革」,不論這「一般化」是由哪一個政治立場(中共官方的也罷,中共官方對立面的也罷)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