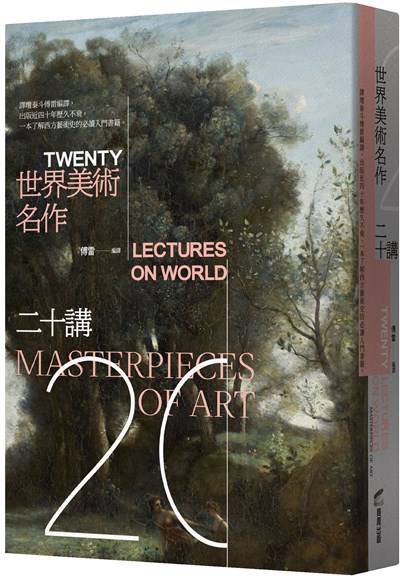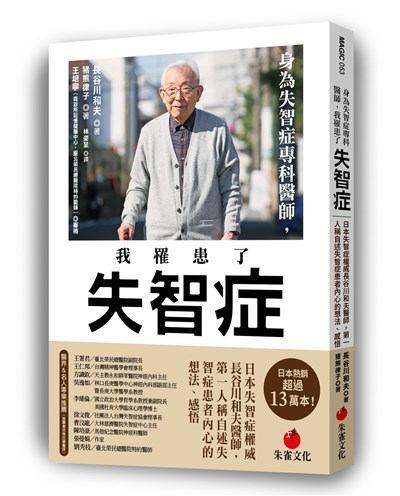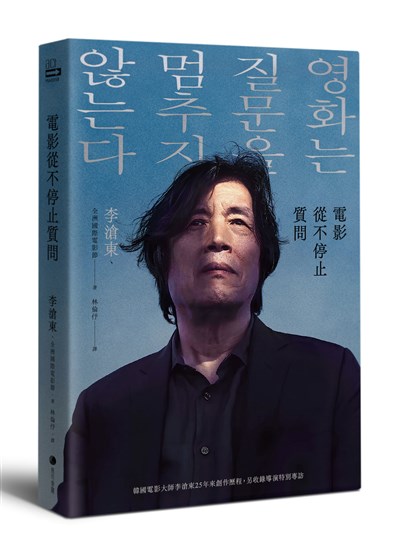作者說:「疼痛這個永恆的生命磨難,給了我們一個非比尋常的機會,促使我們在如此極端的時刻,以極端的方式回應,並表達自己。」我們或多或少都曾經歷各種疼痛,在體內巨大無聲的戰場中孤軍奮戰。可是,透過文學隱喻和日常詞彙,疼痛似乎在語言之間被轉移、偷渡了,因而變得可以共享,可以同理,可以被療癒。這本書無疑也是作者慘烈痛過的印記,它是如此鮮明有力而充滿希望,獻給所有在疼痛中受苦的人。
文章節錄
《聆聽疼痛:為痛苦尋找話語、慈悲與寬慰》
即使世界末日的喪鐘響起,連餘音也在最後的日暮晚霞裡從靜海孤懸的峭壁上逐漸散去,這世上仍會有一種聲音——人的無盡細語——在娓娓訴說著。——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諾貝爾獎得獎感言,一九五〇年
維根斯坦敦促我們改變「疼痛無法與人分享」的這個直覺信念。只要我們還能產生可用的疼痛語言,疼痛就能與人分享。我們或許對它能被分享的程度不太滿意,但這不應該讓我們回到私人世界,想在裡頭尋找更有意義的描述。不管是哲學家(維根斯坦及梅洛龐蒂)還是受苦者(史泰隆及喬治)都指出,那裡除了黑暗之外,我們什麼都找不到。
當然,許多時候我們並沒有默默遁入黑暗之中——特別是當疼痛還沒那麼糟糕、當我們仍極力想突破那道高牆的時候。雖然史泰隆告訴我們,他在傷痛來襲時只能結巴地說話,但他並沒有一直保持沈默,當傷痛稍微減緩時他就開始說話了,最後他還寫了一本關於自身傷痛的書,以動人的方式與他人分享經驗,甚至把自己結巴的部分都寫了進去。
我們緊抓著經驗的內在性不放,但同時也在顛覆著它。史泰隆用整整一本書來告訴我們,疼痛是「難以表達」的。吳爾芙也是如此,她在生病時感覺自己越來越孤立,因此認定這個經驗是「難以傳達」的,然而她寫〈談生病〉這篇文章卻邀請我們進入她的病榻世界——好比進入一個隱蔽的世界——並清楚傳達了她的感受。同樣,雖然狄金生把疼痛等同於空白,但她透過詩來傳達,意味著疼痛並不是真的那麼空白;而孟克則給了我們一幅關於疼痛的動人畫作,其中受苦者的吶喊無人聽聞。所以,即使這些藝術家宣稱受苦是一種孤獨而難以表達的經驗,他們的作品卻和這個訊息相互抵觸;他們與觀看畫作或閱讀文字的人分享了他們的經驗,即使他們知道這樣的經驗無法充分地交流。
我們需要投身這個世界,這樣的需求實際上不可能被消滅。它和求生本能一樣地直覺,而這兩者或許本就密不可分。著名的精神科醫師及集中營倖存者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Frankl)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被釋放出來後,藉由書寫指出了人的這個基本需求。就算是在最極端的受苦處境中,我們還是渴望能夠越過自我的疆界,並找到某種類似意義的東西。即使是在「為什麼?」這個問題最劇烈地折磨著我們的時刻——為什麼這種惡夢會發生在我身上?為什麼不乾脆自我了斷來脫離苦海?——多數人不會任由自己被捲入這個內向的漩渦,而是奮力往前邁進、向外連結。
所有的受苦,不管是源於自然因素(疾病)還是人的禍心(猶太人大屠殺),都讓我們變得孤立無援,但即使我們覺得已經與世隔絕,多數人還是想盡辦法要重回世界的懷抱。我們能否絕地逢生,其實就繫於這一念之間。
這種同樣是超越自我藩籬、與他人建立共同感的需求,成就了英語文學中最著名的篇章。一六六三年,約翰‧多恩(John Donne)在痛失愛妻及五個孩子後,被復發的熱病擊垮。這種當時在倫敦奪走許多生命的傳染病讓他臥床不起,幾個星期中他飽受折磨,幾乎不得喘息。許多醫師及專家都被請來會診,從催瀉到放血種種方法都用上了。不過當他對這些治療沒有反應時,他們就放棄了多恩。多恩被放著等死,他感到既害怕又孤單,然而在這麼孤絕的處境裡卻有一件事情使他不再孤單:他聽到遠方的教堂鐘聲零落地響起,這表示又有一個人死於這場傳染病了。多恩突然發現,即使生命如此不堪之際,他也並不孤單:
沒有誰是孤島,兀自獨立;每個人都是陸地的一角,整體的一部分。只要有一塊泥土被海水沖走,歐洲就少了一點什麼,這和失去一處海岬、失去一座你朋友或自己的莊園,並無二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減損,因為人我之間有如髮身相繫,因此無須追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
我們在尚—多明尼克‧鮑比(Jean-Dominique Bauby)的非凡成就中,可以看到福克納所謂「人的無盡細語」的顯例。鮑比是時尚雜誌Elle的法文版編輯,他在四十三歲時嚴重中風,淪為「閉鎖症候群」患者。他雖然全身永久性癱瘓,卻沒有因此委靡不振,當他發現自己還有一隻眼睛可以眨動,便設法(在語言治療師的幫助下)藉由眼睛眨動的次數創造出一個字母系統。他教別人使用這個字母系統,並藉此與人溝通,最後他把自己的生命試煉寫成《潛水鐘與蝴蝶》,不過令人感傷的是,書出版後沒幾天他就與世長辭了。當然,鮑比想與人溝通的欲望有其實際的一面——他想讓身邊的醫護人員知道他的疼痛、飢餓及其他需要,但與此同時,它也存在著更多意義。尋找語言對鮑比而言是一種解放,它讓鮑比不再受困於生病的身體,讓他的想像力得以化身蝴蝶,脫困飛翔。鮑比因此不再孤單。
我們也是透過向親友尋求協助、與診所或網路聊天室病友交談、比手畫腳或塗鴉作畫……來減輕疼痛所造成的孤獨感,至於用什麼方式或有沒有效果,其實都沒有過程來的重要。我們即將進入本書的下個部分——即使面對難以克服的阻礙,也要讓疼痛有話可說。我們總是想說點什麼,不管聲音有多微弱,只要一息尚存,總會細語喃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