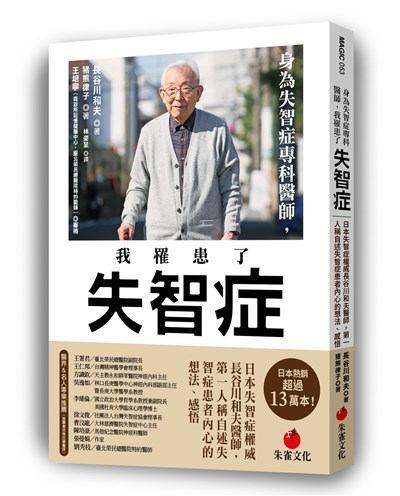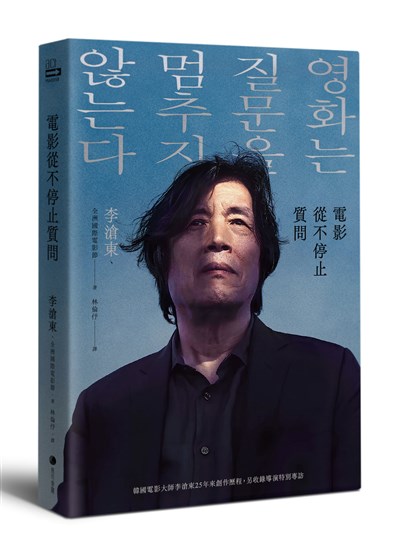「希望每個人都能在這本書裡找到一些感動的力量,找到一種呼應;彷彿在說,你們並不孤獨……而等待,確實會有所回報的。」這段話充分表達了魏德聖導演出版本書的用心,他要用自己2001-2002年那段失業歲月中真實的自白,給此刻正在困頓中的人溫暖的激勵。全書採雙軸線書寫,日記體記下的是真實生活中在困頓中蟄伏,以高度紀律為《台灣三部曲》作準備,找資料、寫劇本、勘景,持續努力著的魏導。另一條軸線是以黃金魚將為主角的小說體,表現為追求夢想不計後果那個強悍的自我。兩線交錯,十分精采。書中收錄了魏德聖導演即將籌拍的電影《台灣三部曲》的三個序場,簡單而有力,想像中的畫面已是張力十足,可以領略到魏導演的大企圖大格局。
文章節錄
《黃金魚將‧撒母耳:魏德聖的蟄伏與等待》
關於我
黃金魚將
我太清楚自己的長相了,我有一條泛著黃金色的背脊,一直延伸到大半邊的尾巴,有著如獵豹一樣的頭顱和光滑的白色肚皮。
我說過我太清楚自己的長相了,水中的世界是走到哪裡都看得到自己的世界。我很清楚地知道從人類的眼睛看進來的,是我們美麗而驕傲的身軀。但這些愚蠢的人們可能不知道,從我們眼中看出去的還是自己美麗而驕傲的身軀,我們的眼中只有自己,永遠只有自己,我們是最驕傲的魚種。
而我,頭上一顆螢光色的斑點,讓我不管白天黑夜都是同類兄弟們的焦點;我甚至知道背脊上的黃金色比他們都來得鮮豔。在這個以顏色決定強弱的魚世界裡,我有個英雄般的名字……一個謙卑而有智慧的英雄名字,我叫「黃金魚將」!
撒母耳
我如獅子般的性格之上卻覆蓋了一個瘦小的軀殼及孩子般的幼稚面孔,這讓我有能力做大事卻沒有人願意相信。他們總要我聽命行事,這使我的狂傲每天被壓抑。
我總是經常性地頭痛。我讓許多醫生檢查過,他們都說沒事,只是神經太緊繃了。我不敢相信我竟不知不覺戴上了伍迪艾倫式的神經質。我不懂我的生命會是這麼糟糕。也許是長時間的作夢充英雄,以至於變得太在意別人對我的看法。我必須壓抑住我的神經質來挽救我即將被毀滅的生命!我急需建立自信,於是我上教會尋求安慰與紓解,卻換來一個讓我的壓力暴增一百倍的名字。
一名來臺幫傭的菲律賓女教友,似乎迷上了我的濃眉細眼,她認為一個像樣的大名可以補償我外表的缺陷。於是她翻開舊約聖經,唸了一段經節,然後認真地對我說:「你是士師,你是先知,在那個沒有王的年代,你就是王!……」她沉默了一下,「……你叫『撒母耳』。」
七月十八日(星期三)
仗著有丈母娘在臺北陪妻子當藉口,我今天一送妻子去上班之後,便直接坐火車回臺南。我想要重新開始寫那我一直想寫的三個劇本,那是一個關於臺灣歷史的大戲,那是荷據時期的臺灣,我計畫要以原住民、漢人、荷蘭人等三種角度來寫出三部屬於那個時代的劇本。每一部的開場都是荷蘭人來了,每一部的結尾都是鄭成功來了。我甚至想以三種臺灣特有的動物來詮釋這三種共生的族群。
原住民是鹿,漢人是鯨魚,荷蘭人是蝴蝶。
這是五年前心裡就產生的一個計畫,雖然已經翻閱了無數史料,但至今仍無法完成。如今我的想法已愈來愈成熟,故事的輪廓也愈來愈明顯。這三個劇本……我愈想愈偉大!
我是閒不下來的人,我必須要做些什麼來讓自己生活得有尊嚴,於是我回到臺南。明天我想先去看看麻豆,去看看赤崁樓,去看安平古堡,去看看臺江內海,先讓自己沉浸在那古老的氣氛中,看祖先們的思想能不能也同時進入我的心裡。
我離開了臺北,到了臺南。
七月十九日(星期四)
我起了個大早,本來是想直接出門的,但我早應該知道我兩個弟弟的小孩不會輕易放過我。其實我也滿喜歡和他們玩的。我兩個弟弟共四個小孩,三女一男,從昨天下午我回來後就一直黏著我。
我帶著這群小孩到我祖母那邊走走。祖母老了,行動也不方便,父親乾脆住到那裡就近照顧,順便逃避家庭。
父親是個愛上大海的人,愛上大海的人喜歡自由。自從把店裡的工作交給弟弟之後,他便以大海為家,幾乎不管烈日嚴冬天天下海。我知道家人沒人能了解他,特別是母親,總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向我哭訴父親的怪脾氣。其實我也不懂,總是覺得他為什麼不舒舒服服地待在家裡抱孫子,偏要天天邊打瞌睡邊騎車地到海上捕魚。
我只記得好久以前有一次,他和我約了一大早要帶我出海,我跟著他和他的一個朋友到海邊,才知道原來父親私下買了一艘舢板船。那次他讓我偷偷地躲在引擎旁的一張帆布裡,以躲過海防的檢查,偷偷出海。他開著船穿過這長長的水道,無意地對我說著:「你看!這海這麼漂亮,你們拍片怎麼不會想要拍海呢?」
我當時沒有說話。
今天也一樣,聽祖母說,父親一大早就去海裡了。祖母家有一大片遮陰的空地,每天早上都會有許多老婦人來泡茶,今天也不例外,這些老婦人幾乎全是我的親戚,我卻總是記不得哪個是嬸婆?哪個是姨婆?但她們永遠都知道我是那個在臺北的「大漢仔」。
中午吃完午飯,趁小孩們睡午覺的時候,向弟妹借了摩托車。我計畫先往當年鄭成功登陸的鹿耳門,看看那個改變臺灣歷史的水域。我當兵前曾經在天后宮隔壁的一家水上遊樂場當過救生員,但我的年輕讓我只對穿泳裝的女孩感興趣。
我順著指示繞過天后宮,自大廟旁的小路來到了港邊的小漁村,我突然覺得這個地方很熟悉。當我騎過一條小橋時,看到了泊船的內港,我驚訝地打了個冷顫。這是我父親的港口啊!
我順著港灣騎了一圈,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父親。別說是父親,我甚至連一個人影都沒看見。在這滿是漁船舢板的內港,卻看不見一個人,真讓人感到有點淒涼。
我來到了入海口,這個寫著「海關天險」的歷史關口讓我差點流淚。原來,我已乘著父親的船不只一次地進出過這裡,父親還曾讓我親自操舟,自大海進入這長達一、兩公里的水道吶!
我沒因為曾駕船駛過鄭成功的路線而感動,卻為了從前的無知而流淚。我不知道父親每天航行在這片水域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站在高處往左看,是一間紀念鄭成功的廟宇,廟前豢養著一隻跛腳迷你馬靠在柱子邊喝水;往右看是被蚵架佔去大半、深長的鹿耳門水道。
我望向大海,思緒回到了四百年前的婆娑之洋,福爾摩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