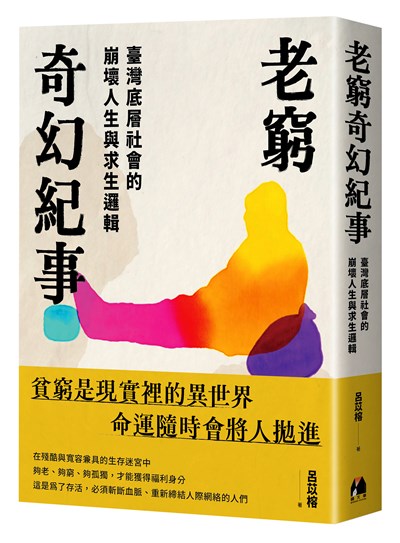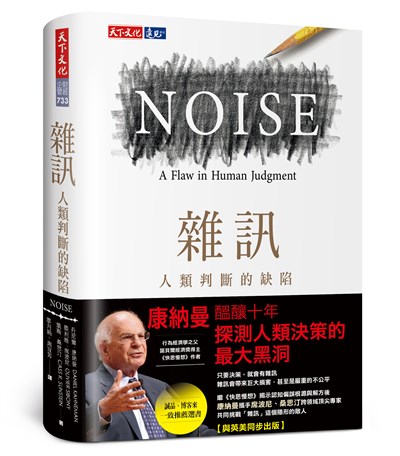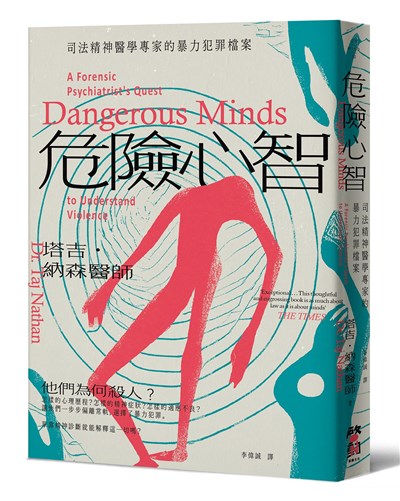人人爆料的時代,究竟什麼是好報導?距今已四十餘年的「水門案」,在政治及媒體角度上都是相當經典的案件,這樁政治醜聞讓人們看見了:當權者因自身權力無限上綱,失去應有的規範;而在政治壓力阻撓下,記者與政界一次又一次的攻防,如同近來巴拿馬洩密文件追查的勇氣,最終挖出了權力核心的腐敗。
文章節錄
《總統的人馬:2名記者、700天追蹤 水門案調查報導經典原著》
「好吧,我告訴你。在一場(競選)委員會的華府會議上,我要不是把支票交給委員會的出納(休.W.史隆二世﹝Hugh W. Sloan, Jr.﹞),就是交給莫里斯.史坦斯本人。」
伍德華等不及要掛斷電話。史坦斯是尼克森的頭號募款人,也是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的財政主席。
現在是九點三十分,距離第二次版截稿只剩一小時。伍德華開始打字:
一張兩萬五千元的本票,顯然是撥款給總統尼克森的競選金庫,在四月存入柏納.巴爾克的銀行戶頭。巴爾克是六月十七日闖入本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被捕、且涉嫌企圖竊聽的五人之一。
最後一張稿子剛剛好在截稿前傳給瑟斯曼。瑟斯曼拿著筆在桌前安靜下來,他轉向伍德華。「我們沒有過像這樣的報導。」他說:「從來沒有。」
※
直到八月一日關於達爾柏格支票的報導刊出前,伯恩斯坦與伍德華間的工作競爭關係無比緊張。雙方都擔心另一個人可能背棄自己,獨自追蹤其後的新聞。假如其中一人利用晚上或週末去追一條線索,另一個會覺得自己也必須這麼做。八月一日的報導刊出兩人的聯合署名,隔天伍德華問瑟斯曼,伯恩斯坦的名字能不能跟他的一起掛在後續新聞上—即使伯恩斯坦仍在邁阿密,並未參與其中。從那時開始,任何水門事件報導都會掛上兩個名字。報社同事把兩個名字結合為一,促狹地把他們的署名命名為伍德斯坦(Woodstein)。
伯恩斯坦與伍德華的相互不信任和懷疑心逐漸消逝。他們了解合作的優勢,尤其因為兩人的個性如此南轅北轍。報導涵蓋的層面、潛在風險與需警惕的地方,全部經由至少兩位致力於此的記者辯證過。藉著分頭出擊再共享資訊,他們擴增了聯繫門路。
雙方各自保有一份電話號碼清單。這些號碼每週至少打上兩輪。(光憑特定線人沒接聽或沒回電,就常是大事發生的預兆。)最終他們名單上的名字加起來擴增到數百人,僅僅不到五十個重複出現。不可避免地,他們會踩到彼此的線。「你們不是一夥的嗎?」一位律師有次問伍德華,「我剛剛才掛掉卡爾的電話。」在另一個場合,有位白宮助理說:「我們試著要搞懂,為什麼我們之中有些人接到伯恩斯坦打來的電話,而其他人似乎在伍德華的名單上。」答案是沒有原因。兩位記者想盡可能避免妨礙到另一個人的工作。通常來說,他們偏好擁有各自的線人,因為這麼做機密消息來源會比較安心:有更多時間可以投入,培養私人情誼。
對那些在編輯室周遭活動的人來說,伍德斯坦顯然不是一座時時運作順暢的新聞機器。這兩人相互爭執,且常在公開場合如此。有時他們會為了一個用字或句子搏鬥十五分鐘。細微差別至關緊要,新聞重點必須命中紅心。探求新聞意義常以最大音量進行,其中一人怒氣沖沖從另一人的桌邊掉頭離開並不罕見。然而或早或晚(通常是晚),報導終將淬鍊生成。
兩人發展出各自的歸檔系統。說來奇怪,是兩人之中行事遠遠較欠秩序的伯恩斯坦,把資料整齊收入黏有姓名標籤的牛皮紙袋,幾乎每個他們遇過的人都有;另外也依主題整理資料夾。伍德華的資料保管得較不正式,但是他們都遵守一條不能違背的守則:他們不丟東西,保留所有的筆記和新聞草稿。很快地,他們塞滿了四座檔案櫃。
通常下筆較快的伍德華會先寫初稿,接著交給伯恩斯坦修潤。伯恩斯坦常常只有時間修潤報導的前半部,使伍德華的後半部像沒塞好的襯衫下襬。這過程常耗去大半個夜晚。
隨著水門新聞的線索和構成面向增加,兩位記者的生活變得幾乎全被工作占滿。而且他們成為朋友,雖然起初小心翼翼。兩人都不需要自己的時間。伍德華離婚了,伯恩斯坦分居中。他們常在編輯室待到深夜,查證資料,讀剪報,勾勒他們的下一步,交換理論。有時候貝瑞.瑟斯曼會加入,最終他放下市政版主編的日常職責,肩負的首要責任是指揮郵報的水門事件報導。
瑟斯曼三十八歲,舉止溫和,稍稍超重,一頭鬈髮,帶著書卷氣。他做過靠近維吉尼亞跟田納西州交界一份小城報紙的編輯、紐約大學的速讀教練、社會版主編,然後是郵報地方版主編—飄泊的記者一路打零工,從布魯克林前進華府。
瑟斯曼有能力掌握資料,並且妥善藏於記憶,準備好隨時可受召喚。所知比郵報任一位編輯,或伯恩斯坦和伍德華還多,瑟斯曼成為水門知識的行動資料庫,連資料室都失手時可以呼叫的參考資料來源。在截稿當下,他會把這些事實源源不絕注入報導中,建構由重要資訊組成的實體,支撐起否則會顯得不具說服力的真相揭發。在瑟斯曼腦裡,一切拼湊成形。水門事件是團謎,而他是碎片的撿拾人。
瑟斯曼本質上是個理論家。換個時代,他或許會成為一位猶太法典學者。他採用蘇格拉底的方式,對記者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誰跟著史坦斯從商務部一起去總統競選連任委員會?米契爾的祕書怎麼了?為什麼沒人說李迪何時到白宮就任,或者他在那裡跟誰一起工作?米契爾跟史坦斯都插手管理預算委員會,對嗎?那件事告訴你什麼?然後瑟斯曼會叼著菸斗吐出一陣煙,咧嘴露出滿足的笑容。
瑟斯曼熱愛歷史跟民調。他的英雄是傑弗遜,而兩位記者總是想像喬治.蓋洛普 緊追在後。每逢反戰運動高峰,城裡上演大規模示威遊行,瑟斯曼幾乎都會派出大批記者去問示威者的年紀、政治傾向、家鄉地,以及他們先前參與過幾次示威。每次他得到的是街上記者早已猜到的相同結論—反戰運動的基礎已變得更廣泛,且較不激進。打從民主黨總部闖入事件發生,瑟斯曼就開始研究哈定政府的茶壺山醜聞 。他對水門事件所抱持的理論,伯恩斯坦跟伍德華不太能理解—此事件跟歷史的必然、戰後美國倫理、商品化以及理查.尼克森脫不了關係。
瑟斯曼與郵報另外幾個編輯在性格上不拘小節。兩名記者從未被指派專跑水門事件。他們感覺只要繼續帶回報導,就不會有問題;假如他們兩手空空,在郵報編輯室的競爭氛圍下,任何事都可能發生。達爾柏格支票報導見報後的幾星期,由於賽門斯和布萊德利對水門事件的興趣加溫,羅森費爾德變得明顯緊張起來。郵報編輯用半挖苦口氣消遣兩位記者(以及更高階層編輯問手下編輯)的不變問題是:「你今天為我做了什麼?」昨天歸於史書,而非報紙。
那成為郵報的工作倫理,始自一九六五年班傑明.布萊德利上台後。一開始他是編輯主任,一九六七年成為總編輯。延攬布萊德利,出於《紐約時報》未必在美國新聞業獨領風騷的想法。
這個願景在一九七一年遭挫,當時時報刊出五角大廈文件。雖然郵報是第二個獲得越戰機密報告複本的新聞機構,布萊德利指出,時報起初的報導「字字見血」。只要憎惡地瞥一眼懶散的記者或編輯,布萊德利就算表達了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