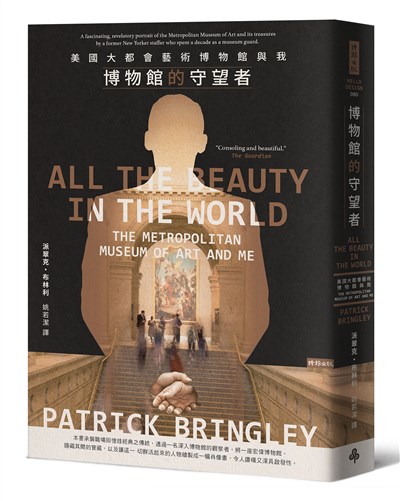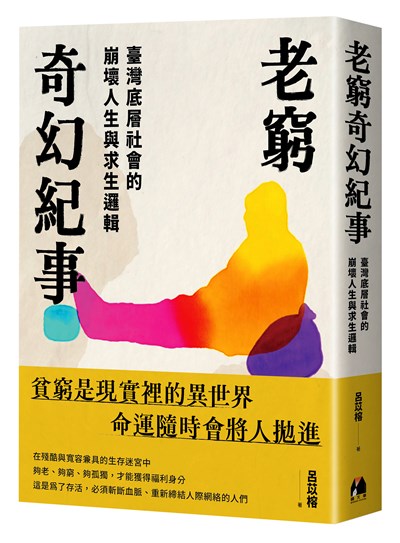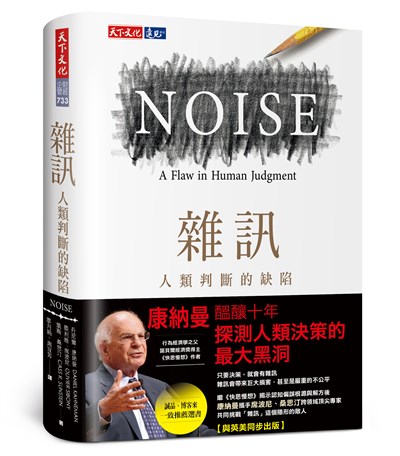當網路讓我們聯繫更密切的同時,是否也逐漸拉開了面對面接觸的可能?是否希望親朋好友能放下手機,專心與我們共處?網路的蓬勃發展,背後產生怎麼樣的人際轉變與心理?如果同樣受困於網路帶來的變化,欲一探究竟,肯定不能錯過科技社會學權威雪莉‧特克的《在一起孤獨》。在本書中,她針對科技與人關係的交互辯證,使讀者理解為何現代人喜歡傳line勝過打電話、為什麼喜歡網路上創造出來的形象勝過真實的自己、為什麼社群媒體讓我們既連結卻又不滿足。如果能有一本書詮釋《攻殼機動隊》、《黑鏡》背後的心理學,那肯定是這本書。
文章節錄
《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
跨世代的不知所措
我研究的青少年都生於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很多人是剛學會走路不久就經由America Online 認識網際網路。但他們的爸媽則是長大成人後才展開網路生活。在這個領域,爸媽是從一開始就在孩子後面追趕的世代。這個模式延續至今:臉書成長最快的年齡層是三十五到四十四歲的成年人。傳統觀點強調成年人與其子女的差別—提出數位世界的移民和「原住民」的根本歧異。但移民和原住民其實大同小異:或許最重要的是不知所措的感覺。如果說被課業和性能力的要求壓得喘不過氣的青少年,是把網路生活當作隱遁和劃清界線的地方;那他們的父母,自稱筋疲力竭的成年人,就是力求對迎面而來的事物有更大的掌控權。而要有效過濾唯有一途:將多數通訊侷限於網路和簡訊。
所以他們永遠開機,永遠在工作,永遠聯絡得到。我記得不過幾年前,曾跟一名朋友和她的兒子一起慶祝感恩節。她的兒子是名年輕律師,剛拿到事務所配發的傳呼器。當時,圍桌而坐的每一個人、包括他自己,都在拿他「合法緊急情況」的概念開玩笑。但到了隔年,他已無法想像不被事務所「奪命連環call」的情景了。曾有一段時間只有醫生才有傳呼器,那是種輪流承擔的「負荷」;但現在,我們全都接受了那種包裝成資產的負荷—或者沒包裝成資產的負荷。
我們為家人和同事隨時待命。某天早上在柏克夏健行時,我遇到四十七歲的曼哈頓房仲霍普。她帶著她的黑莓機,她說她老公可能會想保持聯繫,而他真的每三十分鐘就打來一次。霍普有點半認錯地坦承她「不喜歡」這些電話,但她愛她先生,而他先生需要聯絡她。她恭敬地接聽電話,直到終於有一通收訊不良。「我們出訊號範圍了,謝天謝地。」她一邊說,一邊關機。「我需要喘口氣。」
漸漸地,人們覺得彷彿必須有充分理由才能獨處,有充分理由才能不接電話。當人們想方設法排解科技帶來的壓力,卻又把腦筋動到科技上,這是何其辛酸的事。他們想要過濾軟體和智慧型代理人幫忙處理他們不想看的訊息,霍普和奧黛莉雖然年紀差了三十歲,卻不約而同把簡訊視為解決電話「問題」的途徑。而且兩人都用同樣的方式重新定義「緊張」—發生在現實世界的壓力。想著這點,我的健行同伴說她正試著讓她的丈夫「皈依」簡訊。訊息將有增無減;他能傳的簡訊會比他能打的電話更多,但她不必「事情一發生」就即刻處理。
我們固然對電子通訊的敲擊聲愛恨交織,但這並不代表我們不愛我們聯繫的對象。川流不息的訊息卻使我們不可能找到孤獨的時刻,包括其他人不對我們表示依賴或鍾愛的時刻。獨自一人時,我們並未排斥世界,而是有空間思考我們自己的想法。但如果你的手機永遠在身上,尋求孤獨看來可能與躲藏並無二致。
我們用持續不斷的連結塞滿每一天,不給自己思考和作夢的時間。一旦忙到消耗殆盡,我們又作成浮士德式的交易,大概像這樣:如果我們在與人聯繫的同時又能不被打擾,就足以應付在一起的情況。
波士頓一家大醫院一位三十六歲的護士,以探視母親展開一天的生活。接下來她會採買食物、打掃房子,準備上班。在八小時的輪班和晚餐後,時間已過晚上九點。「我沒有社交的心情,」她說,「我甚至沒力氣用電話追蹤誰的近況。我護校的朋友分散全國各地。我會寫幾封電子郵件。只要上臉書,感覺就沒那麼孤單。就算人們不在那裡,但只要我上去,就好像他們在那裡一樣。我看到他們的新照片、知道他們最近在做什麼,就覺得趕上進度了。」一個五十二歲的寡婦過去長期擔任志工,常有人順路經過找她喝下午茶。現在她擔任全職的辦公室經理,還不習慣新的作息,說她「有點驚訝地」發現自己不再打電話找朋友,傳電子郵件和臉書訊息就滿足了。她說:「打電話感覺像是打擾,彷彿我硬要叨擾我的朋友。反過來說,如果他們打給我,我也覺得被打擾……下班後我只想回家,上臉書看幾張孫子傳的照片,寫幾封信,感覺與人聯繫。我累了。我沒準備跟人打交道—我是指親自碰面。」兩位女士都覺得被以往提供支持的東西:電話給愚弄了。電話的設計有瑕疵,因為它必須即時反應。一開始,逃往電子郵件是疲倦的「解藥」,最後,那使人再也提不起勇氣打電話,更別說「親自碰面」了。五十多歲的法學教授丹指出,他從來不「打斷」工作中的同事。他不打電話,也不要求見他們。他說,「他們或許在工作,做某件事。可能不是好時機。」我問他這是不是新的做法。他說:「噢,是啊,我們以前會出去,那很不錯。」為什麼曾經的同僚型行為,如今會構成干擾?他說:「現在人們比較忙。」但隨後頓了一會兒,糾正自己:「我沒有完全從實招來:這也是因為現在的我不想跟別人說話,我不想被打斷。我覺得是該講講話,那應該挺不賴的,但用我的黑莓機跟人打交道比較容易。」
這種廣為蔓延的態度讓二十五歲的休伊更難處事;他說他「需要的不只是電子郵件和臉書能提供的東西。」如果他的朋友沒有時間見他,他希望他們跟他講電話,這樣他才能擁有「整個人全心全意的關注」。
但當他傳訊給朋友說他想用電話聯絡時,休伊說,他得清楚表明他的意圖:他想要「私密的手機時間,」他解釋:「你打電話的對象必須承諾他們不會接聽其他人的來電,沒在做別的事情。」他說讓他覺得被嚴厲拒絕的是:在和朋友講電話的時候,他察覺朋友也在傳簡訊或上臉書,而這種事不時發生。「我甚至希望他們不要走動。如果對方正在從這個銷售會議到另一個銷售會議的路上,我沒辦法跟他進行嚴肅的對話。私密的手機時間是最難得到的東西,人們並不想做那種承諾。」
有些年輕人—需要簡訊和電話來「聯絡基地」的狂熱分子—呼應了休伊對難以得到「全心全意關注」的感嘆。一名十六歲男孩說:「我會跟對方說,跟我說話。現在是屬於我的時間。」另一名男孩則試著要求朋友打室內電話給他,因為那代表雙方是在同一個地方講電話,而且收訊清楚。他說:「最好能讓對方用室內電話回電給你……最好不過了。」
在毫無干擾的情況下講室內電話曾是日常事務,現在則獨樹一格,猶如人間極品。
休伊表示,最近,每當他得到私密的手機時間,最後都不免後悔。要求別人坐下來、除了跟他聊天外其他什麼事也不做,這是把標準提得太高:「如果我不是要講憂鬱啦、考慮離婚啦、被炒魷魚啦之類的事情,他們會大失所望。」休伊笑著說:「你要求私密的電話時間,就最好履行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