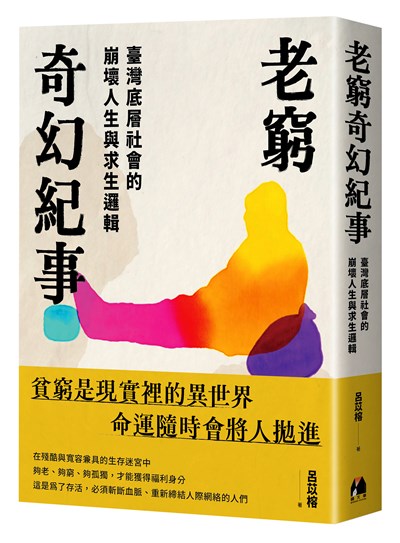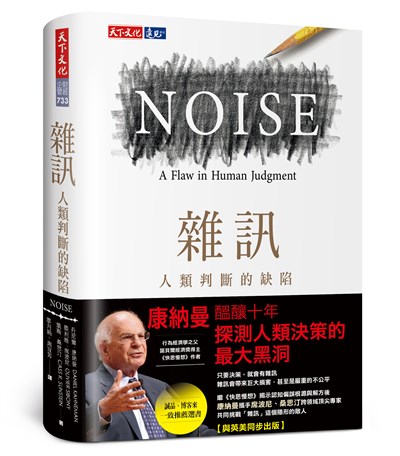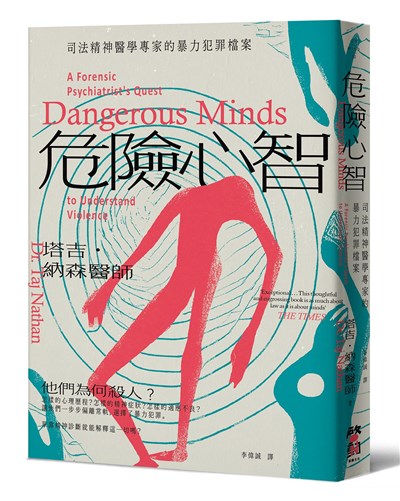繼《如何獨處》後,這次法蘭岑將焦點回到專注已久的主題:人、環境與文學,對生態環境的關注,科技生活對人生活影響的憂心,好友自殺內心的悲傷,透過與這些議題的對話,真實感受世界,審視自己的內心,帶我們到觀點的遠方、思想的遠方、閱讀的遠方。
文章節錄
《到遠方:「偉大的美國小說家」強納森‧法蘭岑的人文關懷》
我念大學四年級時,修了那所大學第一次開設的文學理論研討課,愛上班上最優秀的學生。我們倆都喜歡文學理論讓我們頓覺自己力量強大——這跟現代消費科技類似,我們志得意滿地以為,比起那些還在細讀冗長乏味老派文本的孩子,我們成熟世故得多。基於種種假設性的理由,我們覺得結婚應該滿酷的。我的母親,她花了二十年讓我變成一個渴望全心投入愛情的人,這時卻一百八十度大逆轉,建議我三十歲之前應該(照她的說法)「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很自然地,既然我覺得她什麼都錯,這件事當然也不例外。我經歷了一番艱苦才明白,全心投入是多麻煩多混亂的事。
我們拋棄的第一樣東西是理論。我即將過門的妻子曾在一次不愉快的床上經驗後說了一句令人難忘的話:「你不能一邊解構文學一邊脫衣服。」我們有一年時間分隔兩個大陸,很快發現,即興揮灑理論,填滿給對方的信固然有趣,但讀起來就沒那麼有趣了。而真正為我殺死理論——開始全方位治療我、讓我不再執著自己在他人心中模樣的,是我對小說的愛。修訂一篇小說,或許跟修訂你的網站頁面或臉書檔案有異曲同工之妙,但一頁文稿並沒有亮麗的平面藝術幫你提升自我形象。如果你被別人的小說深深打動,也提筆寫一篇,寫到後來你會無法忽視自己的稿子中虛假或二手的成分。你筆下的內容同時也是一面鏡子,真心愛小說的人會發現,值得保存的只有反映真實的你的那幾頁。
當然,這裡的風險是拒絕。我們都能消化偶爾的不被喜歡,因為喜歡你的人可能有無限多。但一旦你暴露完整的自我而不只是討人喜歡的表面,卻遭到拒絕,就可能痛不欲生。就是這種可能的痛,舉凡失去的痛、分手的痛、死去的痛,讓我們亟欲避免去愛,只想安全地待在「讚」的世界。內人和我,太年輕就結婚,最終放棄了太多自我而帶給對方太多痛苦,以致彼此都有理由後悔當初的不顧一切。
然而,我實在沒辦法讓自己後悔。首先,我們難以信守承諾的掙扎,正說明了我們何以為人。我們不是氦分子,一輩子了無生氣地漂浮;我們會結合,會改變。其次——或許這才是我今天要傳達給大家的主要訊息——痛固然痛,但要不了命。當你考慮另一種選擇,放棄被科技點燃自信的醉人幻夢,痛,就成了活在你所抵抗的世界的自然產物及指標。無痛地度過人生,就等於沒有活過。就算只是對自己說:「噢,我晚幾年再來經歷愛情和痛苦,或許三十幾歲吧。」也是把自己託付給另一個十年,在這顆星球徒占空間耗用資源的十年,當個(我用的是這個詞最該死的意義)消費者。
我前面所說,全心投入所愛的事會如何迫使你面對真實的自己,或許特別適用於小說寫作,但也適用於任何你用「愛」去做的工作。我想在這裡談談我的另一個愛,做為總結。
我從念大學到畢業很多年後,很喜歡自然世界。不算愛,但肯定是會按讚的。大自然有非常非常美的一面。既然我被文學批評理論煽動,一直在想方設法挑世界的毛病,尋找厭惡世界經營者的理由,我自然而然受環保思想吸引,因為我們的環境無疑問題重重。而我愈是檢視不對勁的地方——世界人口爆炸、資源消耗程度爆炸、全球暖化、海洋垃圾污染、最後幾片原始林慘遭砍伐——就愈怒火中燒,愈討厭人。最後,約莫在我婚姻崩解,覺得痛是一回事,但要在更憤怒、更不快樂中度過餘生是另一回事時,我做了一個清醒的決定:不再擔心環境的事。我無法以一己之力對地球做出任何有意義的拯救,但仍想繼續為我愛的大自然奉獻心力。我仍試著減少碳足跡,不過,那是我不再掉回憤怒和絕望的極限了。
然後,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說來話長,但總歸一句,我愛上鳥了。我不是沒有竭力抗拒過這份愛,因為當個鳥類觀察家很不酷,因為任何洩漏真情的事一定不酷。但一點一滴,不由自主,我發展出這股熱情,雖然這股熱情有一半是著迷,但也有一半是愛。所以,沒錯,我就我見過的鳥類列了一份嚴謹周密的清單;沒錯,我竭盡所能觀察新鳥種,但同樣重要的是,每當我看著一隻鳥,不管哪種鳥,就算是鴿子、麻雀,我都能感覺到心裡洋溢著愛。而愛,一如我今天試著說明的,是我們麻煩的開始。
因為現在,我不只喜歡大自然,還對它明確而重要的一部分有了深切的愛,所以別無選擇,只好又開始擔心環境。環境的消息並未比先前我決定不再擔憂時來得好——事實上是糟得多——但現在,那些受威脅的森林、濕地、海洋不只是讓我徜徉的明媚風光,還是我愛的動物的家。而且,這裡浮現了奇怪的矛盾:我對這顆星球的憤怒、痛苦和絕望,固然隨著我對野鳥的關注而變本加厲,但,當我開始投身鳥類保育、深入了解鳥類面臨的諸多威脅後,說來奇怪,我卻變得更容易,而非更難與我的憤怒、痛苦和絕望相處。
為什麼會這樣?我在想,首先,我對鳥的愛儼然成為一個入口,通往心中一個重要、但沒那麼自我中心的部分,我從不知道有這東西存在的地方。我不能再以地球居民的姿態一輩子漂流,不能再只管喜不喜歡而把承諾留給未來,反而被迫面對「要不就徹底接受,要不就斷然拒絕」的自我。這就是愛會對人做的事。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不脫這個基本事實:我們會再活一陣子,但終有一死。這個事實才是我們憤怒、痛苦和絕望的真正根源。你可以逃避這個事實,或者,透過愛來擁抱它。
前面說過,鳥完全出乎我意料。大半輩子,我未曾為動物費過多少心思。或許我那麼晚才找到通向鳥的路算是不幸,也或許能找到就算幸運。總之,一旦你撞上那樣的愛,不論早晚,它都會改變你和世界的關係。以我為例,經過幾番嘗試,我仍放棄新聞寫作,因為真實的世界不像虛構的世界那樣令我興奮。但在皈依鳥類令我奔向痛苦憤怒絕望,而非逃之夭夭後,我開始接受一種新的新聞寫作類型。在某個時候,我最憎恨的東西成了最想要的東西。二〇〇三年夏天我去華盛頓,當時布希政府正對這個國家做一些令我火冒三丈的事;幾年後我去中國,因為那段時間,中國對環境造成的浩劫讓我輾轉難眠;我前往地中海,採訪宰殺鳴禽(一種候鳥)的獵人和偷獵者。在以上的例子裡,每當面對敵人時,都會遇見我真的很喜歡——甚至立刻愛上的人。搞笑、大方、優秀的男同志共和黨幕僚;無所畏懼、不可思議、熱愛自然的中國年輕人;還有一個愛槍成癡的義大利國會議員,眼神非常溫柔、會對我引用動物權倡導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話。在上述的例子裡,過去那麼容易在我心底蔓延的全面性憎惡,已不再那麼輕易滋長了。
當你像我過去很多年那樣,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間裡憤慨、冷笑或聳肩,這世界和它的問題依然那樣驚心動魄。但當你走出去,讓自己和真實的人,甚或只是真實的動物發展真實的關係後,你便會面臨非常真實的危險:最後可能交付出「愛」的危險。誰會知道接下來可能發生什麼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