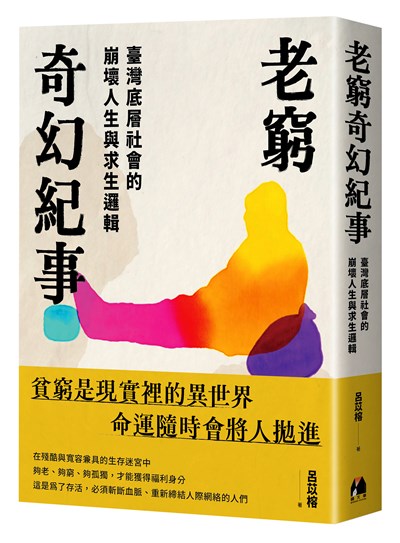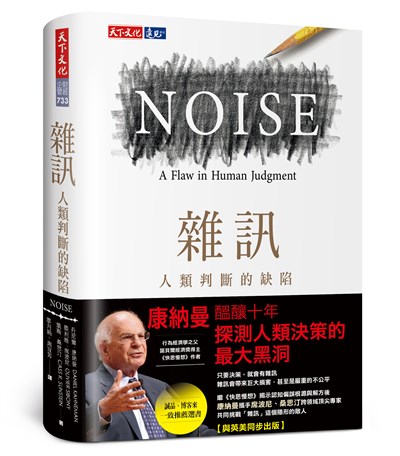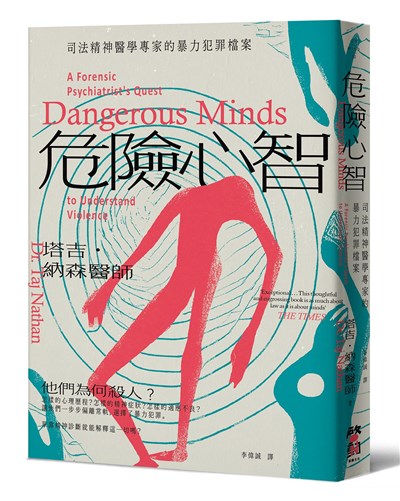2018 Openbook好書獎-中文創作
評審推薦語/李令儀(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清大社會所兼任助理教授)
我們的社會裡有這麼一群青少年,出生於貧困、父母長期失業、至親重病、嗜賭或入獄等「高風險家庭」。他們長期過著失落、失學、失業的日子,甚至因家庭失能而安置在兒少機構。這些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少年,為數近兩萬人或者更多,卻往往被我們忽視。然而,主流社會的漠視和排除,更將他們往社會底層推,低學歷、低技術、低薪的條件限制,讓他們落入難以向上流動的惡性循環。
繼去年的《血淚漁場:跨國直擊遠洋漁業真相》之後,《報導者》團隊再度交出直擊社會議題的重要調查報告。除了訪查上百名邊緣少年,以血淚個案深描他們的身心靈困境之外,書中也挖掘造成廢墟的結構性因素,檢討缺乏統整「分割式」的政策,並提供香港、南韓相關機構的另類做法。
弱勢少年的故事雖然讓人嘆息,讀來備感沉重,但即使是廢墟,也仍舊看得見曙光。善意之光來自中小企業主提供的工作機會、補救教學老師的陪伴,或是寄養家庭母親的愛與包容。這些援助和關懷之手,牽引少年與社會、社群取得連結,找到走出廢墟的契機。《報導者》團隊的系列報導,已初步讓有權者、讓我們「看見」這些少年的處境,但是若要清掃廢墟、就地重建,則需要大家一起審視並改善造成廢墟的結構性因素。這本調查報告,因而是召喚你我一起思考和行動的起點。
——轉載自《Open Book閱讀誌》
文章節錄
《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廢墟裡的少年──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
1
十三歲的小傑被送到中途之家時,還有幾顆乳牙沒落下,個子清瘦、營養不良;他被分配到十人一間的上下鋪,生輔老師管教嚴格,小傑卻滿足得露出可愛的小虎牙,他說這是第一次感到被關愛。
七、八歲懂事時,他就看著父母、兩個舅舅跟著阿公阿嬤吸毒、販毒,大人們總呼朋引伴窩在房裡,共用針頭與吸食器,屋裡充滿濃烈的塑膠味;狂歡後,歪斜的針頭、乾掉的血漬,就由家中唯一清醒的小傑善後。小傑說:「他們一旦這樣做(吸毒)我就很不喜歡;安非他命、海洛英、大麻,因為他們沒有一個人會管我,我就等於一個人,像鬼一樣……」
全家六位大人在過去幾年間,因販毒相繼入監,被通緝的阿公最晚入獄。有長達三年的時間,阿公「跑路」到外縣市避風頭,小傑白天上學,晚上與阿公會合,早上再由阿公送他回學校。這讓他在上課時總無精打采,時而中輟;而當阿公也被逮了,他就開始了一個人的生活。
失去家人照料的小傑,來到一所專門留容國中中輟生的學校,在這裡他遇到與他生命經歷一樣艱苦的少年:A的父親長期失業後酗酒不顧家庭,B的外配母親被父親家暴離異,C幾乎被棄養,為生存曾偷竊、討債。
臺灣有一群少年,正過著和自己年紀極不相稱的生活,遭遇多數成人一輩子也未曾面對的幽暗。他們之中,多數來自政府定義下的「高風險家庭」。
高風險家庭下的少年
高風險家庭有其複雜的成因,有的是父母入獄,難以照料子女,也包括照顧者因貧困、失業、重病、罹患精神疾病等,無法照顧家中孩童。從二○○五年開始,政府啟動高風險家庭的通報系統3,為面臨風險的兒少,提供預防服務。
根據衛福部統計,過去三年,高風險家庭通報數從二萬五千戶增加到近三萬戶,牽涉的孩子高達四萬三千名。這之中,十二歲到未滿十八歲的少年,就有近一萬六千名。而臺灣每年有約五千名風險程度更高的兒少,因家庭失能,必須送入安置體系。臺灣風險家庭下的少年,初步估計超過兩萬名。
臺灣一年不到二十萬個孩子出生,生育如此辛苦,但這些少年活在家庭失能與欠缺社會支援、如同廢墟的狀態裡,是一群幾乎不被國家看到的存在。
長期關注高風險家庭的政務委員林萬億說,這些年臺灣的高風險家庭數持續成長,在通報之前,孩子們早已傷痕累累,「我相信還有一些黑數沒有被通報。」 除了未通報的黑數,是否開案,與縣市資源和評估品質有關,也使得社工目前開立個案服務的量相對低。
偏鄉裡的脆弱家庭
沿著國道三號,距離熱鬧的斗六市,僅十五分鐘車程的林內鄉,彷彿是個心跳停止的地方,沒有活力的所在:青壯人口大量外移,留下老幼和失能者孤零勉力地生存著。
十六歲阿姚的家,是個縮影。
走過堆柴的大院,屋子裡巨大神明桌上頭擺著關公、媽祖、千手觀音、唐三藏等神明,牆頭紅紙寫著「朝朝暮暮神降臨」。牆壁處處龜裂,陰暗處蜘蛛結網。阿姚領著我們到他的房間,唯一的燈泡連著電線頭搖晃空中,裡頭一團黑,書桌上擺著刺青機和一瓶開封喝去半罐的烈酒。
阿姚的母親不到四十歲,跟五個男人分別生了六個小孩,戶口名簿上登記的父親,是母親的第一任丈夫,至今他不清楚自己生父是誰;做乩童的阿祖和姨婆負責照顧這群同母異父的孩子。他從小被放養自找生路,小四時就與家庭背景相似的同伴瞎混,跟著
「會館」出陣頭。
「我早餐沒錢買,沒辦法,就去會館,去一次(陣頭),擋得了一禮拜,」他說。每次出陣頭八百或一千元的紅包,夠他吃飯、抽菸、買酒。長期扛轎,他的背厚實而圓拱,卻也壓縮了身高。
農村的早婚、複雜的婚姻、重組的家庭、脆弱的經濟……阿姚只淡淡地說:「我哪會按呢,很衰,出生在這種的(家庭)。」他胸肩到右上臂的半甲刺青刺著大大的八爺,面對陌生人經常露出防禦的眼神。他喝酒抽菸拉過K,曾因拿磚頭傷人、結夥械鬥,短暫進過少年觀護所。他用身體對抗自己和社會,抗議生命裡的各種磨難。
來自雲林的立委劉建國,是少數理解在脆弱家庭成長是什麼模樣的成人。父親在他八歲時過世,不識字的母親一人做工、幫傭,扶養五名子女。劉建國還記得他得負責騎腳踏車到廟裡領紅包、棉被、米和醬油,他在求學階段被歧視,目睹母親被欺負,「那時的我,其實就是高風險家庭的孩子。」
那不只是窮困,那種困是「負」的,負到當少年有一點行為能力時就得扛,或是逃。
過去二十年,這個問題不斷在惡化,劉建國觀察到,雲林的「三多」增加了:單親外配多、隔代教養多、失業者多;他們共通的處境是近貧。他說,雖然家貧不一定失去功能,但只要主要的照顧者罹病或失業,整個家就深陷困頓之中,「而且在六都之外,城鄉差距愈差愈大、愈來愈恐怖、愈來愈離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