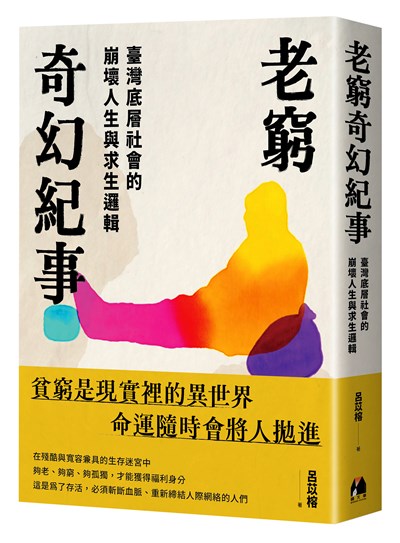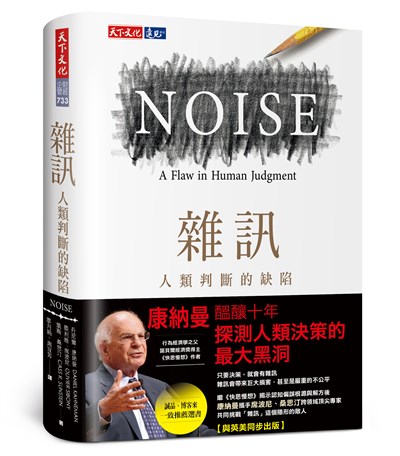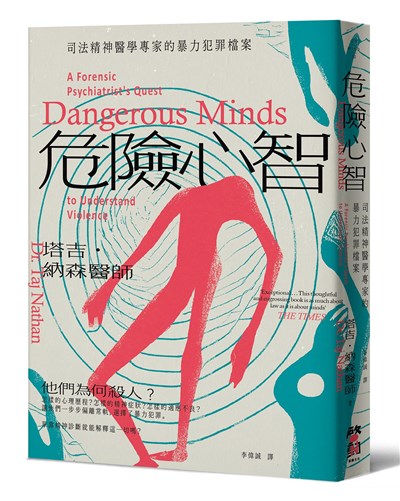什麼是信仰傳統最重要的核心呢?透過回溯六千年來宗教歷史的演變與發展,英國極負盛名的宗教學者阿姆斯壯女士帶領讀者返回前現代世界之前,尋找宗教最具價值的神聖、靜默、超越性的傳統,並為我們這時代作診斷,也試圖重建可以讓現代人感到滿足的現代宗教論述。
文章節錄
《為神而辯:一部科學改寫宗教走向的歷史》
第十一章 未知
從一九二〇年代的科學革命開始,越來越多人相信「不知」是人類經驗中無法根除的一部分。一九六二年,美國學者孔恩(Thomas Kuhn)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既批判波普系統性否證現存科學理論的學說,另一方面也挑戰一種舊信念:科學史是一場線性、理性、不帶包袱的進步,在客觀真理上直奔更加精準的成就。孔恩認為,累積假設檢驗只是科學史的一部分而已。在「常態」時期,科學家們的確是邊做研究邊檢驗自己的理論,但他們並不是朝新真理而行,只是為了確證當時的科學典範。老師和課本也都以支持當前流行的正統理論為目標,傾向忽視所有對它構成挑戰的證據;換句話說,因為典範與神學教義無異,也會形塑信念並強化頑固,所以科學家無法突破時下通行的典範。可是,「常態」時期之後就是戲劇化的典範轉移(一九二〇年代便是如此)。由於不確定性和令人疑惑的實驗結果不斷出現,累積到不容忽視的程度,科學家們開始為找出新典範相互競爭。這個過程並不理性,裡頭充滿出乎意料的嘗試,憑藉想像朝未知一躍,而且這些摸索都受到其他領域的隱喻、意象和假設影響。孔恩認為美學、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也參與了科學發展,所以「純科學」這種理想其實是虛構的。一旦新典範站穩腳跟,另一個「常態」時期也隨之開始。科學家再次為維護新模式努力,忽視可能戳穿它並不完美的線索,直到下次重大突破發生。
帶著新啟示的力量降臨早期近代世界的科學知識,似乎與我們從人文學科中獲得的知識並無根本不同。在《知與存有》(Knowing and Being)中,化學家和科學哲學家麥可.波拉尼(Michael Polyani,1891-1976年)主張,所有的知識都是默會的(tacit),不是客觀而有意識地習得的。波拉尼讓人留意到實務知識的角色;由於近現代時期看重的是理論知識,實務知識的重要性被嚴重忽略。舉例來說,我們無法精確解釋怎麼游泳或跳舞,學會了就是學會了;我們也無法詳細說明怎麼認出朋友的臉,但就是認出來了。我們對外在世界的感知不是機械而直率地吸收資料,而是將大量事物統整成焦點式的覺知,將它們放進深植於我們之中的詮釋框架(但這框架埋得太深,我們無法讓它外顯)。統整的速度和複雜性遠遠超過相對笨重的邏輯或推論過程。事實上,在知識變成默會之前用處很小。學會開車之後,「駕駛手冊就轉入潛意識裡,幾乎完全化為技能的默會操作」。
學某種技能時,我們得扎扎實實寓於(dwell in)無數肌肉動作,儘管操作時並不完全知道自己是怎麼做到的。波拉尼認為求知過程都是如此;我們內化某種語言或一首詩,「讓自己寓於其中。這些展延在我們之內發展出新的官能;我們整個教育就是以這種方式發揮作用;當我們每一個人內化文化遺產,文化便成長為人,以這樣的眼光觀看和經驗生命」。這種看法與卡帕多奇亞教父有相似之處,後者堅持學習關於神的知識不只要靠大腦,也得以身體參與教會聖禮傳統。聖禮能啟發人嘗到某種形式的知,這種知沉默無言,也無法清楚表述。
波拉尼認為,科學方法並不單純是從無知到客觀的進步,它也包括更複雜的、從外顯知識到默會知識的運動。在這個面向上,科學和人文學科其實很像。為推進研究,科學家們經常得相信他們知道將來會被推翻的事,可是他們又無法確知目前的哪些信念以後會被拋棄。因為無法證明的假設太多,科學研究永遠得有宗教人士稱為「信仰」的要素——也就是在愛因斯坦相對論還沒有經驗證據時,物理學家對相對論抱持的那種信仰。
科學理性主義以解決問題為重,這種方法也的確帶來系統性進展:解決一個問題之後就把它放在一邊,科學家們繼續向前解決下一個。可是人文學科不是如此,因為它們處理的是死亡、悲傷、邪惡和幸福的本質這些大哉問,這樣的問題無法一勞永逸解決。我們可能得花一生的時間玩味一首詩,它才會揭露它的全部深意。這種沉思的運作方式或許與推理不同,但並不因此就不理性。它像是海德格說的「思考」,是反覆的、遞增的、接收的。法國哲學家馬塞爾(Gabriel Marcel)這樣區分「問題」(problem)和「神祕」(a mystery),前者「擋我去路」且「全然現於我前」,後者則「讓我沉浸其中,而其本質不全然現於我前」。我們得挪開問題才能往前進,但對於神祕,我們是情不自禁涉入其中——就像希臘人投入艾留西斯祕儀與死亡相搏一樣。馬塞爾說:「神祕是我親身涉入的東西。因此,我只能把它想成某個領域,在這領域裡,『在我之內』和『現於我前』的界線失去意義、也失去最核心的效力。」我們永遠可能把神祕變成問題(這也許是現代人常遇上的誘惑),再試著以相應的科技解決它。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偵探故事也是以問題解決模式為基礎,冠上「神祕」之名。可是對馬塞爾來說,這是「根本惡行」,是「知性墮落」的症狀。
對於知識追求,哲學家和科學家開始回到更具否定風格的途徑。然而杜尼修、多瑪斯和艾克哈的這項傳統已在近現代時期滅頂,大多數宗教團體沒想到它。他們仍舊以近現代的方式思索神,把神當作客觀實在。神「就在那裡」,可以像其他存在物一樣分門別類。舉例來說:一九五〇年代時,我滿懷真心記下天主教教理問答中「天主是什麼?」的答案:「天主是至高之靈,唯有祂自立自存,在所有圓滿中俱為無限」。杜尼修、安瑟倫和多瑪斯聽了恐怕會從墳墓裡驚醒。「界定」(define)的字面意義既是「設立限制」,我們豈可界定必然超乎一切言語和概念的超越實在?教理問答竟毫不遲疑地答是。
並不令人意外的是,許多深思之士無法信仰這個既遙遠又抽象的神祇。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咸信世俗主義即將成為新的意識形態,而宗教不再能在公眾生活中呼風喚雨,但無神論依然不是簡單的抉擇。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說人類意識中有個神狀的洞,那是神聖一直以來待的位置。對我們所說的「神」的渴望內在於人類本性,這份渴望承受不了宇宙完全沒有意義。可是沙特主張,即使神存在,我們也必須拒絕祂,因為祂否定了人的自由。這種信條可不讓人舒服,它要人硬起心腸接受我們的生命沒有意義。這種壯烈行動將自由神化,但也否定了我們天性中很根本的部分。
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毅然捨棄十九世紀將人性神格化的夢想。人必有一死,這讓人生失去意義,是以任何試圖理清人類實存的哲學皆為幻覺。我們必須在沒有神的情況下自立自強,將愛的一切牽絆和關懷都投注於這個世界。可是,這並沒有辦法解放世界。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1942年)裡,卡繆指出,想拋下神,人必須終身投入絕望而不合理的奮鬥。古哥林多王薛西弗斯熱愛生命,憎惡死亡,但因反抗眾神遭到天譴,被罰永遠要做徒勞無益的苦差事。薛西弗斯每天都得從山腳推巨石上山,但石頭一到頂峰就滾下來,他只能日復一日重複同樣的過程。這深刻描繪出人生的荒謬,局中人甚至無法在死亡裡安歇。知道自己還沒開始就注定失敗,我們還可能獲得幸福嗎?卡繆認為,如果我們能睥睨眼前的死亡與荒謬,使出全力創造自己的意義,那麼我們還是可能獲得幸福:
我就留薛西弗斯在山腳下吧。一個人總是會發現他的重擔。但薛西弗斯展現一種更高的忠實:否定諸神,扛起巨石。他也認定一切都很好。這個此後再沒有主宰的宇宙對他來說既不荒瘠,亦不徒勞。組成那塊石頭的每個微粒,暮色籠罩的山陵的每片礦岩,本身便形成一個世界。朝向山頂的奮鬥本身,就足以填滿人心。我們應當想像,薛西弗斯是幸福的。
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很多人發現拋棄神並不能帶來美麗新世界。在人類存在的理性中,我們嗅不出啟蒙運動沉穩安詳的樂觀氣氛。卡繆擁抱這種未知,他不確定神是否存在,但他選擇相信神不存在。我們必須與無知共處,一起活在對我們的問題始終緘默的宇宙裡。
可是,卡繆過世還不到十年,世界已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反叛力量直接挑戰現代性氛圍,新的宗教追求興起,新型無神論也紛紛出現。雖然無知似乎是人與生俱來的限制,但人對確定性的強烈欲望還是貪如饕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