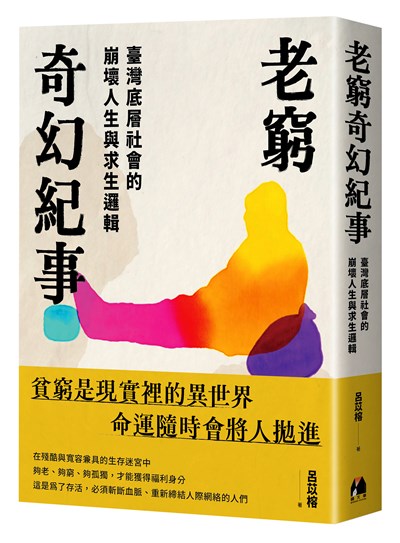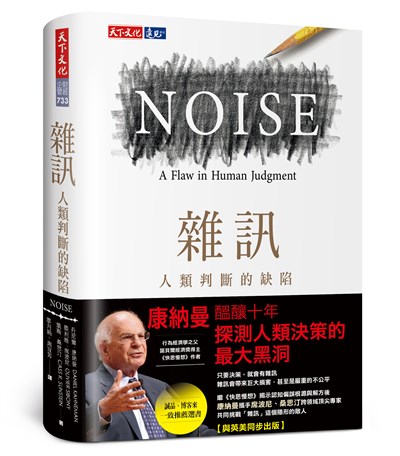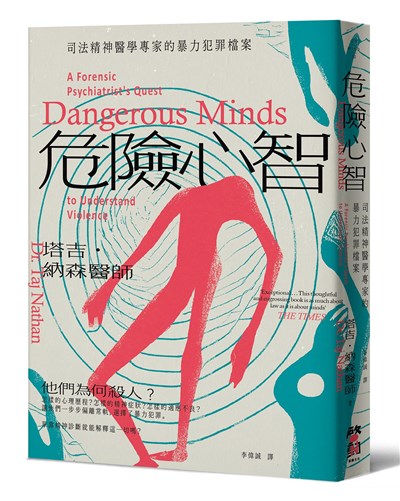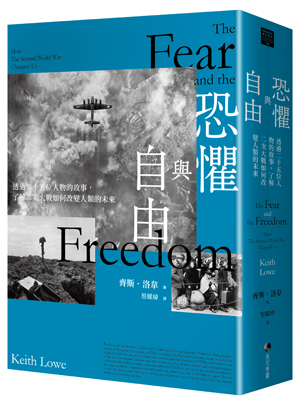
《恐懼與自由》是《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的姊妹作品,本書利用二十五位大人物、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描繪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都面臨巨變的世界。恐懼,甫因為兩顆原子彈而結束大戰的世界,人們都知道,下一場全球戰爭恐怕會導致實際上的末日,而非象徵上的末日。自由,戰後世界各地的人們急於從各種壓迫力量解放出來,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至今依舊如此。
文章節錄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只是災禍的年代,也是英雄的年代。有一個人知道被稱譽為戰爭英雄是怎樣一回事,他名叫李歐納.克里歐(Leonard Creo),曾是美軍第二三二步兵團的一名步兵,而他的故事恰好足以呈現英雄的美名何其強而有力、同時又何其空洞。
在克里歐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許多開端。
1
這位在紐約生長的青少年,清楚意識到了一九三九和一九四○年突然席捲歐洲的動盪:他曾萬分激動地收聽新聞報導,「彷彿那是場美式足球比賽」。到了一九四一年底,當日本轟炸珍珠港、美國被捲入戰爭中,局勢變得更為切身。三個月後,他以十九歲之齡志願投身陸軍:起先擔任砲兵,隨後被重新培訓為通信兵,而後再次受訓成為四十二步兵師的一名步槍兵。但直到一九四四年,他才終於登上了開往歐洲的運兵船,他的戰爭從此真正開始。
克里歐在那一年年底首先登陸法國。他的單位作為整個師的先頭部隊,被派往德法邊界的前線,加強史特拉斯堡市(Strasbourg)的防務。這座城市尚未獲得確保。大量美軍部隊被抽調到更北方參與其他戰役,使得這段前線僅有稀薄的守軍,克里歐經常發現自己或多或少獨自一人在戰線上巡邏,或獨自守衛萊茵河的一小段。
一九四五年一月某日,德軍從河流對岸發動攻擊。隨後發生的事在他腦海裡一片模糊。他為了避免被殺,從一處據點奔向另一處。他向敵軍發射火箭筒。他不記得自己害怕,只覺得興奮─「我高興得要死!」但他隨後被一顆子彈擊中肋部,德軍一枚砲彈又在他身邊爆炸,破片插滿了他的腿。「我的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接著是一連串其他的結局。克里歐接受緊急治療之後被送回美國養傷。即使嚴重傷殘,但陸軍並未將他除役,而是留下了他,準備讓他在康復後從事後備工作。
他在長島慶祝了歐戰勝利日,但不太熱情,因為他知道戰爭還沒有真正結束:還要打敗日本才行。他更加熱烈地慶祝了投下原子彈,以及對日戰爭勝利,因為這些結局更為毅然決然。但他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才正式除役。
圍繞著這許多戰爭結局的氛圍,是徹底的改頭換面。師長得知克里歐在史特拉斯堡的功績,頒授了一枚銅星勳章給他。嘉獎詞提及克里歐「英勇不屈」,以及他「面臨凶殘的機槍及砲火」,仍「隻手」阻止敵軍渡河。這些話足夠讓任何人以自己為榮。
2
於此同時,幾乎「所有」歸國的大兵都在美國得到英雄式的接待。他們對國家的貢獻獲得《軍人權利法案》(G. I. Bill)正式認可,法案賦予他們諸多優待,包括低利貸款、免費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失業時每週二十美元、為期一年的保障收入。克里歐最終運用了這些供給,在大學學習藝術─這在戰前根本不可想像。大學畢業後,他也運用豐厚的傷殘津貼自給,得以逐步確立藝術家的名聲─藝術家成了他的終生志業。像克里歐這樣的人,在戰後的發展當然是一片光明。
這種對待退伍軍人正式及非正式的尊重態度,終其一生都伴隨著他。克里歐經常被稱作英雄─有時是通稱,但有時專指他的戰時紀錄和勳章。這個稱號一度令他心滿意足,但後來卻令他愈來愈尷尬。當他回想起史特拉斯堡的那天,他意識到嘉獎詞裡的某些具體細節並不準確,再說,他的所作所為或許也並不特殊。「任何一個普通人在那種局面下就是會這麼做。你沒有逃走的話,就會那樣做。」不僅如此,「戰爭結束時,他們決定每一個參與過實戰的步兵都應當獲頒銅星勳章,於是我的銅星又加綴了橡葉裝飾。意思是我得到了兩個(勳章)。第一個毫無價值,第二個不具意義。」
今天,他發現二戰老兵自動獲得的讚揚「令人不適」而且「荒謬」。他從不參加戰爭紀念活動,因為他不能忍受那種只憑著年齡和軍服,就把每一個廚師和文書都變成英雄的文化。「我們每過一天就會看到愈來愈多奉承,因為我們的人數愈來愈少。很快他們就會看到最後一個,就像他們對最後的一戰老兵那樣。然後他們就會在某個小人物身上施加一切讚美,而那人說不定只是A連的文書之類。」
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克里歐的一生。他的參戰讓他得以利用《軍人權利法案》學習,並且成為藝術家:如今他的畫作得到全美國的博物館和大學永久珍藏。他在戰時受的傷讓他養成了走路的習慣─起先是為了復健,後來則成了運動。如今他是冠軍競走選手,在老兵競走比賽中創下了所屬年齡群體的世界紀錄。二戰也讓他第一次出國:如今他會說三種語言,走遍了全世界,在墨西哥、義大利、西班牙、法國都長住過,如今則在英國長住。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話,以上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我採訪他的時候,他對這一點十分堅決。「它差不多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改變了我的人生。」他說,「發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全都來自那場戰爭。」他只對另外一點同樣強調。「我不是英雄。“我”這麼說的話,你一定要相信我。」
李歐納.克里歐的故事,反映出全世界(尤其戰勝國)紀念二戰的方式有著根深柢固的問題。
克里歐不是自己選擇當英雄的,這是強加在他身上的稱號,而這個稱號許多年來似乎獨立於克里歐本人之外,自行成長和發展。正如他比多數人更加理解的,戰爭的真實事件和我們「紀念」這些事件的方式是大不相同的兩回事,其間不斷擴大的出入令他非常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