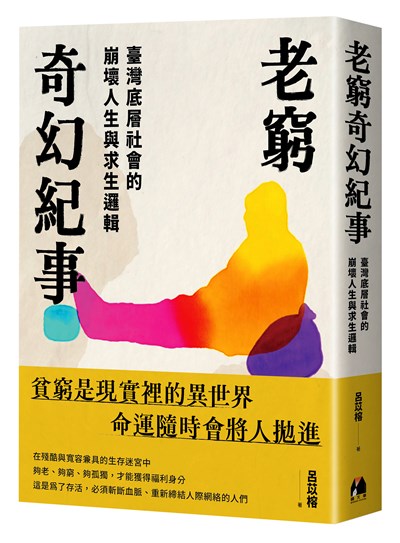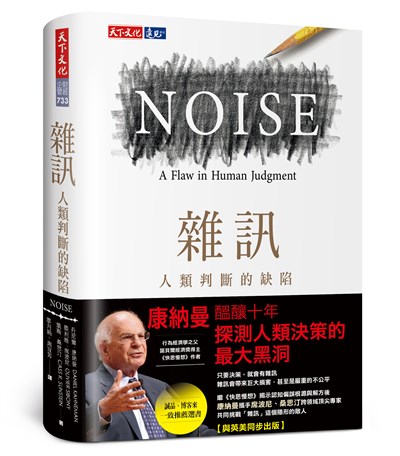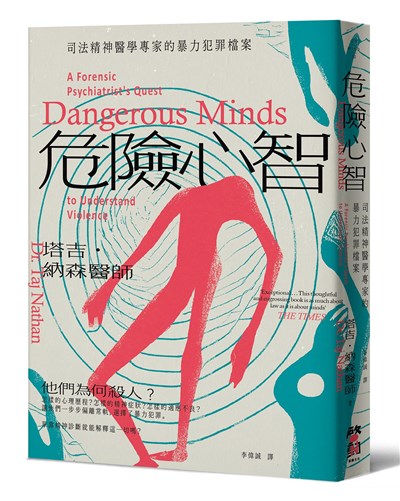前職業網壇天王阿格西從十六歲進入職業網球界,持續稱霸球場二十餘年,是許多年輕人景仰的偶像,但當記者問他「如果人生可以重來的話,你會怎麼過?」他說他不知道,因為他從來沒有選擇人生的自由,他也在《公開:阿格西自傳》中坦誠對網球懷著深沉神秘的恨意,並詳述自己人生的掙扎與成功的動力。
讀者可感受到阿格西這些話的無奈與深沉悲哀,也就了解他剛出道時穿耳洞、戴耳環、留長髮、穿牛仔褲上場打球,是表達他的叛逆。他所有的時間都被練球占滿,七歲開始一天要打2500顆球,一年要打100萬顆球。苦練得出的佳績,令他不知該感謝他鋼鐵意志的爸爸,還是恨父親奪走本來屬於他的一生。
阿格西是男子網壇最先贏得四大滿貫賽冠軍與奧運金牌的金滿貫得主,但職業生涯也有大起落,曾經從巔峰掉落到世界排名141名。中輟失學的他意識到必須為家鄉失學的孩子贏得勝利,才能累積幫助那些孩子受教育的基金,這使他的奮戰有了更高的意義,從離經叛道到謙沖回饋,讀來令人感動且勵志。
阿格西球技精湛,文筆也佳,把傳奇人生坦白誠實地公開,沒有一點做作,好像他本人在跟你說話,非常好看,翻開閱讀就不想停下來,由於他剛訪問過台灣,讀者讀起來會更有親切感。他受訪時表示,兒女有選擇自己生活的權利,對照他的人生沒有選擇權,卻應證了才能可被逼迫培養出來,將提供讀者、為人父母者許多思考的空間。
文章節錄
完結篇
我睜開眼睛,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也不知道自己是誰。其實早就習慣了——大半輩子我都不知道。不過,今天早上還是有點不同:這次的混亂感更可怕,更徹底。
抬頭看,發現我躺在床邊的地板上。我現在想起來了:本來我是睡在床上,半夜才跑到地上睡。我幾乎每晚都會這麼做,因為這樣對我的背比較好。如果躺在軟床墊上太久,我的背會很痛。數到三……我展開緩慢而艱難的起床過程:咳嗽、呻吟、轉身側臥、蜷曲成胎兒姿勢,然後翻過去整個人趴著。好,接下來先等一下,等身體裡的血液開始流動。
說來我還年輕,才三十六歲。但是我每天醒來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像九十六歲似的。過去二十多年來我不斷衝刺、急停、高高跳起、重重落地,我的身體早已不像是自己的了,在早上尤其明顯。我的腦袋也沒好到哪裡去。每天睜開眼睛的時候,我連自己都快不認識了,而且這種情況在早上特別明顯。我快速複習一下自己的基本資料:我叫安卓‧阿格西;我老婆是史蒂芬妮‧葛拉芙;我們生了兩個小孩,一男一女,五歲和三歲。我們家在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但此刻我們住在紐約四季飯店的套房,原因是我正在打二零零六年的美國網球公開賽。這是我最後一次的美網公開賽,也是我網球生涯最後一場賽事。我是職業網球選手,不過我恨網球,我對網球懷藏著一股深沈、神秘的恨意。
最後這組基本資料進入腦海之後,我從趴著的地上起來,改成跪坐的姿勢,用細微的低聲說:拜託,讓這一切結束吧。
然後又說:不,我還沒準備好讓這一切結束呢。
隔壁房間傳出史蒂芬妮跟孩子們的聲音。他們聊著、笑著,一邊吃早餐。我強烈渴望能夠看見他們、觸摸他們(同時也強烈渴望吸收一些咖啡因)。這個念頭給了我脫離地板的力量,我想把自己拉起來,讓自己站直。「憎恨」這東西老是害我屈膝跪地,但是「愛」則讓我雙腳挺立站直。
我瞄了一下床頭的鬧鐘,七點半。史蒂芬妮讓我睡晚一點。最近這幾天的疲憊實在難以招架。除了體能上的壓力,我到底要不要退休這件事,也帶來如狂潮般的情緒波動,讓我倍感疲倦。現在,今天第一波的疼痛開始從倦怠感當中竄出。我用手扶著我的背,但我的背彷彿控制了我的全身,感覺就好像晚上睡到一半有人溜進來,在你的脊椎上加了一道防盜的方向盤鎖。既然我的脊椎被防盜大鎖鎖著,那要怎麼打美網公開賽?難道我生涯最後一場比賽就這麼完蛋了嗎?
我天生就有脊椎滑脫症。也就是說,我最後一節椎骨脫離了其它椎骨,叛逆地自行突出來,造成我走路內八。也因為最後這節椎骨沒對齊,所以我脊椎骨柱裡面可以容納神經的空間變得很小。一般人的脊柱裡面本來就沒多少空間,而我的又更少,只要一點小動作便會壓迫到神經。再加上有兩片脫出的椎間盤和一根不斷成長的骨頭(因為想要保護那塊受損區域,但卻沒有效果),結果只會造成脊柱裡的神經徹底像是幽閉恐懼症發作一樣。每當神經向我抗議那個擁擠的空間環境,每當神經發出求救信號的時候,就會產生一陣足以令我倒抽一口氣、遍及我整隻腿的劇痛。唯一的解藥其實是躺下來等待痛苦過去。然而,這種劇痛有時會在比賽中途來襲,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改變我的打法:用不同的方式揮拍、用不同的方式跑動、用不同的方式做所有動作。每當我改變打法,我的肌肉就開始抽搐。人都不喜歡改變,人的肌肉也一樣。我的肌肉一旦被逼著改變習慣的運動方式,它們便加入了脊椎的叛亂,而此時我在球場上最大的對手也就成了我自己的身體。
吉爾,我的體能教練兼好友、我的救主、我的代理老爸,他是這樣解釋的:你的身體說它不想再打球了。
我告訴吉爾,我的身體已經這麼說很久了,我本人也已經這麼說很久了。
但是,從一月份開始,我的身體決定要用吼的了。我的身體不想要退休——因為它早就退休了,它早就已經在佛羅里達買了棟公寓跟白色休閒褲,準備要養老了。其實我一直在跟我的身體討價還價,懇求它暫時重出江湖,到這裡打幾個小時網球,再到那裡打幾個小時網球。我和身體之間的協議重點,就是一劑可以暫時舒緩疼痛的可體松注射。然而,在「那根針」發揮效用前,自有許多折磨要受。
幾天前我剛挨了一針,好讓我今晚可以出賽。那是我今年的第三針,我生涯的第十三針,也絕對是最令我害怕的一針。首先,醫生粗魯地叫我擺好姿勢(這位醫生不是我平常看的那一位),身體拉直,臉朝下趴在他的診療檯上。護士拽下我的短褲。醫生說他要把那根長達十八公分的針盡量貼近我發炎的神經,不過由於突出的椎間盤骨擋在半路上,針頭沒法直接進入,所以醫生想繞過骨頭,以便解開我脊椎上的防盜大鎖,這樣我才能功力大增。他先把針刺進去,再將一台巨大的X光機拉到我背部上方,檢視針頭與神經的距離。針頭必須盡量接近神經,卻不能真的觸碰到它,如果針頭碰到神經,縱使只是刮到一點點,將造成無法想像的痛楚,不但會毀了我的賽事,還可能永久改變我的人生。醫生移動著那根針,插進去、拔出來、轉幾圈。我的眼睛早已痛到滿是淚水了。
他終於找到正確的那一點。正中紅心,他說。
然後他把可體松注入我體內,那股燒灼的感覺差點沒讓我咬破嘴唇。隨之而來的是一股壓力,我感覺好像被醃起來防腐了,體內被灌滿了。脊椎裡安放著神經的小地方,也似乎被抽成真空了,壓力不斷增強,直到我的背部快要爆裂開來。
醫生說:有壓力,才能確定一切都在正常運作。
好一句人生箴言啊,醫生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