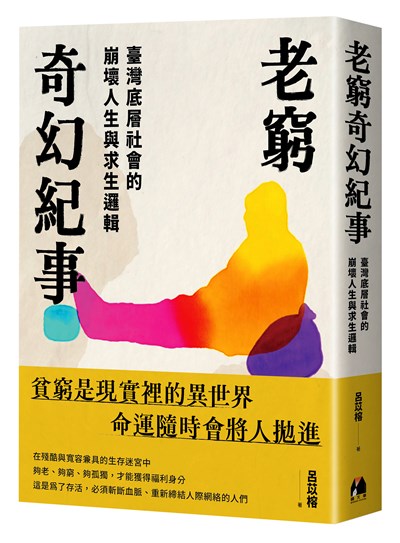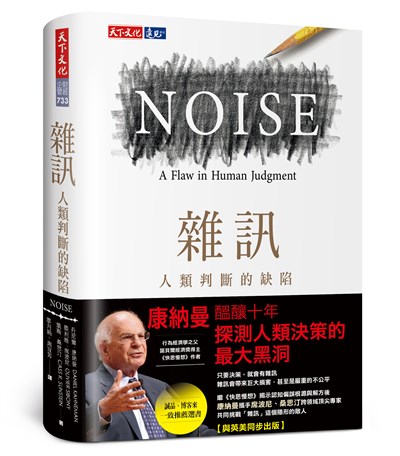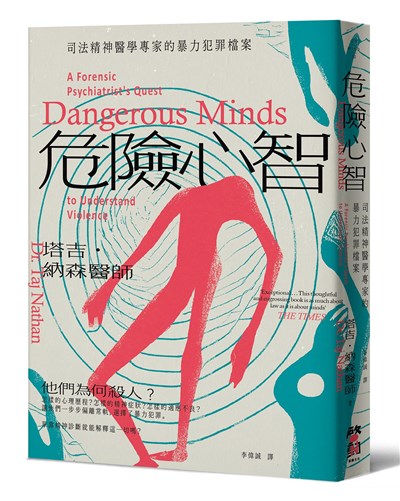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凱斯‧詹京斯不論教學與著作,都從後現代主義論點分析與批判歷史學,他於1991年完成《歷史的再思考》一書,刻意以精簡篇幅讓讀者快速掌握史學方法論的精神,不僅奠定他在史學方法論的重要地位,如今也成為他的經典代表作。中文版最早於1996年推出,台灣如今再版,讓更多華語讀者分享。
書中先引介歷史的定義,作者主張歷史主要由歷史學家創造論述,是一種隨時代調整的移動性本質,卻往往招來連串誤解與濫用;其次,歷史學家傾向以科學看待自己的專業,但史學研究過程充斥難以分辨真偽的資料,必須靠推論拼湊出歷史輪廓,所以也有人傾向把史學視為有很大創造性的一門藝術;最後,作者認為今天理解的歷史未必真實,因此試圖重新建構全新的史學方法,以批判、放棄傳統知識。
作者反覆提醒讀者,面對歷史,我們必須維持某種程度的懷疑主義,而且,在後現代主義的世界中,歷史學也已演繹出各種不同的樣貌,各種新的歷史類型大量湧現,包括以兒童、黑人、反動、下層階級為主軸的歷史論述。不過,新出現的這些歷史類型,其實仍然受到地方性、國家民族性與國際性的影響。
這本書的書寫固然對專業的史學工作者更有用,但對於一般讀者來說,仍有提醒的價值,就是大家必須以更開闊的心胸接受關於歷史的不同詮釋,並如作者所言,宜維持某種程度的懷疑主義,去接納隨時可能出現的、意料之外的史學新觀點,並能在自覺中走出傳統史學的迷思,去理解與發現歷史最接近事實的真相。
文章節錄
讓我由「歷史乃論述過去,但絕不等於過去」的這個想法談起。這個想法可能會令讀者感到非常奇特,因為從前你可能不曾注意這種區別,即或曾注意到,可能還為此感到困惑。一般人之所以不在這個區別上做研究,原因之一,是我們這些使用英語的人,往往忽視了「歷史」——對於「過去」的書寫╱記錄——和「過去」本身,事實上是不同的,因為「歷史」這個字涵蓋了兩者。因而,我們最好記住這個差異——用「過去」一辭表示各處從前發生過的事,而用「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一辭代表「歷史」。此處的「歷史編纂」係指歷史學家的著作。這個辦法不錯:以「過去」為歷史學家處理的目標,而以「歷史編纂」為歷史學家照料它的方法,並且用「歷史」(此處指H 大寫的歷史)一辭,去指關係的總體。然而,習慣不容易破除,我自己也可能用「歷史」一辭去指過去,指歷史編纂和指關係的全體。但是請記住,每當我在這樣做時,我心中還是牢記著上述的區別—你也該這樣。
然而,這個對「過去」和「歷史」之間的區別的說明,也很可能看起來是不怎麼重要的。我們會想:分不清楚兩者間的差別又怎麼樣?又有什麼關係?讓我舉三個實例,說明為什麼辨明「過去」和「歷史」之間的區別是重要的。
1.過去已經發生。它已逝去,只能由歷史學家藉非常不一樣的媒體(如書籍、論文、紀錄影片等)喚回,而非藉由實際的事件。過去已逝,歷史是歷史學家在工作中對它的解釋。歷史是歷史學家(或其他像歷史學家的人)的工作。當他們會面時,彼此互相詢問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你在做什麼題目?當你在「做」歷史時(「我正要去大學讀歷史」),你所讀的是收入在書籍、期刊等之內的這份工作。這表示歷史簡直就是存在於圖書館和書架上的。因此,如果你開始上一門關於十七世紀西班牙的課程,你不是真正到十七世紀或西班牙,而是拿著書單去圖書館。那裡才是十七世紀西班牙的所在——在杜威(Dewey)的圖書分類法號碼之間——因為,教師還曾叫你到別的地方去「讀它嗎」?當然,你可以去其他能夠找到遺跡的地方,比方說西班牙的檔案保存處。
但是不論你去哪裡,當你到達以後,你還是得「閱讀」。這種閱讀不是自然的而是學得的(例如由各種功課上),和由其他文本賦予充分意義的。歷史(歷史編纂)是一種存在於文字間的、語言學上的構造。
2.假設你是在高等中學研究英國的過去—十六世紀的過去。讓我們想像你用的主要教科書是艾爾頓所著的:《都鐸王朝治下的英國》(England under the Tudors)。在課堂上,你對十六世紀英國的各層面進行了討論,也記了筆記,但是你在寫論文和做大半的校訂工作時,習慣用的是艾爾頓的這本書。考試的時候,你是在艾爾頓的「護駕」之下作答。當你通過考試以後,你對於英國歷史的知識有了高等程度*的資格——對思考「過去」的一項資格。但事實上,更正確的說法是你對艾爾頓有了高等程度的知識。因為在這一階段上,你對於英國過去的「解讀」,如果基本上不是艾爾頓的解讀,還能是什麼?
3.這兩個「過去」和「歷史」區別的例子看上去似乎是良性的,但是實際上卻可以造成巨大的影響。例如說,雖然曾有千百萬的婦女生活在過去(在希臘、羅馬、中世紀、非洲、美洲……),但其中卻只有極少數出現在歷史上,也就是歷史文本上。套句俗話便是,婦女「給藏起來不讓進歷史」,也就是有系統的被排除於大多數歷史學家的記述之外。因此,女權主義者現在從事「將婦女寫回歷史」的工作,而男性和女性雙方現在也都正注視著關聯緊密的對於「男子氣概」的建構* 2。在此,你或可停下來想想:有多少其他群體和階級,過去曾經、現在仍是被歷史書所省略,其原因何在。而如果這些被省略的「群體」對於歷史記述非常重要,卻受到如此的忽略,其後果又將如何?
接下去我們還會再談到研究「過去」與「歷史」區別的重要性和各種可能性。但是,現在我想引申前面一段文字中的另一議論。在前文中,我說我們必須了解「過去」和「歷史」並非彼此緊密縫合在一起,以致只需要對於任何現象做一種且唯一的解讀。同一研究的對象可以因不同論述的方式而有不同的解讀,而每一種對象,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也有不同的解讀。
為了開始舉例說明這個論點,讓我們試著想像透過一扇窗戶我們所能看到的景致(雖然無法看到全景,因為窗框幾乎真的將它框住了)。我們可以在最近的前方看到好幾條道路;再遠一點有另外幾條道路,路旁有房子;我們可以看見起伏的農田,農舍點綴其間;幾哩以外,我們可以看到天際邊的山脊。在中距離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市集城鎮,碧空如洗。在這個景致中,沒有什麼可說是「地理」。可是一位地理學家顯然可以從地理學的觀點說明它。因此,他(她)可以解讀這片大地是在展示特殊的農田模式和農作方法。
這些道路可以解讀為地方性和區域性交通網絡的一部分;可以用特殊人口分布解讀農場和市鎮;可根據等高線地圖製成地形圖;氣候地理學家可以解釋天氣和氣候,以及比如說其所造成的灌溉類型。就這樣,這個景致可以變成別的東西——地理學。類似的,社會學家也可以給這同樣的景致賦予社會學上的解釋。市鎮中的居民可以成為研究職業結構和家庭單位大小的資料;可以由階級、收入、年齡和性別的觀點研究人口的分布;氣候可以視做影響休閒設施的因素,種種等等。
歷史學家也可以論述同樣的景致。今日的農田模式可以拿來和圈地以前的模式相比;現在的人口可以拿來和1831年及1871 年的人口相比;可以分析一段長時間中的土地所有權和政治力量。我們可以檢討這個景致中的某一點如何逐漸變成一座國家公園;某些鐵路和運河又在何時及何種情況下停止作用,種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