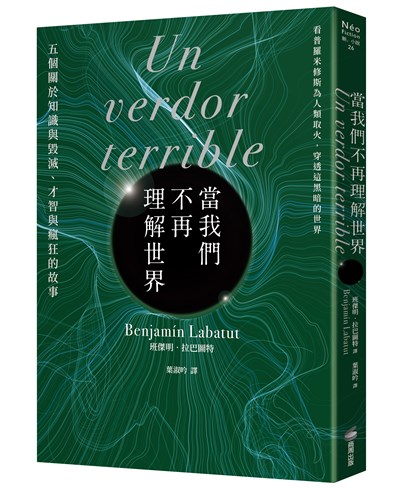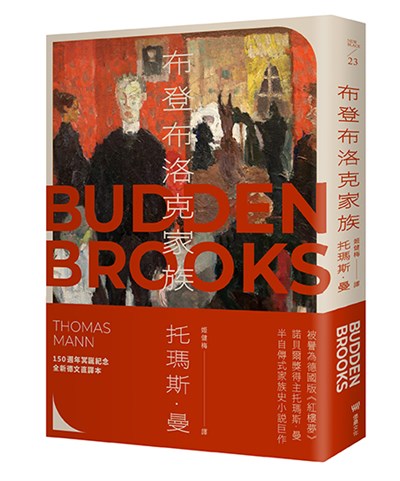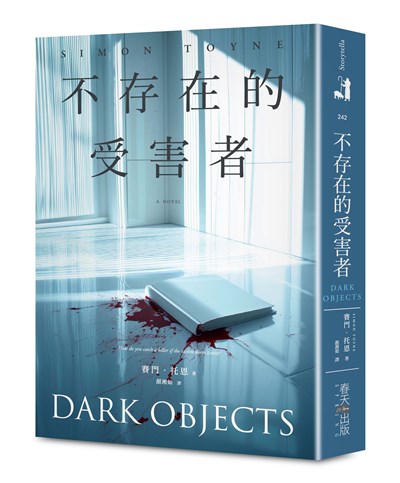胭脂,是一個女子的名字、是畫上的一抹紅、是一個錦盒…是狠毒、是恥辱、是刀劍、是欺騙;踏過千瘡百孔的時代,在歷經萬人踩踏如爛泥的肉身上,胭脂仍紅如火,是女子綿延不絕的愛。作者張翎用三篇故事,寫出三代女子在上海、杭州、溫州和巴黎,富家千金愛上窮畫家,一連串因牽掛而背叛家庭,因命運而分離,因文革而隱匿,因生存與奪寶而說謊,再一次交織出女子在殘酷厄運下的堅強生命力。
文章節錄
《胭脂》
這時臺上押上來一個精瘦精瘦的小夥子,押他的是兩個比他年長些的人,也是精瘦精瘦的,卻比他站得直。那個被人押著的人佝僂著身子,因為脖子上墜著一塊大牌子。牌子上寫著兩行字,一行大,一行小,大的那行在下,扣扣全認得,是「武建國」。小的那行在上,扣扣只認得兩個字,一個是「流」,一個是「偷」。被押的那個人一上臺就噗通一聲跪倒在了地上——是讓人照著腰眼踹了一腳。那一腳踹得狠,他嗷地叫了一聲,身子蜷成一個球,頭抽了一抽,縮進了頸脖裡頭。
踹他的那個人一把揪住他的頭髮,把他的臉從脖子裡揪扯出來,正正地對著臺下,扣扣就看見了他左邊臉上一塊紅色斑記。頭皮扯得很緊,那塊紅斑被扯得吊了上去,像一隻被撕成了一半的蝴蝶。扣扣的眼皮跳了一下,她認出了那半隻蝴蝶。那半隻蝴蝶比她上次見到的時候,長大了很多。
臉上長著蝴蝶的人咧開嘴嘶嘶地哼著,露出兩排黃褐色的牙齒,兩道眉毛蹙成一團磨得起了毛的舊麻繩,頭扭來扭去,想從揪他的人手裡扯出一絲寬鬆。
敲鑼的老太太聽不得那嘶聲,揚起鑼錘,朝著那人的額頭敲過去。鑼錘落下去的聲響很古怪,像菜刀柄砸在沒熟透的西瓜上,有些脆脆的,又有些沉悶。
「裝什麼可憐?偷人東西的時候怎麼不知道怕?」老太太厲聲呵斥道。
那人沒防備老太太會出手,怔了一下,才伸出雙手捂住了額頭。扣扣發現他的指縫裡有些東西流了出來,膩紅膩紅的。
那人咿嗚一聲哭了起來。那哭聲一點兒也不像是男人的,倒像是被人踩到了爪子的老鼠,或是被刀剁去了一截尾巴的貓狗。
「皇天,這是東門老武家的小兒子。」
站在外婆身邊的一個女人對另一個女人說。
「這小子從小就渾,他爸管不了他。去了黑龍江兵團,受不得那裡的苦,逃回來了。沒戶口,天天偷雞摸狗混世。」
另一個女人嘆了一口氣,說:「腰眼和腦門,都是要命的地兒。要是殘了傻了,年輕輕的,將來還怎麼活?」
兩個女人誰也捨不下那份熱鬧,嘴裡嘆息著,腳卻不肯走。
這時臺底下衝上來一個男人,手裡捏著一根粗木棍。男人比臺上那幾個男人都年長,也比他們粗壯,身上穿的那件汗衫,已經洗得掛絲,早已看不出顏色,露在外邊的胳膊和頸脖,被太陽晒得黝黑,上面有一層豬油似的亮光,是汗水。
男人推開臺上那幾個人:「省省你們的力氣,看我怎麼教訓這個猢猻。」
男人朝那個臉上有斑的人一腳踢了過去。這一腳踢在屁股上,勁很足。那人似乎被剛才那一鑼槌打掉了魂,木木的,不再做任何掙扎,像只裝滿了米的麻袋一樣倒了下去,軟軟的,沉沉的,臺上只剩下一團凸凸凹凹的灰布——那是他的衣服。
穿汗衫的男人掄起手裡的木棍,照著那團灰布砸了下去。灰布彈跳起來,卻又落了下去。扣扣又聽見了哭聲。這一次,是放開了嗓門的哭,或者說,是嚎。
男人這一下太凶猛了,棍子啪的一聲斷成了兩截。男人閃了胳膊。男人扔下那半截剩在他手裡的木棍,用一隻手捂住另一邊的肩膀,嘴唇突突地抖。
「我老武一家,一家三代,碼頭工人。我爺爺是搬運工,我爹是,我也是。我們,我們無產階級,就不信,管不好,一個混蛋。」
男人用一條腿勾起地上的那團灰布:「你給我起來,別裝死,在我這兒不管用。你要死,去,去黑龍江死,別在這兒,禍害鄉親。」
男人用那隻沒閃著的胳膊,揪起那團灰布,往臺下走去。
「老姐姐你給我,讓讓路。這幾位兄弟,別費心神了,回去歇著,把這個混球,交,交給我管教。要是他敢,再禍害人一次,你們直,直接抓我。誰不知道,我,東門老武。」
敲鑼的老太太舉起鑼錘,像是要敲鑼的樣子,不知怎的,卻沒敲成,手僵在半空,嘴巴張成一個黑黢黢的小洞。
一行人眼睜睜地看著男人把人帶下臺去。
「這個老武,苦肉計呢。沒看見那一腳那一棍子,落的都是不緊要的地方。那麼粗的棍子,哪能一下就斷了?裡頭有戲呢。」外婆旁邊的那個女人悄聲對另外那個女人說。
眾人終於不情不願地散了。臺上的人開始卸下那條紅布橫幅,用指甲挑開黏在上面的字。那條紅布還會貼上別的字眼,派上別的用場,興許在這個街口,興許在下一個。
外婆終於可以把扣扣放下了。外婆累了,顧不上髒,一屁股坐到了馬路砑子(注)上,呼哧呼哧地喘著氣。
扣扣的腿麻了,腳踮在地上像扎著一萬根針。扣扣靠在一棵樹身上,想等著腳上的針落地,可是針還沒落地,她就彎下腰來哇地一聲吐了。
外婆看見她吐出來的都是些還沒來得及消化的餅乾末子,那些雄雞、羊羔、兔子(或是貓)的渣末,可扣扣卻知道不是。
至少不全是。
扣扣是把堵在喉嚨口的心吐出來了。
外婆從兜裡掏出那塊剛才包過餅乾的手絹,來擦扣扣的嘴。
「沒事,沒事,肚子空了,好吃晚飯。」外婆輕輕拍著扣扣的背。外婆發現扣扣的襯衫黏黏糊糊的,全是汗。
「認出來了吧,那個人?」外婆問。
扣扣沒說話。半晌,才點了點頭。
還要過很久扣扣才會知道,這幾個月裡,扣扣上學的時候,外婆幾乎天天在外邊走。外婆在執拗地尋找著那個人的蹤跡|那個用一記耳光在外婆的耳膜上留下了永不癒合的小孔的人。
那天的相遇,並非偶然。
「你現在,再也不用怕他了。」外婆說。
那天回家,外婆去了灶披間,捅開爐子,用慢火燉了一鍋綠豆粥,又炒了一盤雞蛋蝦皮,就去招呼扣扣出來吃飯。
扣扣沒回聲。外婆進屋一看,發覺扣扣已經躺在床上睡著了,身邊放著那個裝過豆腐乳的敞口瓶。瓶蓋是擰開的,裡邊空無一物。
扣扣吃完了她的餅乾存貨。她的動物部隊全軍覆沒,片甲不留。
夜裡,扣扣被一陣奇怪的格格聲驚醒。她以為是老鼠。她豎起耳朵仔細聽了許久,才恍然大悟:那聲音來自她的身體,是她的骨頭在爆裂,像拔節長高的竹子。
第二天早上起床,扣扣發現穿了兩年的鞋子小了,她怎麼也套不進去。
注:馬路砑子:中國北方方言,指馬路與人行道相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