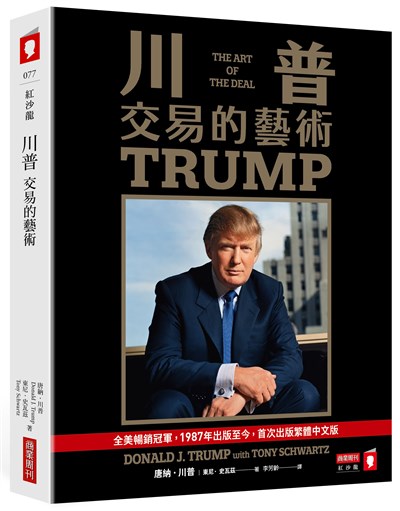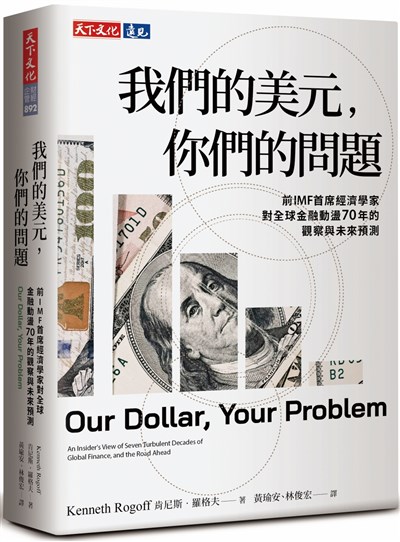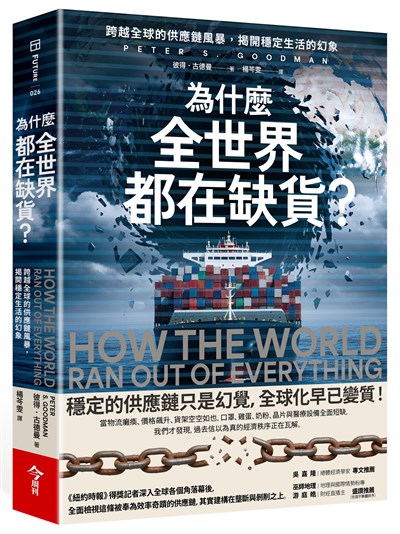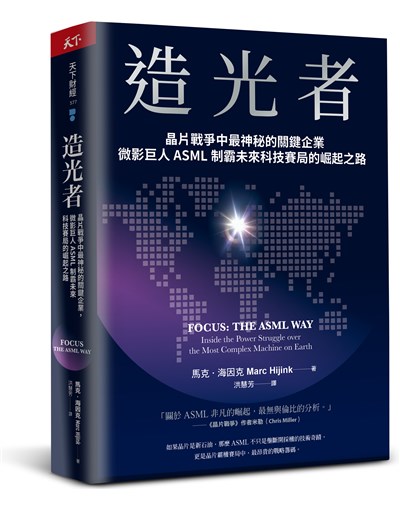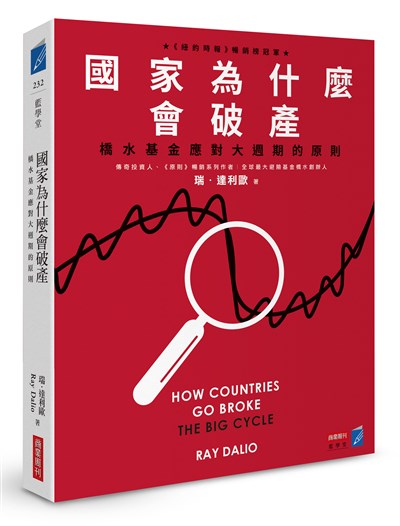
達利歐最新力作,揭開國家大債週期與破產風險的秘密,出版前即受萬眾矚目,白宮政策圈與華爾街投資界預購期間搶讀,甫出版即空降《紐約時報》暢銷冠軍。
2025全球最矚目政經議題:為何再掀全球關稅戰、美國國債會帶來什麼後果?政府舉債、全民發現金,背後潛藏哪些危機?從2018年至今,美中對抗的核心糾結是什麼?美股、日債、黃金,該怎麼配置?背後的運行邏輯就是「大債週期」!當你看懂局勢,才能守護資本、抓住危機中的機會。
內容節錄
《國家為什麼會破產:橋水基金應對大週期的原則》
第19 章 我展望的未來
⊙基於我的範本與指標展望未來
我運用我的大週期範本及一系列指標來判斷我們目前所處的週期階段,並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情況。為了進行投資,我將這個概念性範本轉化成一個更具體的分析決策系統。我將用這些概念來說明我認為當前的情勢如何,以及我所預期的未來走向。
我會從我在2025 年3 月撰寫時對整體情勢的看法開始說起:
根據我的評估,當前的局勢與1905 至1914 年、1933 至1938 年以及歷史上許多國家的關鍵時刻最為相似,正如前文所述,我將其定義為大週期的第五階段。在此階段,各國普遍呈現以下特徵:國家債務累累、管理效能低下、社會嚴重分裂,並且面臨其他國家的威脅。這種環境會強烈催生具有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軍國主義及威權主義傾向的領導人。
藉由歷史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危機的時刻總會導致專制統治,因為民主制度變得嚴重分裂而癱瘓,其領導人也無法妥協。在這些時期,只有權力才是最重要的,因此那些獲得權力並更為專制的當權者,往往更傾向於與國內和國外對手進行對抗,而非合作。新領導人總是誓言要為增強國家實力而戰,並且更願意發動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衝突,最終將貨幣秩序、國內政治秩序與國際地緣政治秩序推向重大衝突與秩序重構的臨界點。
根據我的評估,所有主要大國目前都處於這種狀態(即負債過高、治理低效且社會分裂),而正是這種局勢日益升溫催生出更多具民族主義、保護主義、軍國主義和專制主義傾向的領導人及政策。這些領導人,尤其是美國的川普總統,渴望為增強國家實力而戰,並且更願意參與經濟、地緣政治和軍事衝突來獲得勝利。近期事態發展基本遵循我所闡述的典型大週期範本,這種範本正將世界推向重大衝突與巨大變革的臨界點。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變革並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因為它們最終會變成什麼樣子,仍然掌握在那些控制權力的人手中。
現在,讓我們參考前述的一些原則,更深入地探討一下這五大力量及當前發展態勢。我主要關注美國,因為無論從哪個衡量標準來看,美國都是最重要的國家,其變化對全世界的影響將最為深遠。儘管如此,其他七大工業國和中國也都處於類似的位置,並且在這個大週期中相互作用,世界各國都會受到它們的影響,同時也會影響所發生的事情。順帶一提,在我們討論的所有變數之外,人口結構變遷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力量,未來會有大量老年人不再工作,並且使醫療保健成本上漲而變得難以支持,與此同時勞動力人口又在減少,因此只有極小部分人真正具有生產力。
關於我們所處的大債務週期階段,正如本書前文所述,根據我的評估,美國及大多數主要國家(七大工業國家及中國)目前負債過高,正處於大債務週期的後期階段,不得不頻繁依賴「貨幣政策3」(即央行藉由購買債務來資助巨額財政赤字)。因此,如果這些國家的長期大債週期問題得不到某種方式的控制,未來五年內,主要儲備貨幣計價的債務資產與債務負債被迫進行大規模重組/貨幣化的概率極高,約為65%;而未來十年內,機率可能升至80% 左右。這是因為當前的債務資產與債務負債規模已十分龐大,且預計將進一步攀升至更高水準,這將導致政策陷入兩難:若利率過高、貨幣過緊,雖能滿足放款人(債權人)的要求,卻會嚴重損害貸款人(債務人);若利率不夠高、貨幣不夠緊,則無法滿足放款人(債權人)的需求。
正如前面所述,債務危機即將爆發的重大警訊是現有政府債務資產(如公債)持有者的大規模拋售。這將與政府新債的發行和銷售同時發生,導致債務供給遠超過需求,迫使央行面臨兩難選擇:要麼選擇讓名目利率和實質利率大幅上升,要麼選擇大量印鈔並購買長期政府債務以壓低利率,從而導致債務和貨幣貶值。在我看來,現在似乎是一個很好的時機來記住以下原則:
顯然,減輕如此沉重的債務負擔符合這些國家的根本利益。根據我對歷史的研究,當國家陷入類似處境時,它們往往會採取各種在當時(以及現今)看來難以想像的極端手段來刪減債務負擔,包括:凍結債務償付、沒收敵對國家資產、實施掠奪性稅收及資本/外匯管制、債務違約或延長償還期限,以及改變流通貨幣的類型(例如,取消與黃金等硬資產掛鉤或發行新貨幣)。
我不是說這些事情一定會發生,但我想指出的是,在川普這樣具爭議性的領導人之前,像羅斯福和尼克森這般的傳統領導人也曾採取過這類激進的改革措施。儘管目前我認為大多數方案仍不太可能發生,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就是各國領導人必須妥善解決債務供需失衡問題。重要的是要警惕這些極端措施可能引發的風險,也要動態跟蹤事況演變。在我看來,最理想的方案是實施我提出的3% 三重解決方案(指縮減支出、增加稅收及降低利率的組合),配合協調有序的「美好的去槓桿化」進程,即透過財政緊縮和債務重組等通縮性去槓桿手段,與貨幣寬鬆和債務貨幣化等通膨性去槓桿手段達成平衡。無論如何,那種透過超額舉債來維持非生產性人口過度消費的時代即將終結。未來的主要目標就是在提升生產力的同時減輕債務負擔(這一過程往往伴隨著債務與貨幣價值的同步縮水)。
如前面提到的,美國及多數主要經濟體目前可能已走完短期債務週期的三分之二進程。從實值與名目經濟成長率、利率及通膨水準綜合判斷,這些國家正接近均衡水準。2022 年3 月啟動的貨幣緊縮,終結了聯準會等七大工業國央行長期奉行的免費提供大量貨幣和信貸的模式。從那時候開始,聯準會與各國央行政策基調從以下特徵發生根本轉變:a)對貸款人(債務人)有利但對放款人(債權人)不利且具有通膨性的貨幣政策;轉向 b)略顯緊縮的貨幣政策(按我的評估標準)。伴隨貨幣緊縮與供應鏈壓力緩解,通膨率已回落至略高於央行目標區間的水準,促使各國央行逐步放鬆政策。現在大多數國家正處在一個新的典範中,就是央行實施相對溫和的貨幣政策(具體鬆緊程度因各國而異,例如美國經濟成長強勁,尤其是科技業,而其他七大工業國家則表現疲軟)。但英國、法國及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正面臨本書前文所提及的政府債務供需失衡問題。單就通膨與成長率而言,當前名目與實質利率水準看似處於合理區間,即能滿足債權人的基本收益要求,又不至於對債務人造成過度壓力。但根據本書分析的財政供需動態,現行利率水準(按我的評估標準)仍顯不足。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當前這場顛覆性變革正以截然不同方式衝擊著各行各業——事實上,影響程度之大,遠超我記憶中的任何時期。過去數十年來,儘管債務規模持續攀升,但償債支出並未同步激增,其主要原因在於,從1980 至1981 年至本次加升息前,利率始終處於向下趨勢。由於實際的債務支付存在滯後效應(即固定利率的債務到期前利率不會調整),償債支出將繼續上升,逐步向現行利率水準靠攏。就2025 年3 月的最新通膨與經濟成長數據而言,聯準會此時啟動寬鬆政策顯然不合適。但這引發出一個根本性難題:做為一個實質上的全球央行,聯準會該如何制定出一項能讓大多數人都滿意的貨幣政策?我認為,這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聯準會將因此面臨更多的批評和干預。從過去經驗來看,每當央行身處在比類困境時,其政策獨立性往往會遭受挑戰,我們絕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聯準會能永遠保持獨立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