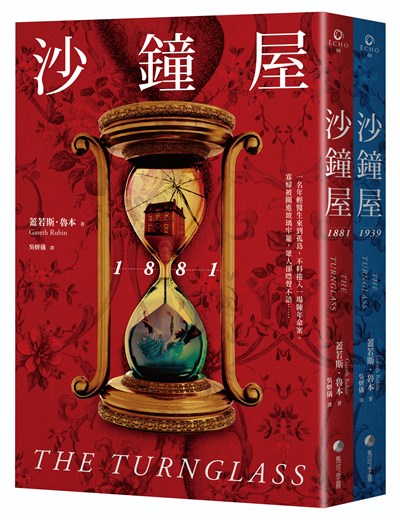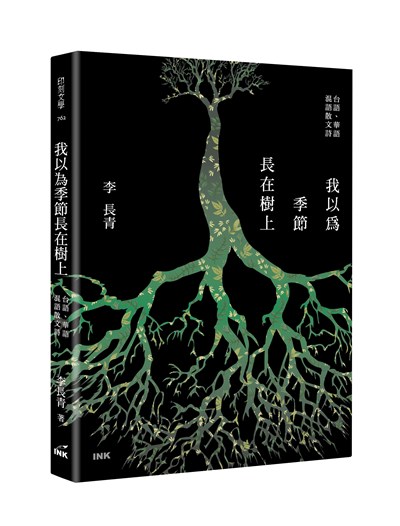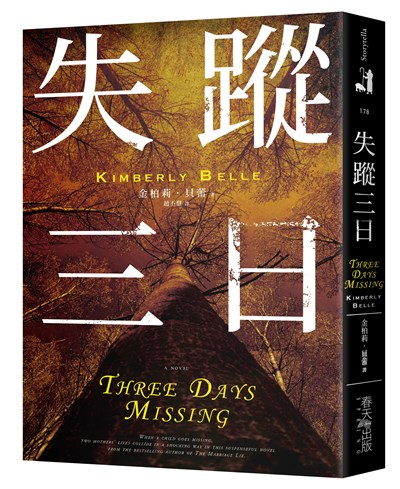
六歲的伊森參加學校過夜戶外教學的時候失蹤了。校方報警,
所以,
內容節錄
《失蹤三日》
凱特
工作上的電郵已經讓我的手機響個不停,而我還在催促著伊森完成早晨的例行公事。起床,著裝,看在上帝的份上刷牙梳頭。在我兒子短短的八年生命裡,他就從來不是一隻早起的鳥兒,而我也不是最有耐心的母親,即使我沒有一個從我踏出電梯的那一秒就計時的老闆。
我並不是說全職媽媽的壓力不大,但是至少那時我跟伊森兩個一條心,都戰戰兢兢繞著安德魯丟在滿屋子的蛋殼走。但是半年來我們養成了這種習慣,打從分居開始。伊森磨蹭,我嘮叨。
「快點,寶貝,我們得走了。」
他睡覺壓住的頭髮仍然根根倒豎,他的T恤上有污漬,皺巴巴的,也就是說他可能是從地板上的髒衣服堆裡隨便抓了一件。我兒子是個邋遢鬼,而且一點也不會覺得不好意思。他也手腳不協調,長相也不僅僅是彆扭而已。他的耳朵太大,鬈髮太不服貼,而他的眼鏡總是佈滿了指紋,好像就是沒辦法乖乖架在鼻梁上。
但是我全心全意愛他—我並不是包容他的古怪,我就是愛他的古怪。如果說安德魯教會了我什麼的話,那就是你不能愛一個人的這一點那一點,要愛就得愛全部,即使是醜陋的那一部分。
我催著伊森下樓,穿過擁擠的門廳,從後門出去。我們小小的牧場風格房屋不值多少錢,但是離婚是很花錢的,每次我的律師覺得勝利在望,安德魯就會又冒出一個荒謬的最後通牒來。我們蜜月時買的那張古董邊桌、他八百輩子前打破的那對水晶燭台、伊森嬰兒時期的照片底片。只要他要的不是伊森,我就會滿足他的每一個需索。
伊森停在汽車前,仍半睡半醒。「你還在等什麼啊?上車啊。」
他沒動。我查看手機上的時間—六點二十七。
「伊森。」沒聽見回應,我就輕輕搖了搖他的肩膀。「快點,甜心,上車。不然你就要錯過遊覽車了。」
也就是說從停車場到小鎮的另一頭只剩下三十三分鐘。今天的目的地:達洛尼加,在亞特蘭大以北一小時的地方,是早年淘金熱興起的城鎮。伊森的班級會在地下兩百呎的礦坑裡跋涉,淘選黃金和不太珍貴的寶石,睡在星空下的木屋裡。上個月他從學校拿回了家長同意書,我還以為是愚人節的玩笑呢。有哪個老師有那個膽量帶著一車的小二生去兩天一夜旅行的?
「這是我們每年都有的活動啊。」愛瑪老師是這麼回答我的。「我們住在YMCA的夏令營營區裡,所以百分之百安全。每五位學生就會有一位老師或是監護人照顧。孩子們一整個學期都在期待。」
她對每一個小二生的直升機父母都是這麼說的,但是拿這一套說辭來對付我,她抓錯了重點。我擔心的不是伊森的人身安全,而是情緒上的安全。伊森的智商高達一五八,是資賦優異的等級,卻也伴隨著特殊挑戰。這是個智力上優異、社交上卻笨拙的孩子;是個愛分析愛思索的孩子,時時刻刻都需要刺激;是個求知若渴的孩子,永遠有問不完的問題。他的說話,興趣,思考模式—他的世界跟同齡的孩子相差太大了,幾乎沒有共通點。他來康橋兩年了,還沒帶過一個朋友回家。沒人約他出去玩,沒人邀他去過夜。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的班級整個春天都在上礦坑的歷史,愛瑪老師往他無底洞似的腦子裡填入了一堆水力沖採和地下坑道網的故事。我兒子跟我說這叫開採礦脈,而在今天早晨之前,他迫不及待想要親眼見識—儘管他除了跟我或安德魯之外從來沒有睡在別人的屋子過。他纏著我哀求,弄得我心軟了,只好吞下我的憂慮,簽了那張可惡的同意書。
他爬上後座,我拋給他一條無花生的早餐棒,他卻不吃。
「怎麼了,寶貝?不舒服嗎?」
「不是。」他看著早餐棒,扮個鬼臉。「只是不餓。」
「還是吃吧。你會需要力氣走階梯,進進出出礦坑。」我是刻意提醒他這一點的,想要激起一些他之前的興奮。
但是我兒子很清楚我的用意,他給我的表情就是標準的伊森臉。下巴往下,挑高眉毛,眼珠子將滾未滾。他重重嘆了口氣,連小小的身軀都抬了起來。
「你早上老是肚子餓,今天為什麼不一樣?」
「不知道。」他的眼鏡往下滑,他動動鼻子把眼鏡推回去。鏡架太鬆了,假玳瑁眼鏡對他的頭來說太重了。伊森八歲,可是身形卻像是六歲的孩子,又一個他得面對的劣勢。「我就是不餓。」
妳不能再這麼嬌生慣養他了。我聽到安德魯的聲音,清晰得有如他就坐在這裡,在我旁邊的乘客座上。不然的話這孩子永遠也學不會自立自強。
妳不能。他永遠不會。這就是安德魯一個讓人刮目相看的本事:他是怪罪別人的專家。而且他只練習了短短幾年就達到了專家的水平。
不過安德魯不在這裡,而我需要去上班。我只能勉強付得起康橋經典學院一半的學費,尤其是離婚手續仍在辦,帳單又像流水一樣來,我的恐懼就跟伊森恐懼床底下的怪物一樣。我的老闆沒有孩子,她不了解伊森的小小愛因斯坦腦袋需要比常人還要多的時間來衡量正反兩面。我需要這份工作,所以我得讓他上那輛遊覽車。我發動汽車,倒出車道。
去學校的路上我一直從後照鏡觀察伊森的表情。我不止一次希望我跟他父親的離異能不要那麼驚天動地,希望我們的交談不必限於紙上,也不必隔著最少兩百呎的肢體距離。限制令讓共同養育孩子變得更棘手,尤其是你這個要去達洛尼加的兒子坐在那兒瞪著窗外,活像是要去做根管治療。
我按了收音機鍵,關掉了晨間節目的閒扯淡。「甜心,拜託跟我說,是怎麼了?哪裡不對勁?」
他的目光閃向我,停駐了一秒就又移開了。他聳了聳肩,即使他明明有答案。伊森一定知道答案。
「你是擔心別的孩子嗎?」
他皺眉,而我知道我說到他的痛處了。
「是不是又有人跟你搗亂?」
我刻意不說欺負,他的老師一直避免用這個字眼,還有那個小混蛋的名字—即使我們兩個都知道她指的是誰。愛瑪老師總是大事化小,當作稚氣的拌嘴,保證都在她的控制之下。但是問題也就出在這兒。她把所有的欺壓都當作幼稚的小吵小鬧,即使都已經見血了。
「要是你告訴我出了什麼事,我可以幫你處理。我會跟愛瑪老師談,確定她知道問題所在。愛瑪老師和我都是跟你同一國的,知道嗎。我們想幫忙。」
「沒什麼,好嗎?沒有人跟我搗亂。」
「那你是擔心離開家嗎?」
伊森對著後照鏡皺眉。
「那你真不用擔心,知道嗎。愛瑪老師會把你照顧得很好。」
沒有回答。他沉坐在椅子裡,兩手包著手肘,指尖在皮膚上緊張地敲打—他只要不想談,就有這個小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