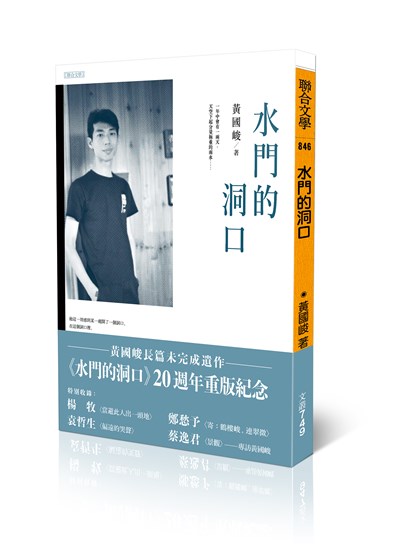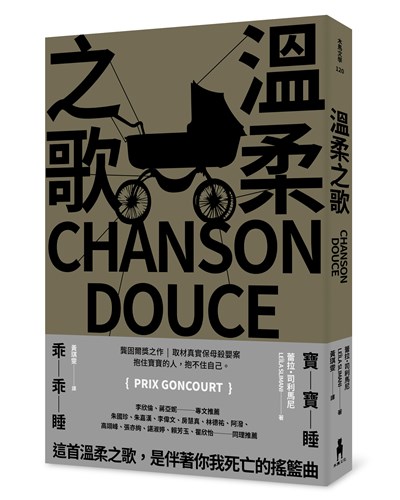2023 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
評審推薦語/黃涵榆(決選評審,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吳明益說故事的方式一直都很吸引人,他總是用一種內斂而帶著憂鬱的情調娓娓道來,以極其自然有機而不做作炫耀的方式,融入他個人豐富的物種、山川、水文與節氣的生態知識與關懷,邀請與陪伴讀者細細地凝視、聆聽與感受。他的作品有種「專注的美學」,那是身處在這個一切都在加速和抖動的碎形化時代的我們所迫切需要的。
在《海風酒店》裡,吳明益像是書中的巨人Dnamay,讓角色穿過孔竅,走進他的身體,來到「巨人之心」。他讓角色們以各自的方式訴說自己的生命歷程和存在情境,讓他們的創傷得到理解或療癒。
《海風酒店》沒有作者中心的敘述霸權,有的是各個海豐村民、巨人甚至食蟹獴的訴說、回憶,以及與夢境交織而成不同時間向度的跨物種視角和敘述網絡。督努、秀子/玉子、歪脖子尤道、娜歐米、小美、阿樂、馬蘭⋯⋯有著各自的慾望、迷惘、執著、創傷和追尋,都匯集在海豐村。
面對水泥廠巨獸的海豐村,不再只是花蓮和平村的投射,而是具有多層次真實的魔幻村落。某種具有神話色彩的生態體系,儼然已在《海風酒店》成形。巨人的血管和山上的水脈與平地的地下水層相連,它透過畫眉鳥、蝙蝠、貓頭鷹、土撥鼠和食蟹獴傳遞的訊息,孤獨而憂鬱地看著大地上物種、物質和生態系數千萬年的質變與滄桑。
相較於殖民擴張和工業開發對山林的「穿孔」,巨人任由人類與動物角色走進體內,象徵著一種好客、安頓與療癒。動物帶著和人類接觸時留下的傷痕與殘肢,在巨人之心度過餘生,但巨人之心也並非全然和平之地,不同物種依照各自的生命規律活著。
「海風酒店」從原本部落的卡拉OK店「升級」為多角化經營的酒店,見證了許許多多的漂泊、失落、鄉愁與挫敗。隨著舊村落被一棟又一棟新蓋的水泥屋取代,背山向海的酒店依舊孤獨地守候,訴說著曾經的滄桑,見證著一些人辛苦地活下來。那將是不會被任何短視、貪婪、野心或冷漠沖刷掉的,記憶與生命的沉積層。
內容節錄
《海風酒店》
從沖積扇到沉積層(節錄)
大約是五、六年前的一個學期期末,我盤算著要找什麼藉口帶學生去一趟旅行,這樣就可以少上一堂課。那年我決定的行程是從花蓮美崙溪的出海口,走到砂婆噹水源地。這趟行程通常是從北濱公園出發,然後經過菁華橋,繞道對岸的將軍府,再過花蓮車流相當頻繁的一條馬路後繼續往上。一路能看見花蓮港區、學校、市區、養殖戶、農地、鐵道,直到部落。
帶著大批同學總是不輕鬆,主要還是照顧每一個人的安全,也很難確保每個人聽見彼此說話。這天從出發時天氣就不好,走了十幾分鐘才過將軍府,雨就大到幾乎不可能繼續下去的程度。
於是我把隊伍拉回將軍府當時暫借出去辦展的最大建築裡,那是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建成的,軍事指揮官中村大佐的官舍。旁邊一處充滿歷史氣息的空間,正展出一位我並不認識的素人畫家的作品。她的作品多半是花蓮的風景,其間微微透露著某種非常個人性的氣息。
畫家知道我在文學系任教後,不斷跟我陳述她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她的人生宛如一部小說。這已經是我生活的常態,間或有人會寫信或在談話中傾訴他們的生命故事。我都盡可能保持感興趣與不感興趣之間的神態,避免讓對方覺得我沒有禮貌,或太過信任我因而談話時太過毫無保留。一個正常人,是沒辦法對每一段人生都真心對待的。我討厭偽裝對任何事都關心的感覺。
一段時間後,雨停了。我得載部分同學回學校,其餘有交通工具的同學就地解散。我們一走展場就剩下創作者本人了,她突然對要離開的我說:「我曾經做過二十幾個工作,當小妹、撿漂流木,還開過酒店。」
我問在花蓮嗎?
她說:「不是,在和平。」
和平是在花蓮以北的一個小地方,是一個大部分臺灣人都感陌生的地方。唯一會被記憶的部分就是它有一個巨大的水泥廠。在水泥廠建廠之初,曾經聚集了各國探勘、採礦,以及建築的工程師,並引入數量龐大的外籍勞工。水泥廠的設廠過程,引發了在地居民和環境團體的抗爭,形成了一場數年的拉鋸。最終就是你看到的景觀——不管你開的是舊蘇花或是蘇花改,都不能繞過巨大的火力發電廠,不能不抬頭看到水泥廠的輸送管道,從溪那端的山綿延而來。去年(二○二二年)臺海緊張時中共軍演,共軍就透過合成圖來表達他們已經可以遙望島嶼的東海岸,而東海岸的視覺座標就是火力發電廠的煙囪。
雖然小說寫的是真正的事件(不是遠歷史也不是近未來),不過不是單用現實材料構築的,當然,它的建材也並非全屬夢境。我刻意讓它和現實保持距離,希望讀者享受到在小說裡的敘事時空;我也試著以身為作家的角度,看待那段猶疑的時光、那些猶疑的生命。如果有讀者問我這是不是一本環境小說?我會說,是一本小說。
寫作的時間與過程非常破碎,因為我已經進入了生命的「責任之年」,不再像年輕的時候,認為遠方比一切都重要。我的創作比不上生活,但我也不捨得放棄,於是只能在生活的責任之外,找出寫作的瑣碎時間。一周我大概有半天的時間可以訪談、蒐集資料、寫作,有些段落甚且是在等候接送家人時,在停靠路邊的車上完成的。這趟寫作常像隻身的旅途被大雨打斷,為了避雨遇到了另一個人,發生了另一件事,雨停後走上了另一條路。旅程很長,但並不是秋天、冬天、春天、夏天這樣形成一個圈圈,而是碰上B,於是走向C,但並不是毫無理由的,很有可能是因為X的緣故。每一個我訪談、接觸過的人,都成了一個節點,一個可以摺疊的箭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