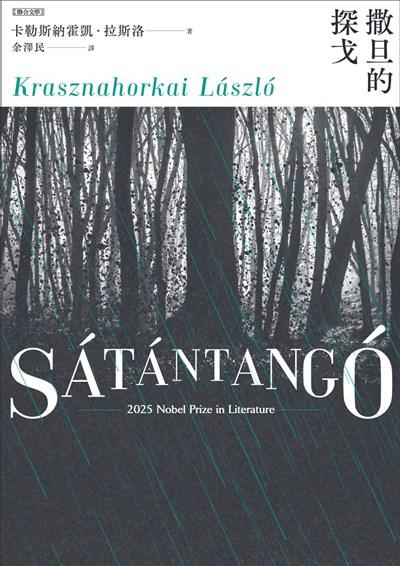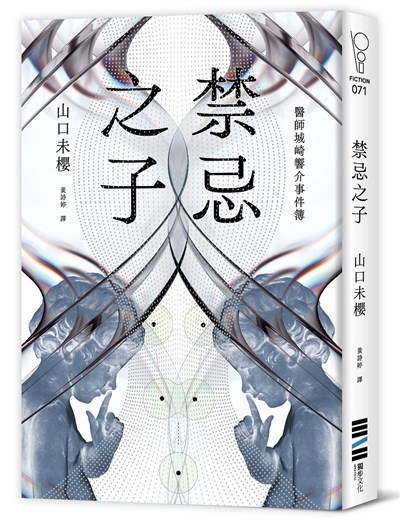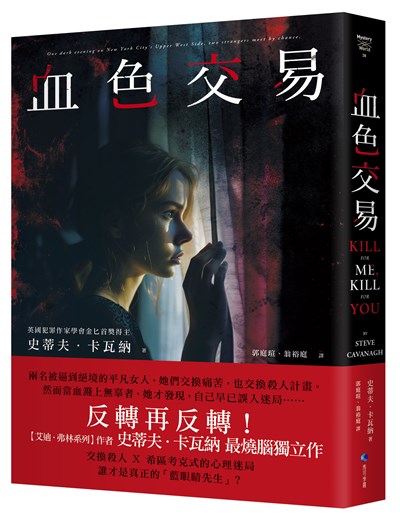從部落原鄉到都會城市等題材,泰雅族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帶領讀者經歷了一場文化遷徙過程。許多原住民急欲到都市找尋自小嚮往的未來夢,那些從山上望去如繁星墜落的原野,卻帶來許多社會化的適應與衝突,水泥城市的種種又何嘗不是處處野蠻。
文章節錄
《城市殘酷》
最初的狩獵
老人把第五個鐵絲編成的陷阱完成,放入坐在草地上的小孩手中。這次,老人捲起褲管,露出枯枝模樣,多瘢痕的腿。他唾些口水在掌中,拾起細麻繩,就著大腿搓了起來。
「尤達斯(泰雅族語,祖父之尊稱),這做什麼用呢?」小孩瞪大眼睛,那散落的細麻繩逐漸接合成固結一線。
「捕貓頭鷹,夜晚你聽到樹林裏傳來『噗嗚──噗嗚──』的東西。」
「我知道,」小孩興奮地站起來,左手支著左腿。「眼睛會發光的大鳥!」
老人微笑起來,伸出蟹角一樣的手,把成形的繩線,遞向小孩。此時,山澗傳來琤琮的聲響,就在他們附近。
「要學呢?尤達斯教你。」小孩拍起手來,手中的鐵絲陷阱與繩線紛紛掉落草地上。「沒人再肯用心學這技藝了,連你雅爸(泰雅族諳,父親之稱謂)只願意到都市裡!」
「喔──」小孩低吟一聲,他不知道尤達斯為何把眉頭蹙得都打結了。「可是,我要捕山豬,能嗎?」小孩癡望繞在老人脖子上,用豬牙串成的項鍊。
「當然能,別忘了,你是泰雅族人。」老人停下手上的工作,伸手把項鍊取下來,套入小孩的脖頸。
「這會令你記住的。」
小孩俯下頭,兩手玩弄著項鍊,還拿到耳旁敲擊起來。他忽然想起什麼,停止了遊戲。「上個月,在八雅鞍部不是有人用陷阱圈到一頭山豬嗎?怎麼又給跑了?」
「他們鞭打牠,掙跑的。」老人對遠空睥睨地笑了一下。「真正的獵人,應該學習用番刀勇敢地插入山豬的脖子,那是牠最弱的環帶。」老人比畫看,拾起番刀橫在脖子部位,小孩點頭表示懂得。「這才叫勇士哪!」
小孩背後突起的草叢窸窣著,一陣風在草上吹過。
「尤達斯,教我做勇士。」小孩露出雪亮的眸子,一下子,又羞愧地垂下頭,望草地。「你也是勇士囉!」
老人被小孩的問話逗弄得傻笑起來,然後定睛看著小孩。那尚未完全長熟的骨架竟承載泰雅族桀傲英勇的血液哩!
那微微擺動的草叢突然像海浪般喧嘩起來,然後從中分撥,赫然一對烏濁的山豬眼出現,猛地朝小孩背後襲來。老人弓身躍起,幾十年的狩獵經驗,使他的判斷,精準地,用番刀狙取牠的頸部,老人也被山豬鼻側的獠牙撕裂了腑臟。小孩跌靠在澗邊的沙土,左頰感覺到濕冷,他睜開眼,看見山豬抖動前腿站了起來,委實是老人未能將牠一舉殲滅。小孩一骨碌站起,拐著腿奔向前,他的小手驚顫地握住刀柄,閉著眼睛把插在山豬頸部的番刀,奮力地推了進去,當他能夠感覺出這頭野獸終於倒在地上,他睜開了眼。「這難道就是學習勇士的代價?」
有一會兒,他才聽到自己的哭聲,彷彿繞過了好幾個山頭。
女王的蔑視
第一次見到她是在1942年,2002年在靖國神社廣場再度見到她,時間穿越了60年,她仍然像一支番人的箭矢,準確地射中我的心臟。
1942年,我以警備補的名義被任命到一處中部蕃社任職,樟木構造的駐在所位居蕃社制高點,我的宿舍在整個駐在所最後一廊的右側,再過去就是懸崖,正確的說,駐在所的西、北面是崖壁,東、南面以高約三米的石牆隔開蕃社,簡直就是一座堡壘,天知道我們懼怕些什麼?
雖然沒有人打掃,駐在所木質廊道經常保持著潔淨,廁所挖空的圓形木桶狀內壁也恆常涮的發出沉穩的光亮,這是怎麼辦到的?第三天到蕃社出勤,我被命令儘速向駐在所報告一日所見,天色還沒有完全降下黑幕,就在後廊轉角處隱約視見移動的女子,她像一抹森林飄動的雲彩瞬即隱沒山中。我後來才知道她是早晚整潔駐在所的清潔婦。
隔日清晨我特意在竹雞尚未啼叫前醒來,轉進廁所,果然看見清潔婦――其實是位面容皎白的少女――手持清潔用具離開廁所,我們在廊間相遇,少女彷彿視若無物,我卻清楚的看見盛開的櫻花亦遠遠不及的臉龐,和那額頭上一抹青綠色的黥紋,在我看來,那是一株晨霧洸漾的鑽翠。
從同僚口中知道少女是位孤兒,父執輩的親屬曾經在早期的理蕃事業中喪命,所長念其孤憐,引進駐在所從事清潔工作。接續的幾天,我總是心不在焉,總要趁空徘徊駐在所,雖然幾次遇見少女,她仍然像一隻山中悠遊的雲豹,額頭上的鑽翠宛如宮殿禁止俗民百姓通行的禁令,我試著呼喚她的名字,少女卻讓整個廊道靜默如神秘難測的荒野之地。
一日清晨,我又因輾轉反側而早起,幾乎是夢遊一般來到廊道盡處,這時我發現了我的女王,她露出皎白的後頸跪著擦抹地板,我終於忍不住抱住了她,我的嘴巴無法發出少女的族語,但她毫無抗拒隨著我的帶領來到了不遠的宿舍,她很快的脫下包藏著美麗軀體的餘物安靜地躺在溫熱的床褟,像一隻馴服的雲豹發出難以抗拒的野性之美,我用日語一邊說著空泛的承諾之語,一邊熱烈的與山中的少女會合,整個癡迷的過程,少女始終不發一語,她默默的忍受我的衝撞,眼神卻無法掩飾落難的女王遭到侵犯的蔑視,從此以後,我再也不曾獲得如此錯綜複雜的經驗。
一個月之後,我離開駐在所前往南洋參加創造大東亞共榮圈的聖戰。六十年之後,已成老婦的少女來到了我所在的東京都靖國神社,少女的名字細瘦的夾雜在台灣慰安婦名單上,那鉛黑色細瘦的字體就像一支番人的箭矢,從1942年起堅定的啟程,跋涉千里、準確無誤地射入――我的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