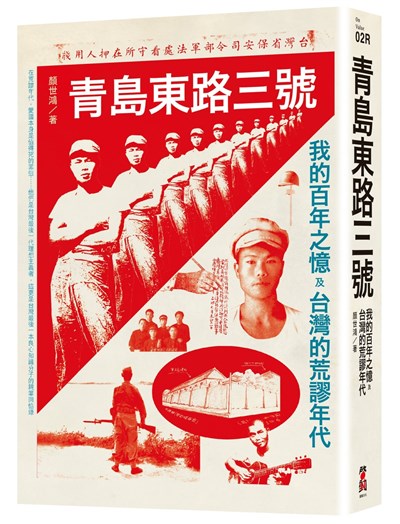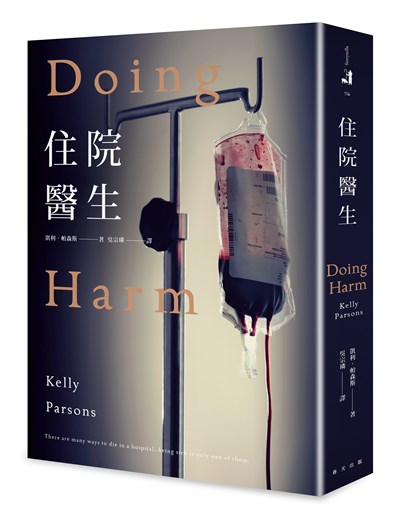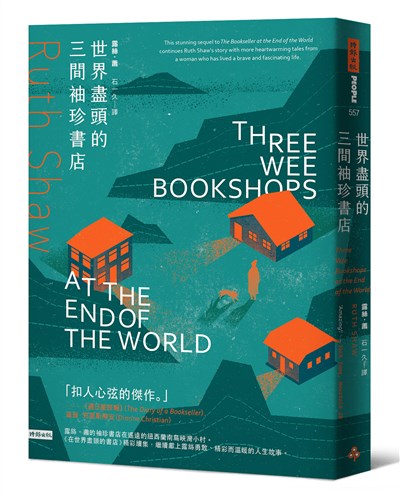這本書是鍾怡雯散文作品《野半島》的延伸之作,但風格迥異,褪去野氣灑脫適意、色彩鮮明,雖逢母喪,卻以此為新的契機,過去曾逃避、無法深入處理的身分認同情結,從養貓、看樹、餵鳥、旅行的日常生活中,明確定位「家」之所在。
文章節錄
《麻雀樹》
麻雀樹,與夢
大前年的事了,社區入門口那四棵高及二樓的棕櫚還健在時,麻雀分批夜宿棕櫚和小葉欖仁。棕櫚最後被鋸了,只剩樹墩。失去樹和樹影的掩映,紅磚牆在陽光下亮得刺眼,樹墩的年輪對著藍天無語。
好端端的幹麼鋸樹?
問了幾個鄰居,說是隔幾間的鄰居嫌麻雀吵,推說棕櫚的根會破壞地基,逮到機會便把樹殺了。這是個藉口。真正的禍首是住在棕櫚樹上的麻雀。棕櫚是被誤殺,殃及池魚。誰教棕櫚長在他家正對面,還讓麻雀夜宿,就更該命絕。
去年春天,從怡保回來隔天清晨,我到三樓灑水,咦,有什麼不太對?
磚牆。眼前這磚牆怎麼特別顯眼?停了幾秒,突然醒過來,喔,小葉欖仁。小葉欖仁被腰斬了。四樓高的大樹剩不到兩樓,樹幹筆直朝天,無枝無葉,紅牆因此在天光中顯得特別醒目。受傷的殘樹木訥訥地,有苦說不出。麻雀失去了棲息之地,我的視覺彷彿也頓失依靠。不論從哪一樓望出去,都覺得很空洞,一如我的心情。
怎麼老是拿樹開刀?
每天望著光禿禿的小葉欖仁發呆。八重櫻一如往常,稀落開過便冒綠葉,交差似的,好像長葉子才是它的正事。大概小名取壞了,我們都叫它小櫻。叫久了連開個花也小家子氣。吉野櫻倒是滿樹燦爛。大櫻名字取得好,花開得爭氣,葉子也長得氣派。
幾番風雨花開花落,大小櫻什麼時候綠葉成蔭了竟沒察覺。人回來了,心還掛著母親。離家二十幾年,第一次清明節返馬,不是掃墓或祭祖,而是憂心母親有什麼閃失。手術後剩下一個不會走不能講話的母親,這半條命可不能再丟了。清明節是大節日,我擔心她熬不過,步步為營,提防死神再下手,回去守著。然而,五天後,在返臺的飛機上,我決定放手。母親用各種方式告訴我,她得走了。
回來後便看見被腰斬的小葉欖仁。
有一天我在二樓整理舊衣物,突然發現,吉野櫻的枝葉在二樓窗戶外搖曳,社區中庭,社區外的竹叢,遠處的大樓,以及更遠處的天空雲影,被它茂密的枝葉掃呀掃。搬進社區隔年種的,十年花樹竟然高及三樓,成了社區最有氣勢的大樹。
樹在搖曳,風在葉與葉,枝與枝之間的舞動千變萬化,我看得入神,發起呆來了,滿腦子母親有苦說不出的表情,像那些遭橫禍的樹。
看樹跟發呆,就成了母親過世前過世後,我最常做的事。
等我再次從怡保回來,八重櫻和吉野櫻的綠蔭愈濃,小葉欖仁掙扎著從腰斬之處冒出新枝。大別母親之後,這世界彷彿失去重力,走起路來腳底沒辦法著地似的,跟鍾太太被地心引力拖著走不動的樣子,全然相反。母親一放手,我成了斷線風箏在空中飄浮遊蕩,不知什麼時候能夠降落,落點又該在哪。
就看樹。看樹枝樹葉,也看看不見的根。有根多好啊。
一天黃昏在社區散步,忽然發現燈光下的吉野櫻長滿一粒一粒的什麼,走近一看,喔,麻雀。
吉野櫻長了一樹麻雀。
不只開花散葉長櫻花果,夜裡,這樹還長得出麻雀,隔天太陽出來,像霧水一樣消散無痕,枝歸枝,葉歸葉,讓人懷疑昨夜的麻雀樹是個夢。真希望半夜幫母親穿殮服的場景也是個夢,日出之後,還能打電話叫媽。
麻雀樹之夢竟然持續了一個多月。如果真是夢,這夢也太長了些。四月底到六月初,我夜夜倚在二樓的窗口,簡直看痴了。這樹,怕長了上百隻麻雀吧?
最吵的不是早上,而是黃昏。
麻雀占位子時總是三心兩意。上下左右東挑西選,位子換了又換,有時七八次了還無法定位。挑位子時碎碎唸,搶位打架時更不得了,又氣又急像開罵,懂鳥語恐怕會發瘋。小傢伙可不這麼想,麻雀一來牠總是很激動,發出一長串頻率奇怪的類鳥叫節奏。我學法語,貓學鳥語。牠學成我的生活可要大亂了。
麻雀一安靜,夜,便真正來了。
白天的麻雀很神經質,一點聲光都讓牠們起疑。夜宿的麻雀神經大條,或許因著夜色的掩護,對人類完全無動於衷。從前牠們住小葉欖仁時,只聞聲不見鳥,小葉太高了,樹葉又密。如今牠們在昏黃的燈光下現形,鄰居紛紛跑來觀賞「睡覺的麻雀」,指指點點,不停說,好可愛好可愛。
麻雀把頭埋胸口睡得圓滾滾,那麼安詳,那麼自在,如果真是夢,也是讓人微笑的溫暖美夢。或者,借用鄰居的措辭,好可愛的夢。
麻雀不只可愛,還很聰明。牠們千挑萬選的好位子,都在吉野櫻中段的葉子底下,下雨時,層層天然屏障幫牠們擋雨。我從二樓看出去,夜雨中的麻雀動也不動,雨從牠們頭上的綠傘滴落,順勢往下滑。
幹麼擔心麻雀淋雨?牠們比我睡得還沉哪。
入夏之後,麻雀回到開枝散葉的小葉欖仁。麻雀樹,就更像夢了,跟母親離世一樣。
有一天在三樓灑水,側身,卻見葫蘆竹停了隻麻雀。牠在看我。把手伸過去,沒想到牠竟跳上掌心,楞頭楞腦地打量我,眼神那麼單純那麼乾淨,一下看進了我的心。不知人間險惡啊,小東西。麻雀的頭好小好滑。比貓頭小多了。
牠沒走。偏著頭,還是看我。我也偏著頭,看牠。人鳥相望。那一刻,整個世界退得很遠很遠。
母親過世後,第一次,我流下眼淚。
這不是夢,我很肯定。
還是天天看樹,天天煮飯。腳底漸漸有了重量。我得回到日常生活。我家在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