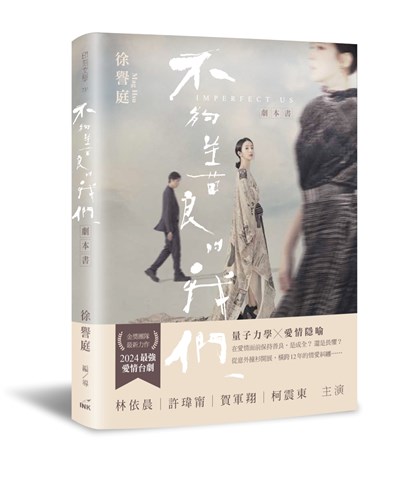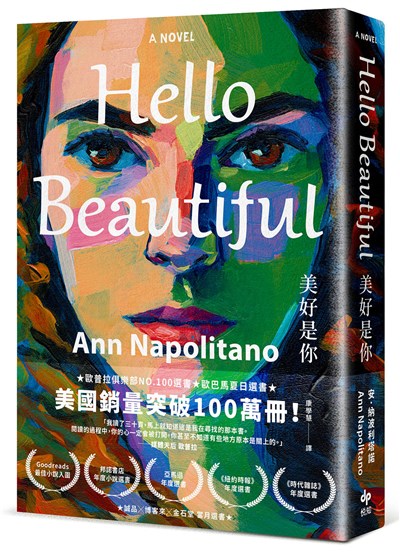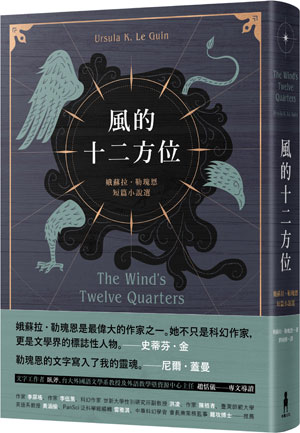
娥蘇拉.勒瑰恩是奇科幻界的標誌性人物。她的文字有女性的柔軟、男性的剛強,並以此風格屹立類型小說界至今。可是我們也想知道,在大師還不是大師,在大師也在尋找自己的「真名」時,她的文字是什麼模樣。這是她的第一個短篇選,也是里程碑。這本書是極為珍貴的創作寶藏,我們希望熟讀勒瑰恩的讀者能收藏她的起點,初來乍到者能從作家的初心開始。透過這本選輯,從中找到她諸多作品中最適合的敲門磚,開始一趟屬於讀者自己的勒瑰恩旅程。
文章節錄
《風的十二方位:娥蘇拉.勒瑰恩短篇小說選》
離開奧美拉城的人
(援用威廉.詹姆斯之論述改寫而成)
這篇心理神話的中心要旨——也就是故事中的替罪羊概念——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他的《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便闡述過。好幾人因此懷疑不解地問我,為何我致獻的對象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實情是,儘管我深愛杜斯妥也夫斯基,但打從二十五歲後,我就再沒機會重讀他的著作,忘了他曾寫過這主題。但當我在詹姆斯的〈道德哲學家與道德生活〉(The Moral philosopher and the Moral Life)一文中讀到此概念時,心裡是充滿震撼與認可的。詹姆斯如此寫道:
「又假使,如果我們能獲得一個勝過傅立葉、貝拉米與莫里斯 先生所描述的烏托邦世界,其中的數百萬人更能永遠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只是須應允一個條件:其中一個被遠遠排擠在外的失落靈魂必須過著孤獨悲慘的日子。那麼,儘管我們當下會想緊緊抓住這幸福,但是還會感到什麼樣糾結的情緒?當我們經過深思熟慮接受了這交易的結果,這樣的安逸會是多醜陋的一件事?」
很難有人能將美國人的良知困境描述地更好了。杜斯妥也夫斯基是個偉大的藝術家,想法也相當激進,但他早期的社會激進主義後來物極必反,使他成了個極端的反動分子。相形之下,儘管來自美國的詹姆斯表面上顯得如此溫和、天真、紳士——看看他是如何使用「我們」二字,假設他所有的讀者都和他一樣善良敦厚!——但他一直、也永遠都會是一名真正的激進思想家。講述了「失落的靈魂」後,他又立刻寫道:
「所有更高層次、更有穿透力的理想都是具有改革性的。它們鮮少偽裝成過去經歷所造成的結果,而是在可能對未來產生影響的起因呈現出來,也就是目前為止的環境與教訓,教會我們必須屈服之事。」
無論是在此篇故事、其他科幻小說或所有關於未來反思的作品中,都可看見對於這兩段話的直接應用。將理想視為「影響未來的可能起因」——這是多麼細膩又令人振奮的一句話!
當然,我並沒有在讀完詹姆斯的文章後坐下來說:好,現在我就要來寫篇跟那個「失落靈魂」有關的故事。創作鮮少如此簡單。我會坐下來,開始提筆講述故事,單純是因為我想。而且腦中除了「奧美拉」(Omelas)四個字外,半點概念也沒有。這四個字是來自一面路牌:薩冷(Salem)/奧勒岡州(Oregon)——並將上頭字母拼法顛倒。你不曾把路牌顛倒過來看嗎?「止停」、「行慢速減,進行童孩」、「山金舊」……薩冷等同schelomo(所羅門)等同salaam(平安)等同和平。美拉斯、奧、美拉斯。奧美拉。Homme helas(啊,人類啊。)「勒瑰恩女士,請問妳靈感是打哪兒來的?」還用問嗎,自然是因為我忘了自己讀過杜斯妥也夫斯基加上把路牌顛倒過來念,要不然呢?
嘹亮的鐘響驚飛燕雀,夏日慶典也隨之在輝煌巍峨的濱海之城奧美拉這麼拉開序幕。海港裡,可見船上纜繩彩旗飄揚。歡慶的隊伍繞行於紅頂漆牆的屋舍之間,長滿青苔的古老庭園夾道兩旁。人龍陸續穿過一條條林蔭大道、一座座寬廣的公園與一棟棟的公共建築。有些人打扮得隆重體面,長者身穿或紫或灰的硬挺長袍、工匠師傅臉上神情肅穆莊嚴,此外,還有歡天喜地、文文靜靜的婦人帶著奶娃邊走邊閒聊。在其他條街上,樂曲的節奏更為明快,鑼鼓喧天。遊行的群眾手舞足蹈,孩子在人龍間鑽出鑽進,興高采烈的喊叫聲如展翅翱翔的燕雀在鼓樂聲與歌聲上穿梭迴旋。所有的遊行隊伍都朝著城市北方蜿蜒前進,來到那片被稱作綠野的廣闊溼地。草地上,男孩女孩在明媚的陽光下一絲不掛,雙腳、足踝泥跡斑斑,四肢柔軟而纖長,趁著賽前訓練躁動難安的馬兒。馬兒身上不見半點鞍具,只套著條韁繩,連馬銜也沒給咬上。牠們的鬃毛上編著一條條銀色、金色、綠色的絲帶,鼻孔翕張,歡騰跳躍,彼此噴氣誇耀,個個興奮異常。所有動物之中,也只有牠們會將人類慶典看成自己的。在那遠遠的北方與西方,山巒半環繞著濱海的奧美拉城,早晨的空氣清新涼爽,天色湛藍,十八峰上依舊白雪皚皚,陽光輝映,猶如延燒數里的白金色火光。和風習習,吹動賽馬道上的旗幟,輕柔飛揚。在那靜謐的寬廣草地上,你可以聽見樂聲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蜿蜒迤邐,時隱時現,由遠而近,猶如空氣中一道依稀隱約的甜美香氣,輕顫凝聚,最後化為陣陣歡樂喧天的嘹亮鐘響。
多麼的歡欣啊!該如何描述喜悅、描述奧美拉城的人民呢?
儘管歡樂,但他們並不痴傻。如今,人們已鮮少將快樂二字掛在嘴上,因為歡愉的笑容已成明日黃花,而這樣的形容常令人做出特定的假設。聽到這樣的描述,你可能會聯想到一名國王,不是騎在高大駿馬上,尊貴的武士環繞身旁,就是坐在一頂由結實魁武、肌肉賁張的奴隸高抬的金輦上。但奧美拉城沒有國王,他們不用劍,也不畜養奴隸,並非民智未開的野蠻人。我不清楚他們社會的規令和律法,但想來肯定不多。正如他們沒有君王與奴隸,奧美拉城中也無股市交易、商業廣告、炸彈或祕密警察。不過我必須重申,他們並非痴愚,既非單純敦厚的牧羊人,也不是出身高貴的蠻族,或溫和乏味的烏托邦主義者。他們就和我們一樣複雜。問題在於,我們有個壞習慣,而且在迂腐學究與世故之人的推波助瀾下,我們開始將快樂視為一件愚蠢之事,唯有痛苦才稱得上智慧,唯有邪惡才有意思。拒絕承認邪惡的平庸陳腐與痛苦的窮極無聊,是藝術家的不忠之罪。如果打不贏他們,就加入他們;如果會痛,就再來一回。但讚揚絕望就是譴責喜悅,擁抱暴力就是放棄一切。我們幾乎就要失去一切了。我們已經不知該如何描述一個快樂的人,也不知要如何歡慶喜悅。我該如何描述奧美拉城的人呢?他們並非一群天真快樂的孩童——儘管他們的孩子確實過得無慮無憂。不,他們是一群成熟、智慧、充滿熱忱的成年人,生活幸福而美滿。喔,多美好的奇蹟啊!真希望我能描述地更好,讓你們能夠相信。從我的話聽來,奧美拉城就彷彿童話。好久好久以前,在一個好遠好遠的地方。假若你能想像,或許最好是讓你自己去勾勒,因為毫無疑問,我無法滿足所有人的想像。比方說,科技呢?我猜想,你不會在他們的街道與空中看見什麼車輛或直升機,這點也符合奧美拉城人民幸福快樂的形象。因為快樂是建立在你能清楚分辨什麼是必須的、什麼是非必須但又不具危險性、什麼又是危險的基礎上。然而,在上述的第二大項中——也就是那些非必須但又不具危險,安全舒適、奢侈豪華、充裕富足的東西等等之類——他們仍可擁有中央空調、地鐵列車、洗衣機,以及所有這兒尚未發明的神奇之物,像是漂浮的光源、無燃料動力、能夠治癒感冒的配方等等。又或者,這些東西他們可以一樣也沒有。無所謂,你開心就好。我自己喜歡想像這些來自濱海城鎮的人是在慶典前幾天,搭乘小小的高速火車或雙層列車來到奧美拉城,而奧美拉城的車站本身也是城裡最美輪美奐的一棟建築,只是比起雄偉壯觀的農夫市集,仍稍顯遜色。但即便有火車,恐怕在你們部分人心中,奧美拉城仍是個天真純潔、充滿粉紅泡泡的地方:笑容、鐘聲、遊行、駿馬……哼,那又怎樣。若是如此,請自行在腦中加上一場雜交派對――如果雜交派對的形容能幫上忙的話,別遲疑。不過,請別想像那是發生在某座神殿之中,美麗的祭司或女祭司已陷入半狂喜狀態,一絲不掛,準備好要和任何男女翻雲覆雨,愛人也好,陌生人也罷,只要能和深具神性的血肉之軀合而為一就好。儘管這確實是我閃過腦中的第一個念頭,但說真的,最好還是別想像奧美拉城中有任何神殿或寺廟——起碼別是有人看管的廟宇。宗教,可以;神職人員,不行。當然了,那些美麗的赤裸胴體大可四處遊盪,將自己當作神聖的舒芙蕾般獻身給飢渴的欲望與狂喜痴迷的肉體。就讓他們加入遊行的行列吧,就讓他們在鼓樂聲中交媾,在鑼鈸聲中迸耀欲望的榮光。還有(這並非無足輕重的旁枝末節),別忘了這些歡欣儀式孕育出的後代會得到所有人的關愛與照料。我唯一確知的一件事,就是奧美拉中沒有內疚與愧歉。但除此之外,還該有些什麼?起初,我認為那兒沒有毒品,但這也太清教徒了。對於那些喜愛者來說,「珠籽」(drooz)那隱約而持久的香甜能為奧美拉城增添幾許芬芳。它先是能為頭腦和四肢帶來輕盈與明亮,幾小時後,是一種恍恍惚惚的慵懶感,最後會讓你看見神奇的幻象與宇宙最深奧難解的祕密,並體驗到超出任何想像的性愛快感,而且它並不會使人上癮。對於口味溫和些的人來說,我想奧美拉城中應當有啤酒。除此之外,這座歡樂的城市中還該有些什麼呢?勝利的榮耀?這是自然的,以及對於勇氣的讚揚。但是,就像將神職人員排除在外般,我們也別在奧美拉城中安排士兵。建立於殺戮上的喜悅並不正當。不行,那太可怕了,而且無關痛癢。那分源源不絕、慷慨豐盛的富足感,以及那分巨大輝煌的勝利榮耀,並非來自抵抗外在的敵人,而是與世上所有最美好善良的靈魂和諧共處,與燦爛的夏日交融並存。這才是盈滿奧美拉城人民內心的快樂。他們所慶祝的勝利是屬於生命的勝利。我不認為奧美拉城真有那麼多人需要珠籽。
此刻,多數的遊行隊伍都已來到綠野。誘人的食物香氣自紅色與藍色的炊事帳中傳出。小孩臉上黏呼呼的,極為可愛。有個男人的親切灰鬍間也沾上些許香濃糕點的殘屑。少男少女都已上了馬,開始聚集在賽道的起跑線上。一名笑容滿面、矮小肥胖的老嫗將籃中的鮮花發放給大家,高䠷的年輕男子將她的花佩戴在他們閃閃發亮的髮上。一名年約九、十歲的小孩獨自坐在人群邊緣吹奏木笛。人們駐足聆聽,臉上綻露笑容,但並沒有開口與他交談,因為他只顧自己吹個不停,對眼前人潮視若無睹,那雙黝黑的瞳眸完全沉浸在甜美輕盈的旋律魔法之中。
吹奏完畢,他緩緩放下握著木笛的雙手。
他這分小小的沉默宛若信號,霎時間,起跑線附近的亭子傳出嘹亮的號角鳴號,激昂、惆悵,響徹雲霄。馬兒立起纖細的後腿,其中幾匹還嘶鳴回應。一臉肅穆的年輕騎士撫摸馬兒脖頸,輕聲安撫:「噓,噓,我美麗的馬兒,我的希望……」參賽者開始在起跑線上排成一列,賽場邊的觀眾猶如風中的青青草地與野花。夏日慶典開始了。
你相信嗎?你能想像這樣的慶典、這樣的城市、這樣的喜悅嗎?不能?那麼再讓我多說一件事。
在奧美拉城一棟美麗公共建築的地下室,也或許是一座雄偉私宅的地窖中,有一間房。房前有道上鎖的門,房內沒有半扇窗。灰濛濛的微弱光線先是穿透地窖某扇結了蜘蛛網的窗,然後才自房牆木板的裂隙鑽滲而入。這間狹仄房內的角落上擱著兩支拖把,拖把頭糾結乾硬,惡臭難當,附近還有只生鏽的水桶。地是泥地,摸上去有些潮溼,就像大部分的地窖一樣。這間狹室約莫只有三步長、兩步寬,就是個掃帚間或廢棄的工具室。一名孩子坐在房內,或許是男孩,或許是女孩,看上去年約六歲,但實際上已經近十歲,智能不足,或許是因天生殘疾,也或許是因恐懼、營養不良和疏於照顧而變得痴傻。他(或她)摳摳鼻子,偶爾心不在焉地摸摸自己的腳趾或生殖器,縮著身子,坐在距離水桶和兩根拖把最遠的角落。他害怕那些拖把,覺得它們很恐怖。儘管閉緊了雙眼,仍知道拖把在那兒,而且門前上了鎖,不會有人來救他。門永遠是上鎖的,也永遠不會有人來,除了有時候——這孩子不了解時間的概念,也不懂時間間隔的計算——門會發出駭人的嘎吱聲,然後打開來,外頭站著一個人或好幾個人。其中一人或許會走進房內,踢踢孩子,要他站起來。其餘人從來不曾上前,只是用驚恐厭惡的眼神在門口窺探。對方會匆匆在飯碗與水罐內裝滿食物和水,然後將門重新鎖上,那一雙雙眼珠也跟著消失不見。門邊的人影從來不曾開口,但這孩子並非一出生就住在這工具間內、而且依然記得陽光與母親的聲音。他有時會出聲哀求:「我會乖的。」他說,「求求你們放我出去,我會乖的!」但他們不曾有過任何回應。孩子過去會在夜裡高聲求助,也很常哭,現在只會發出某種類似嗯嗯啊啊的呻吟,也越來越少開口說話了。他瘦到雙腿細如竹籤,肚子圓滾滾,一天就只有半碗的玉米粉和一些油脂可吃。身上沒有半點衣物,而且因為長期坐在自己的排泄物上,臀部和大腿都長滿潰爛的膿瘡。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所有奧美拉城的子民。有些人來看過他,有些人只要知道他的存在就夠了。大家都清楚他必須關在那兒。有些人知道原因,有些人不知道,可是所有人都明白他們的幸福、城市的美麗、彼此間相親相愛的友誼,以及孩子們的健康、學者的智慧、匠師的技藝,甚至是豐饒的莊稼與和煦的天氣,完全仰賴於這孩子悲慘的不幸。
奧美拉城的人民通常會在孩子八到十二歲懂事時向他們解釋這一切。會來看這孩子的往往都是些青少年,不過也常有大人前來,或再次來看這孩子。無論他們如何解釋,少年人一見到這景象,莫不大為震驚與反感。他們覺得噁心,而他們還以為自己早已超脫這感受。無論聽過多少解釋,他們還是覺得義憤填膺,卻又無能為力。他們想做些什麼,幫幫那小孩,但又無計可施。沒錯,若他們將孩子帶離那可怕的地方,讓他重見天日,把他打理得乾乾淨淨,讓他吃飽喝足,過上舒適的日子,那確實是件好事。但若他們真那麼做了,奧美拉城所有的繁盛、歡樂與美麗都會在轉眼間煙消雲散,化為烏有。這就是條件,用全奧美拉城的快樂與福祉來交換一條小小的生命,解救他於不幸;捨棄數千人的幸福,只為一人或許能有安身立命的機會——這與放任罪惡入侵有何異?
這條件必須嚴格遵守,毫無轉圜的餘地。他們甚至不能給予那孩子絲毫親切的安慰。
親眼見過那孩子並體認到這可怕的兩難後,那些年輕人往往不是帶著淚,就是帶著無淚的憤怒離去。這件事或許會縈繞在他們心頭好幾週,或是好幾年。但隨著時間過去,他們也漸漸理解,即便將那孩子釋放,自由也不會為他帶來多少助益:沒錯,溫飽是會帶來些許模糊的喜悅,但僅此而已。他已太過於退化、變得太痴傻,無法體會真正的快樂。他在恐懼中生活太久,無法自恐懼中解脫。那些痛苦與習慣也太根深柢固,無法再體會人道待遇的好處。沒錯,經過這麼久的時間後,若四周沒了牢牆的保護、眼前沒了黑暗的遮蔽、屁股下再沒堆積著排泄物,或許他反倒會覺得難受。待這些人體認並接受現實可怕的公平與正義後,為了那殘忍的不公不義流的淚也就隨之乾枯。然而,或許正是因為這些淚水、憤怒,以及那分寬厚之心與坦誠接納自己的無能為力,他們才能過著光明燦爛的生活。他們的幸福並不愚蠢乏味,也不輕鬆輕率。他們都知道自己就像那孩子般,並不自由。他們不是不懂得憐憫,正是那孩子的存在,還有清楚認知到那孩子的存在,城裡的建築才得以富麗堂皇,音樂才得以動人、科學研究才得以深入。因為這孩子,他們才會對其他孩童如此溫柔。他們知道,若沒有那不幸的孩子在黑暗中啜泣,那麼,當那些小騎士在夏日的第一道晨光下英姿煥發地準備起跑時,就不會有那名吹笛的孩子用歡樂的旋律為他們伴奏。
現在,你相信了嗎?這樣的一座城市是否比較有了可信度?但我還有一件事要說,一件難以置信的事。
有時候,去看了那孩子的少男少女並不會帶著淚水或憤怒返家;實際上,他們壓根沒有回家。還有時候,年紀大上許多成年男女會沉默一、兩日,然後離家而去。這些人會來到街上,沿著馬路踽踽獨行,不斷走呀走,走出那美麗的城門,離開奧美拉城。每個人都孑然一身,不分男女,無論老少。夜幕降臨,這些旅者走下村莊的街道,穿過兩旁房舍燈火昏黃的窗,來到漆黑無名的郊野。每個人都形單影隻,朝著西或北方的山間而去。他們不停前行,離開奧美拉城,走進黑暗,再也不曾歸來。他們去的地方,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說比起這座幸福之城更難以想像,我無法描述。也或許,它根本並不存在。但他們似乎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那些離開奧美拉城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