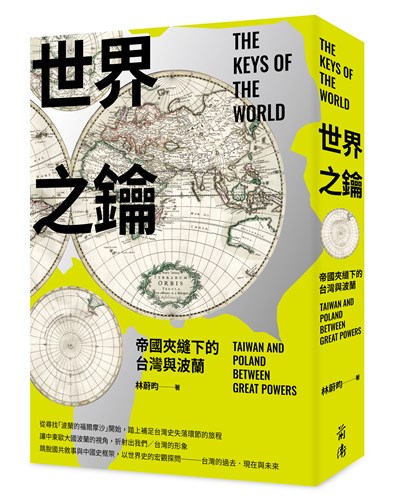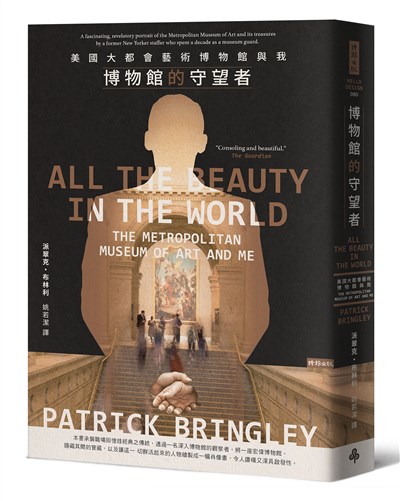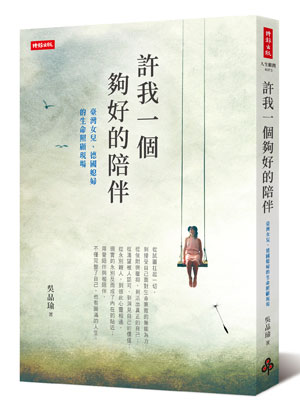
吳品瑜是台灣女兒、德國媳婦,因為選擇陪伴德國婆婆從癌末到往生,進入照顧的現場,每分每秒都是直面自己的淬鍊,一步步學習用「愛」陪伴與被陪伴。期間歷經各種自我的內在掙扎、與孩子的衝突、和婆婆的磨合、身為照顧者的心路歷程、漸漸明白被照顧者的心情…。深刻體會到:「先陪伴好自己,才能好好陪伴他人。」書中不僅僅觀照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也深刻書寫自我成長的歷程,在高齡化社會的台灣,本書非常值得閱讀。
文章節錄
二○一四年三月,全家自旅居五年半的上海,搬遷至吉隆坡,從灰霾沉靄的料 峭春寒,來到怡紅快綠的熱帶雨林。誰知道尚待在服務型公寓,努力找尋新住所的我們,在第三週的某個晚餐後與婆婆網路視訊時,得知她因食欲不振與下肢腫脹,隔天得緊急入院檢查。幾日之後,先生難過地說婆婆是膀胱癌末期,癌細胞早已擴散下腹腔與骨髓,推估至多只有三個月的生命,醫生認為沒有積極治療的必要,便讓婆婆自行回家。
寡居西南德山村多年的她,因為三名子女都不在身邊,也不願意進入安寧病 房,便由基福會進行每日探視與送餐。
當先生靜默地走回房間,我立刻訂了機票,準備隔週帶著三名孩子直飛德國。平日遇上狀況總是猶豫未決的我,竟然迅速地擅自決定,並且自告奮勇地願意回去擔任居家安寧照顧的工作,甚至開始計畫將孩子暫時轉學回德國的相關事宜。至於才剛履新不便請假的先生,知道後只能沉默地接受這權宜之計。
這是我難得地「自作主張」,其後更得學習為這決定負起責任,並且承擔所有 的發生,而不是期待他人的包容與理解,甚至是感激。
然而,當日子越逼近回德國,我越是焦慮。吉隆坡的新生活還毫無頭緒,德國婆婆那邊似乎又是一個陌生與未知的開始,抑或是結束?
我所不知道的是,新生活的混亂不是眼下婆婆的癌症所引發,而是我內在經年不知、無能或不願處理的生命課題 ——「自我」的混亂。
除了「媳婦」這個角色?或是還有更本然的「自我」?行前兩天的清晨,參加德國友人的聚會,當大家聊著接下來的復活節度假計畫,我提到因婆婆罹癌得趕回德國,在座其中一位德國太太訝異地反問我:
「你婆婆生病跟你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要犧牲自己的復活節假期呢?」
「你是誰?」另一位更直白地質問我。經這麼一問,我呆愣地說不出話來,腦門轟隆作響,僅聽見她們正色且斬釘截鐵地說:「你與婆婆是沒有任何關係存在的!」後來,在場同樣嫁給德國人的臺灣友人也質疑我,德國有完善的醫療系統與居家照護,根本毋須子女勞心費力,況且媳婦是外人,為什麼非得親自回去一趟呢?
「於事無補!」這是他們一致的答案。
幾乎超過我所預期的,周遭朋友的諸多質疑,一一拆解了我回德國的正當性,將我逼到死角,非得重新審視「媳婦」的角色,並且釐清自己回德國陪伴婆婆的動機。尤有甚者,當「犧牲奉獻」被視為多餘且無用時,自我感覺良好開始鬆動、稀釋,而「自我」也成了被放大檢視的目標。
無可否認的是,得知婆婆癌末,訂機票回德國的當機立斷裡,50%是被腦袋 裡傳統主流的臺灣媳婦角色所制約,驅使自己按表操課地苦情演出,只是當下太過入戲,乃至無從辨識罷了。另外,49%的決策考量是期待先生的理解,因為婚姻關係近二十年,我們的互動並不好,他總是位居強勢的一方,生活時刻一再被他厲聲責罵與羞辱「笨蛋」、「沒長腦子」、「不會賺錢」與「沒有才華」,於是我每次搶先埋首苦幹,都是抱著「將功贖罪」的惶怖,企圖事前多累積點數,以免衝突發生時,一下子被價值歸零,甚至嚴重負分,導致先生說出更傷人的話語。
老實說來,我人生的戲路並不寬廣,演技也從未能突破,不管扮演青衣或花 旦,乃至老旦或龍套,各種角色的演繹都如出一轍的苦情,反正就是「臺灣阿信」 從出生一路演到老。在家暴的原生家庭裡成長,形塑了我的自卑與罪咎感,我學會用憋屈向命運低頭,以免拳頭將我打得眼冒金星。我也專挑吃力不討好的活,死命埋首工作避免與人正面衝突,並利用缺乏現實感且無限探底的自我犧牲,交換別人的不嫌棄。而在關係上更是像清倉大拍賣似地「輸誠」,極盡討好地試圖換來表象的「長治久安」與和諧。
彷彿唯有不被嫌棄,才能確保自己存在的可能;而以討好防腐封存的和諧關 係,才能防止衝突、暴力再度將我吞沒。
遠嫁異鄉,德國的女權高漲既未能有效教化我,試著突破那個自童年家暴形塑的「自我」,反倒時時讓我無所適從,無論是面對婆婆或先生,我刻意的溫良恭儉讓,有時適得其反地惹惱了盛氣凌人的婆婆,而落在先生眼裡更是咎由自取的軟弱 與無能。
記得二○○二年去義大利嘎達湖(Gardasee)渡假時,我跟先生據理力爭非得 帶婆婆一起去,他有些不悅,因為在講求個人主義的德國,並不時興承歡膝下,更遑論有孝順的概念,他還提醒我婆婆有很多「漏電板」,少有人能跟她好好相處。
果不其然,在度假別墅的第一個晚上,揮汗烹煮的蒜茸蒸蝦、番茄海鮮義大利 麵與巴西利炒蛤蠣才端上桌,婆婆馬上垮下臉說:「我們德國晚餐不吃氣味重的食物,你這樣搞得房子臭烘烘的,我待會怎麼睡呢?」隨即拿出皮包裡從德國帶來的乾硬麵包,轉身進臥房大力甩上門。
當下,老公沒好氣地數落我說:「我早就警告過你,何必帶她出來掃興呢?」 然後自顧自地大快朵頤起海鮮大餐來。
類似「好心予雷親」的哀怨戲碼不斷上演,有時明明是婆婆與我先生之間的衝突,試圖當和事佬的我還公親變事主,討來婆婆一頓痛罵:「你德語那麼爛,根本沒人聽懂你說什麼 」
每次先生總堅持要求我自己正面「反擊」婆婆,但害怕衝突的我寧願選擇自溺的哀怨,似乎永遠都學不會嗆聲,頑愚堅守臺灣苦情媳婦的角色演繹,卻怎麼都符合不了德國婆婆的要求,反而在關係中完全喪失自我,極盡討好又得不到回應後,敏感脆弱且易受傷。事實上,這隱身在「臺灣好媳婦」刻板印象的自我感覺良好,不僅是一種性格的怠惰,更是不願擺脫的慣性受害者情結。
就在婆婆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癌末,回德國陪她走完最後一程的決定裡,依然是50%慣性苦情角色演出,與49%「自我」不確定與價值低落的討好策略。
從來,當我決定做一件事,考量的都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這樣的「做」究竟能否幫助我逃避低自尊與無價值感的追殺,顯然這一切都是被陰暗的情結(complex) 所驅使。
然而,關鍵的1%是無意識的驅使,卻也以此打開意想不到的生命突圍。
未知,並非尚未發生,卻早已曖曖內含光地閃現,只是在黑暗中的我乍見刺眼的亮光,究竟是選擇慣性逃跑?抑或是迎向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