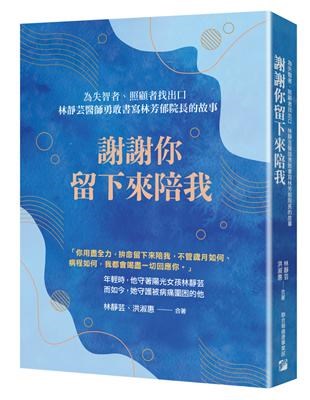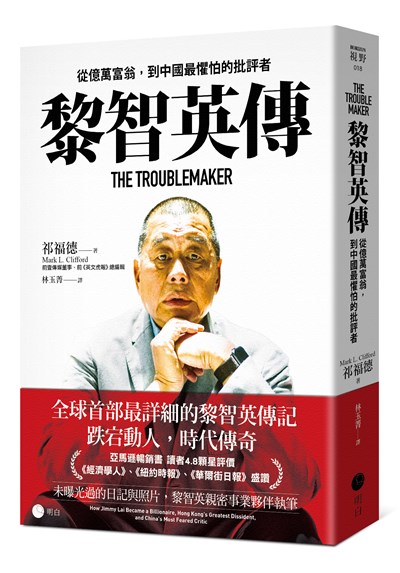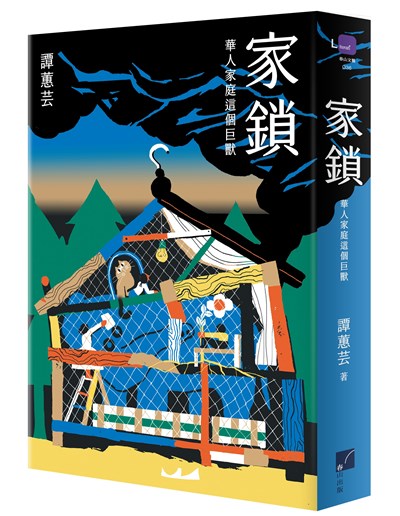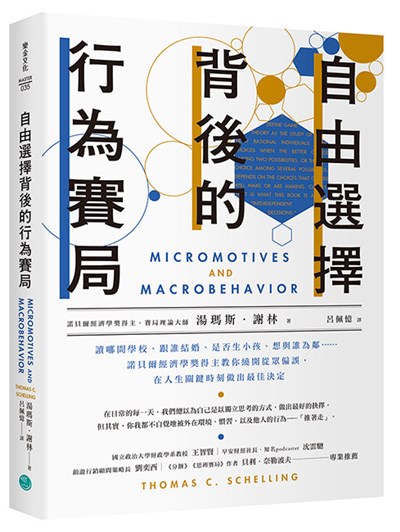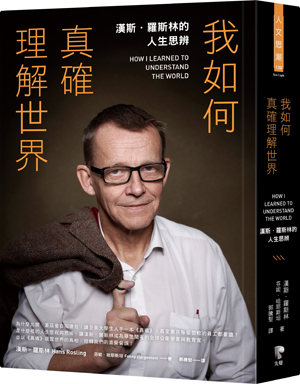
是什麼樣的人生歷程與思辨,讓漢斯.羅斯林成為舉世聞名的全球公衛學家與教育家,並以《真確》揭露世界的真相,扭轉我們的直覺偏誤?本書為羅斯林逝世前堅持寫下的人生自述。他說:「《真確》探討我們為何如此難以理解世局的發展,本書則與我個人和我如何逐漸理解這個世界有關。總而言之,這本書中沒有什麼數據,它探討我和人們相遇、交流的經過。」
文章節錄
《我如何真確理解世界:漢斯.羅斯林的人生思辨》
CHAPTER 3 來到納卡拉
我們的資源何其有限,人們對醫療的需求又是何其龐大。從那天起,當我在清晨走路到醫院上班時,愈來愈常想到:這裡的醫生人數和瑞典相比差太多了。我心想:今天有待我處理的工作,相當於瑞典境內一百個醫生的分量。所以……我該以一百倍的速度為每個患者看診呢?還是說,我只能在一百名患者中挑出一人呢?我每天都得在兩者之間採取折衷方案。
不過事實上,已經罹病卻從來不曾到醫療單位或醫院看診的病患,數量極為驚人,而我們的醫院規模也很小。我們手邊五十個床位總是客滿,其餘的患者只能躺在地板上。但限制我們提供醫療措施的並不是床位數,而是我們這些醫療人員的質量與數量。我有兩年多的執業經驗,少數莫三比克護士只上過四年學校、接受過一年的職業訓練,剩下的職員則有半數以上目不識丁。
就算瑞典境內有一百個醫生來照料我手邊必須應付的人數,莫三比克的嬰幼兒死亡率可又比瑞典高出一百倍。當你面對一百倍的需求,又只能使用百分之一的資源,你該怎麼辦?
了解我們的資源何其稀少,並且以最佳方式使用手邊的資源,成了對我的一項挑戰。這和了解鄉間居民終其一生擁有的資源何其稀少一樣困難。基本上,每個人都處於赤貧狀態,他們幾乎把所有的資源都用來養家活口;而在許多日子裡,他們仍然沒有東西吃。漸漸地,我被迫認知到自己太過好高騖遠。職員和居民努力將我的期望拉低到一個合理的水準,但這個「合理的水準」卻遠低於瑞典醫學院的教育所灌輸給我的目標。百倍的需求、百分之一的資源,表示病患與資源的比例差距達到一萬倍。一萬倍哪!我得承認,為了調適自己、了解自己該如何應付這種差異所做的種種努力,對我的大腦造成了創傷,我稱之為「我的一萬倍創傷」。
關於大眾資源匱乏的心理學,使我更為深入地認識自己。你會以為自己生命中的價值是絕對的,你不覺得自己會蓄意打死一個小偷,直到你被推到臨界點為止。我們原有兩輛救護車,某天夜裡,有人鑽開其中一輛車的探照燈座,偷走了白熾燈泡。這表示那輛救護車再也不能在夜間出勤了。
這起竊案使我感到濃厚的恨意。要是我逮到那個小偷,我擔心我會打死他,就像當初我準備撞死那個偷走我們畜養的鴨子的竊賊一樣。那些鴨子是孩子們的開心果,在這個由中央政府管控、平民難以取得食物的計畫經濟體中,牠們更是我們的肉類來源之一。但是某天夜裡,安妮塔被鴨子的吵鬧與尖叫聲吵醒。她探頭朝窗邊一望,看到有竊賊正在偷鴨子。他很快就衝出鴨舍的門口,我開車緊追在後。突然間,他出現在我前方的路上。我踩下油門,衝過街角,繼續加速。
「幹!他甭想偷我們養的鴨子。」我腦中響過一個聲音。
這時我意識到:我正準備要撞死他。我及時冷靜了下來。
那個竊賊趕緊溜進一個街角,消失不見了。算他走運。在沒有司法體系的社會裡,人們動用私刑的方式可是很殘酷的。
…………
我們的瑞典朋友在我們家前方剎車,笑著從車內走出。我們的住處並不難找。
「我們遵照你們的指示,問大家醫師住在哪裡。他們全都指對了耶!」
這對夫婦週末前來拜訪我們。他們與我們年齡相仿,也是透過同樣的招聘機構,準備到兩百公里外的楠普拉大型省立醫院任職,最近才抵達莫三比克。他先前在新生兒部門擔任小兒科醫師。
家裡有訪客是很美妙的事。我們都很想講話,也渴望與能夠了解我們處境的人對話。我們聊得太投機,以致這頓午餐拖了很久。大半時間我們都在比較雙方的工作場所。
「我底下所有的護士都沒受過專業訓練。」他說。
「我有一半的職員不識字。」我回答。
我們繼續以一種相當男性化的方式各說各話,不過事情仍然很清楚,我們工作上獲得的資源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而情況也必然是如此。省立醫院必須培訓出新的醫療職員,前提是醫療體系必須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之上。
厚實、暗褐色的大門門板上傳來的劇烈敲門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由於電話不通,一位護士徒步從醫院走到我家,請我出動。原來是院裡來了一名患有重病的孩童。
我們驅車前往醫院。我朋友跟我借一件白袍穿,和我一起去看看醫院的情況。我們踏進狹小的急診室時,見到一名母親;她的雙眼充滿驚恐,努力想給一個極其瘦弱的孩子餵母奶。這個才出生幾個月的小孩雙眼凹陷,幾乎毫無意識。護士表示,這個孩子有嚴重的腹瀉。我先用手指在小孩肚子上捏出一個皺褶,鬆開手以後
皺褶仍未散去。診斷結果很明顯:這孩子由於不斷脫水,即將死亡。
小女孩現在極度虛弱,已經無法接受哺乳。我將一根細管插進小女孩的鼻子,深入她的胃部,然後告訴護士應該使用哪些補液、劑量該定在多少。
我的朋友驚駭不已。當我差不多完成治療時,他抓住我的肩膀,將我拽出狹小的急診室。他在走廊上用充滿怒意的眼神瞪著我。
「你太不道德了!換做是你自己的小孩,你絕對不會使用這麼低劣的治療法。這個患有重病的孩子需要立刻接受靜脈內輸液,你卻只使用細管提供補液療法,罔顧這孩子的性命。她會嘔吐,無法獲得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水分與鹽分。我看你是急著在晚餐前到海灘透透氣才會這麼做。」他說。
他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他還沒有被迫接受我已經體認到的殘酷現實。
「不。在這家醫院,這就是標準治療法。根據手邊資源以及包括我在內所有可調動的職員人力,我們就只能做到這樣。每個星期,我總得挑出一、兩個晚上回家吃飯,要不然我和家人在這裡是撐不了一個月的。你也許得花上半小時才能給這孩子打點滴。此外我也知道,護士很有可能不具備管理點滴的技能,這孩子可能完全得不到補液。用細管給予補液比較快。你得接受我們這裡提供的醫療水準。」
「不,我不接受。用細管來治療這個孩子,太沒有道德了。我打算為這孩子做靜脈內輸液,你休想阻止我。」我的朋友說。
我沒有攔阻他。醫生辦公室的一個櫃子裡,還有幾支給嬰幼兒打點滴時會用到的細針筒,我把它們取來。我朋友多次嘗試將針頭插入靜脈,卻一再失敗。然後他要求取來在小型手術中觸及血管所需要的設備,做了個小手術,護士也盡全力協助他;我則回家和家人以及我朋友的太太一起吃晚餐。由於沉重的工作量,我已經一連多天沒和家人吃晚飯了。之後,我才回醫院接這位同事。他費盡千辛萬苦,總算啟動了點滴,小孩的狀態略有好轉,但仍然沒有接受哺乳。
當晚我們徹夜未眠。孩子們就寢後,我和這位朋友坐在沙發上,針對最符合醫學倫理的措施,促膝長談。這是我們之間一次坦誠的對話。
「你得盡全力救治每一個到醫院看診的病患。」他說。
在牽涉到醫學倫理的討論中,數量是很重要的因素。當討論範圍限定為一名患者時,把事情做對並不困難。
「不對,投入所有的資源和時間,試著救治每一個來到醫院的人,才是不道德的。」我回答。
我解釋道:假如我多花時間,致力於改善基層的醫療服務水準、社區醫院與小型衛生處,我們也許能更有效地降低嬰幼兒的死亡率。我的任務是盡全力確保這座城市與其鄰近郊區內孩童的健康與存活。我堅信,大多數死於可防治性病因的患者,都是死在自己家裡。如果我們集中職員人力與資源,使醫院提供最優質的醫療服務,接受疫苗注射的孩童人數將會減少,社區醫院人力會更加欠缺,孩童的總死亡人數將會遽增。對於在我面前死掉的孩子,以及沒有在我面前死亡但之後卻仍然死掉的孩子,我都有責任。面對手邊拮据的資源,我不得不接受醫院的治療水準低落,導致事倍功半的事實。
我的朋友不贊同這種看法,他的立場和醫院裡大多數的醫師和群眾相近。他認為,身為一個醫師,面對每一位前來求助的患者,都必須全力以赴。
「你認為自己能救助更多身處其他地方的孩子,但這不過是理論性的猜測罷了。」他說。
大約到了這個階段,我就不再爭辯了。但我心想:徹底研究你的努力在哪些地方能夠救助更多人,豈不是比全憑感情行事更合乎道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