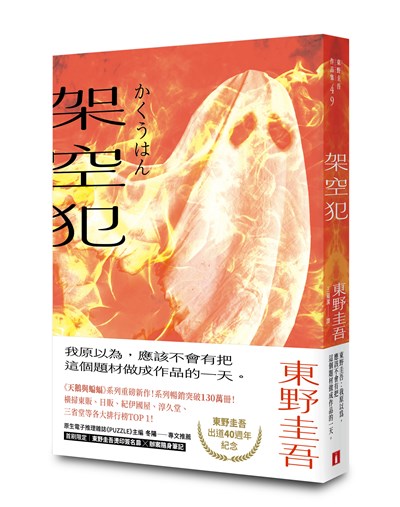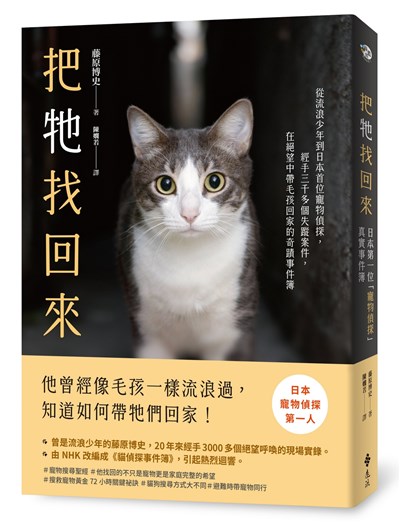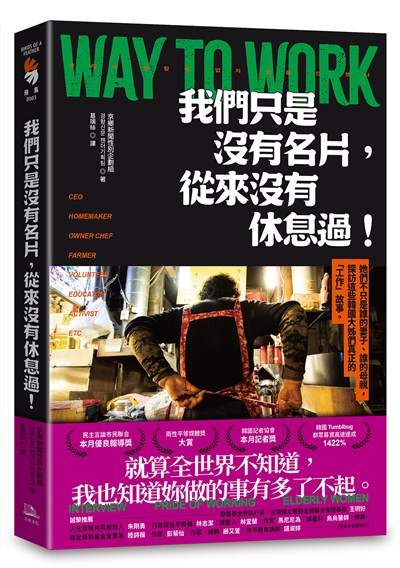以往大家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集中營的文學作品,大多是猷太人受害的故事,《呼吸鞦韆》則敘述幾乎不為世人知道的羅馬尼亞人在俄國勞役營的悲慘經歷,更特殊的是,作者荷塔‧慕勒的母親曾經歷這段悲慘過程卻從不提及,成為她寫此書的原動力,她也在2009年寫完這本小說後,同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桂冠。
作者是出生在羅馬尼亞的德裔,一向擅長書寫女性題材,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少數女性得獎者之一,這本作品與她過去的創作大不相同,而是以真實事件為藍本的小說,可算是不純為虛構的紀實文學與傳記文學,但筆法又不是很寫實,從書名到文字都充滿詩意,是一個主題深厚嚴肅,寫法充滿感性與想像力的小說。
故事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羅馬尼亞人被送到俄國勞役營,幫助俄國做戰後重建的苦工,其實,就是書寫作者的同鄉、德裔羅馬尼亞籍詩人奧斯卡.帕斯提歐爾(Oskar Pastio)的集中營經驗,後來乾脆與奧斯卡合寫,將其一生的故事寫出來,那也是羅馬尼亞人在二戰後,從烏克蘭到俄國再到德國的流亡史,是鮮少記載的歷史真相。
這樣一部殘酷集中營的斑斑血淚史,作者未採取直接控訴手法描述,而是以冷峻、簡潔、幽美的詩意文字來呈現離鄉背井不安的流浪,跳躍、活潑的思維,使得文句流動中,帶些幽默與反諷,也使苦難的歷史有了不一樣的深度,這種特殊的寫作風格,使得很多人處理過的集中營故事有了不同的風貌,閱讀起來也不那麼沉重,讀者可以細細品味字句安排中溢出的想像力與龐大的力量。
文章節錄
關於行李打包
我帶上我所有的一切。
或者說:我把我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
我帶上我所擁有的每樣東西。那其實不是我自己的。它們原先要不是別有他用,不然就是別人的。豬皮皮箱原先是留聲機的箱子。風衣是父親的。那件領口有絲絨鑲邊的時髦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我叔叔艾德溫的。皮綁腿是鄰居的,卡爾普先生的。綠色的毛手套是菲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絲圍巾和盥洗包是我自己的,上個聖誕節的禮物。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一月,仗還在打。我卻得在隆冬中到俄國人那邊去,誰知道在哪裡,驚慌之中,每個人都想送我點什麼,或許還能派得上用場的,儘管什麼都幫不上忙。因為這世上根本沒啥幫得了啥忙。因為我被俄國人列入名單,更改不得,所以人人各懷心思,都送了我一點東西。我收下了,而且十七歲的我認為,這趟遠行還來得真是時候。也不一定非得是俄國人的名單不可,只要情況不會太糟,對我來說甚至是好事。我只想逃離這個像頂針一樣令人窒息的小城,這裡連石頭都長了眼睛。與其說是害怕,我反而有些迫不及待。不過又有點良心不安,我居然頗能接受那份令親戚絕望的名單。他們擔心我到了外地會遭遇不測。可是我只想去一個沒人認得我的地方。
我已經遭遇不測了。禁忌的不測。它畸怪,骯髒,無恥而美麗。事情發生在艾爾連公園的深處,短草丘的後方。回家的路上,我走到公園中央那個圓形涼亭,假日會有樂隊在此演奏。我在那裡坐了一會兒,陽光刺穿精雕細琢的木工。我看到中空的圓形、方形和菱形,白色的藤枝蔓爪串連其間。那是我迷亂的圖案,我母親臉上驚恐的圖案。我在這個亭子中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
但我越是自禁,就折回去得越快──兩天之後。去約會,公園裡這麼說。
我去跟第一個男人約第二次會。他叫燕子。第二個是個新來的,叫冷杉。第三個叫耳朵。之後來了絲線。再來是黃鶯和帽子。後來是兔子、貓、海鷗。接著是珍珠。只有我們知道誰叫什麼名字。公園裡狂野換伴,我讓自己人手相傳。那是夏天,樺樹皮白,接骨木莓和茉莉叢中長著密不透風的綠色葉牆。
愛情有它自己的四季。秋天給公園劃下了句點。樹木光禿禿的。約會帶著我們轉進了海神浴池。大鐵門的旁邊掛著橢圓形的天鵝池徽。每個星期,我都和那個年紀大我一倍的人見面。他是羅馬尼亞人。已婚。我不說他叫什麼,也不說我叫什麼。我們錯開時間入場,鑲嵌玻璃票廂裡的售票小姐、光可鑑人的石板地、圓形中柱、睡蓮圖案的瓷牆、雕花木梯都不該意識到我們約好了。我們先去池子裡和其他人一起游泳。到了蒸汽室才碰頭。
那時候,去勞役營的前夕,而且在我返鄉之後直到一九六八年去國為止,情況也一樣,每次約會都可能換來一次牢獄之災。如果被逮到了,至少五年。有些人就被抓了。他們直接從公園或公共浴池被抓去嚴刑審訊,丟進大牢。從那裡再被送到運河邊上的訓戒營。今天我知道,沒有人從運河那邊活著走出來。就算走得出來,也成了一具遊屍。老朽而殘敗,對世上的愛情而言,再也不堪使用。
至於勞役營時期──要是在營裡被活逮了,我必死無疑。
五年的勞役生涯之後,我日復一日在街頭的騷亂中遊蕩,腦中一再演練萬一被捕時的最佳形容:當場活逮──針對這項指控,我想出了千百種託辭和不在場證明。我背負著沈默的重擔。我把自己包在沈默之中太深太久了,再也不能用言語打開來。即便說話時,我也只不過是換種方式把自己包起來。
最後那個約會的夏季,為了延長從艾爾連公園走回家的路程,我偶然走進了大圓環那裡的聖三一教堂。這個偶然命中注定。我看到了即將來臨的時光。側壇旁邊的柱子上,立著一個身穿灰色大衣的聖人,頸背上圈了一隻羔羊充當大衣豎領。這隻頸背上的羔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你就是不能說。當我說頸背上的緘默和口中的緘默有所不同時,我知道我在講什麼。在我的勞役歲月之前、之中、之後,整整二十五年,我活在恐懼之中,怕國家又怕家人。我害怕這雙重的崩毀,國家把我當成罪犯關起來,家人把我當成恥辱摒棄在外。在街頭的騷亂中,我往櫥窗、車窗、門窗、噴泉和水窪的鏡面裡瞧,滿腹狐疑,我到底是不是透明的。
我父親是畫圖老師。而我滿腦子的海神浴池,一聽到他提起水彩這個詞,整個人像被踢到似地抽了一下。我去了多遠,這個詞都知道。我母親在餐桌上說:不要用叉子叉馬鈴薯,會碎掉,用湯匙,叉子是用來叉肉的。我的太陽穴砰砰跳。她幹嘛講肉啊,明明在說馬鈴薯跟叉子。她講什麼肉啊。我的肉已經被約會攪得神魂顛倒。我是我自己的賊,字詞突如其來就把我逮個正著。
我母親,特別是我父親,就像小城裡所有的德國人一樣,相信金髮辮子和白長襪才叫美。他們相信希特勒的小四角鬍,相信我們七城薩克森人 是亞利安人。我的秘密,純就身體而言,已經無恥之極。又跟一個羅馬尼亞人,再罪加種族恥辱。
我只想離家出走,就算去勞役營也無妨。只是我替母親難過,她不知道她多不了解我。一旦我走了,她會經常想我多過我想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