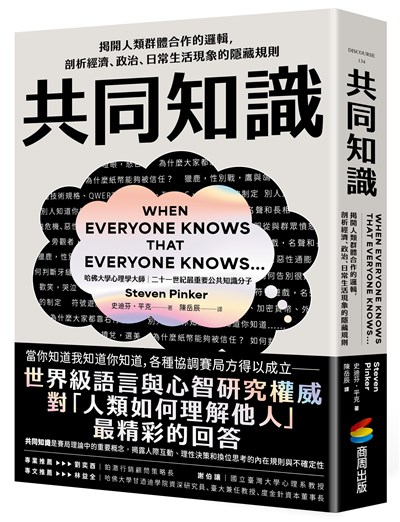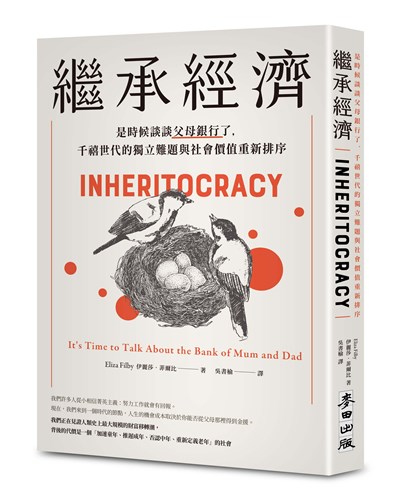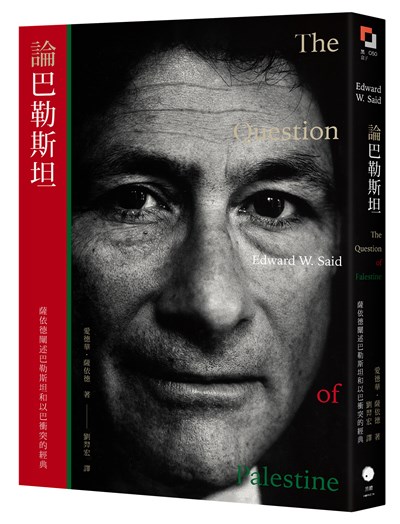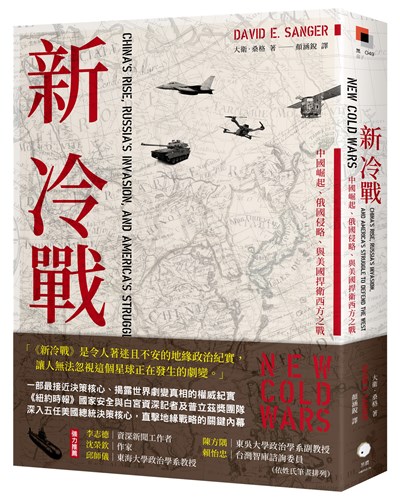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夜裡,罹患癲癇的苗族難民女兒李黎亞被母親抱在懷中,來到加州美熹德郡的醫療中心求診。不通苗語的急診醫生將黎亞誤診為「初期支氣管肺炎」,開立抗生素後便請黎亞父母離去。接續這場烏龍而來的,是一連串的醫病衝突與文化誤解。
作者安.法第曼為了解這樁奇異的醫病衝突始末,實地走訪醫院與社福機構,更深入苗族社群,她在本書中不斷探究,如果病人理解身體乃至世界的角度與西方的科學觀點截然不同,醫生該如何調整療法與溝通策略?出身不同文化背景的雙方,究竟有無可能找到共同的語言?
內容節錄
《惡靈抓住你,你就倒下:一場改變醫療現場的跨文化醫病衝突》
我在書桌底下收藏了一大箱錄音帶。雖然內容都已經轉錄為文字,我還是樂於不時拿出來聽聽。
有些錄音平靜、容易聽懂,內容都是美籍醫生的談話,以及不時插入的咖啡杯碰撞聲或傳呼機嗶嗶聲。剩下的錄音帶有半數以上都非常嘈雜,錄的都是在李家的聲音,李家是苗族難民,一九八○年由寮國移民到美國。在嬰兒的哭聲、孩童的嬉戲聲、關門聲、碗盤碰撞聲、電視聲、空調有氣無力的轟轟聲等背景噪音間,我聽到了母親的聲音,不時夾帶著喘息聲、鼻息及吸唾聲,或在苗語的八個音調間上揚或下滑時發出類似蜂嗚的嗡嗡聲。父親的聲音則更宏亮、更慢,情緒也更激烈。我的口譯員在苗語及英語間切換,音量較低,語氣恭謹。這些嘈雜聲喚醒了一波波感官記憶,包括紅色金屬摺疊椅的冰冷感,這張椅子是客人專用的,我一踏入李家公寓,就擺好等著我入座;還有避邪物投出的影子,那塊物件用麻繩綁著,由天花板垂下,在微風中搖擺;以及苗族菜肴的味道,從最美味的「瓜泥刷」(quav ntsuas,類似甘蔗,帶有甜味的植物莖部),到最恐怖的「泥殺調」(ntshav ciaj,生的豬血凍)。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我第一次坐上這張紅色摺疊椅。同年春季稍早時,我來到李家人所居住的加州美熹德郡(Merced),因為我聽說這裡的州立醫院中,苗族病人與醫療人員之間有些不尋常的誤會。有個醫生稱這些誤會為「碰撞」,聽起來就像兩組不同的人馬砰地迎面猛撞上對方,還伴隨著刺耳煞車聲與玻璃破碎聲。然而,衝突的過程卻常是一團混亂,很少正面相對。雙方都受到傷害,卻沒有一方知道碰撞是由什麼造成,也不知該如何避免下一次撞擊。
我一直認為,最值得觀察的活動並非發生在中心,而是在交界的邊緣。我喜歡海岸線、鋒面以及國界,因為在這些地方總能看到耐人尋味的摩擦與矛盾。比起站在任何一方的中心,處在交界點上更能看清楚雙方。尤其當你站在兩種文化中間,更是如此。當我初次來到美熹德時,我對美國的醫療文化只有淺薄的認識,對苗族文化則是一無所知,我想,若自己能站在兩方之間且設法不捲入紛爭,或許便能讓兩者照亮對方。
九年前,這一切都只是紙上談兵。在我聽聞李氏夫婦之女黎亞的病例在美熹德醫院引發該院有史以來最嚴重的衝突,在我認識她的家庭和醫師之後,我發現我對雙方同樣喜愛,也發現很難將衝突歸咎於哪一方(天知道我還真的試過),於是我不再用單一面向的觀點來分析情況。換句話說,我的思考方式在不知不覺間開始不再那麼像美國人,稍微像苗族人。湊巧的是,在寫作本書的幾年中,我的丈夫、父親、女兒和我自己也都經歷了大病。一如李家,我也在醫院待上很長時間。在候診室的漫長等待中,我常常苦思,怎樣才算是好醫生?我的兩個孩子在這九年間相繼出生,我發現我也常常問自己一個和李家故事密切相關的問題:怎樣才算是好父母?
我成年後的大多數人生都已認識書中人物。我相信,若我和黎亞的醫師素不相識,我不會是現在這樣的病人。我也相信,如果我不曾認識黎亞一家人,我將不會是現在這樣的母親。當我從書桌下拿出錄音帶,隨意播放其中片段時,便陷入回憶的洶湧波濤中,同時,我也想起至今我仍能從書中這兩種文化中學到東西。有時我在夜闌人靜時播放錄音帶,我會想像,如果將兩種錄音黏接起來,就能在一捲錄音帶中聽見苗族人與美籍醫生的談話,雙方將說著共同的語言,而那聽起來,會是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