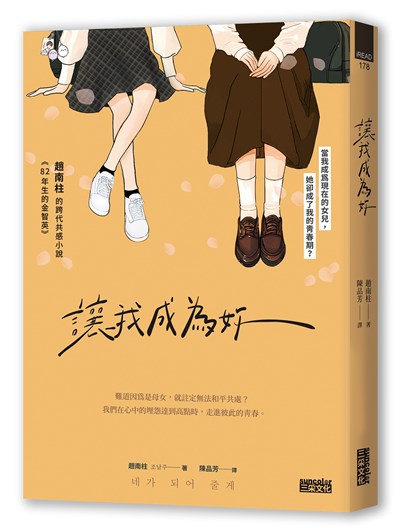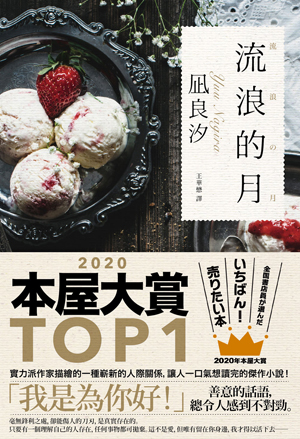
《流浪的月》為日本作家凪良汐跨界大眾文學創作作品,奪下本屋大賞受到書店人員好評。故事從主角更紗原本生長在自由快樂的家庭,父親逝世後母親也接著將她拋下,更紗不得已被阿姨收養後,卻逃離阿姨家意外變成綁架事件受害人。後來被定罪為加害人的男大學生文,命中註定不該重逢的兩個人卻重逢了,相互抱著深刻傷痕長大成人的兩人,傷痕只有他們相互理解與扶持,突破周圍的重重考驗,開始了疾走人生。
文章節錄
《流浪的月》
讀《流浪之月》/作家陳栢青
《流浪之月》很好看,在於小說家寫了一個愛情故事,該是一個甜美的吻,卻挾打巴掌的力道,狠狠甩在這個率以溫柔為要脅的世界臉上。
故事分明社會版頭條,主人翁前半生可以濃縮成一個標題「小女孩遭戀童癖誘拐,白璧染瑕。」。下半生則是「他已經壞掉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受害者愛上當年綁匪。」。小說家厲害就厲害在這裡,看上去是加重鹹,很辛辣,但寫起來卻雲淡風輕,淡淡然,愛的不黏不膩,醬油拉麵吃起來是柚子鹽口感。一切不是你想的這樣。
也因為《流浪之月》,我忽然明白日本的愛情故事為什麼那麼好看?因為我們都以為愛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但說到底,我們的愛情經常是,一個人對一群人。談個戀愛就是跟家庭、跟整個社會和傳統一鍋談--尤其是在日本,作為一個活在「我們」之中,群體意識極重,強烈感受到人們眼光的封閉部落般社會裡--沒有什麼是兩袖清風,愛都在拖泥帶水,《流浪之月》是開給你整輛水泥車了,以前羅曼史愛情故事愛寫跨越階級性別家族恩怨,《流浪之月》跨越的極致是,罪。是社會強加給你的身分:
你不只是女人。你還是受害者。你是被用壞掉的人。你在報紙頭條上是被誘拐者,可你偏偏愛上對方。
他不只是男人。他是加害者。他是害你壞掉的人。他長期帶著電子鐐銬過生活。他的身分履歷裡永遠註記這個身分。他也許不可能愛你。
小女孩遇上成年男子。未成年偏碰上蘿莉控。他們不告而別,他們遠走高飛。他們住在一起。沒人知道這中間真的發生什麼,但人們覺得已經知道了。這女孩一生都背負這件事情,當她長大了,人們看她的眼神總帶她回到當年被帶走那一刻,「我說的話就沒有人聽進去。透過『體恤』這層多餘的濾網,我只是笑,就變成『妳是不是在勉強自己』」,人們不希望女孩擁有她自己,人們希望她成為一個故事,而且是一個受害者的故事,是髒掉的故事。好讓人們說一聲加油,說辛苦了。好讓人們覺得自己很溫柔,所以《流浪之月》好看,好看在這本書豈止是愛情故事,有時是恐怖故事。恐怖不是在「發生什麼」,恐怖是在是書反應了「你以為發生什麼」,恐怖的是「你以為發生什麼」所以要對方「加油」、「辛苦了」,最溫柔,才最恐怖。這種溫柔還不能反抗。善意會吃人。這是雙倍恐怖。這該死的溫柔和善良。
《流浪之月》耐看,在於小說的深邃。看起來是愛情,但小說家探討的,首先是群體和個體。是「自由」。什麼是自由人?面對一種美名為溫柔的暴力,一個強加故事設定給你的社會,「個體」的極致是什麼?
但《流浪之月》始終是一個愛情故事。小說也安排對照組,女孩長大了苦苦追著當年男子,跟監他,甚至住到他家旁邊。而這女孩身邊,又跟了一個家暴男,作為女孩的前男友,女孩跟蹤男子,家暴男就跟蹤女孩,得不到,就毀了女孩。所以女孩和家暴男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只是因為敘述角度的不同嗎?只是因為女孩是主角,她的愛就比較神聖?其他人就是癡漢?
就是這樣兩兩比較,愛無分輕重,但有了清濁。你會發現,都稱之為愛,家暴男之愛是「得不到就毀了你」,其實是把愛變成拘束,愛你入骨其實是拖你一起死。蘿莉控男子看似誘拐拘禁了女孩,但對女孩來說,「和他在一起,很自在」,原來真正的愛反而讓人自由,讓我飛。
於是,《流浪之月》看起來是愛情故事,但他要說的其實是「自由」、「發現自己」,而當你以為他要尋找的是自由,是自己。你會發現,愛情出現了。
相信我,只有你能對你自己說,辛苦了,和加油。但你永遠不會這麼說,畢竟,是你真正想要的,就永遠不會喊苦不打算退。像是這本書。像這樣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