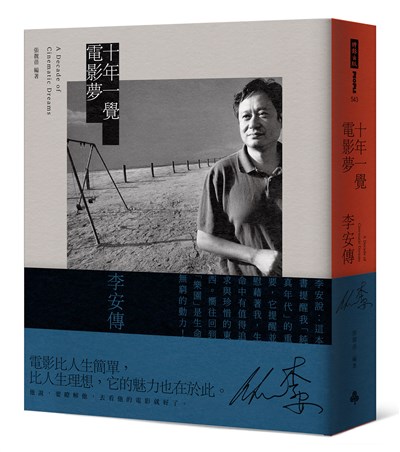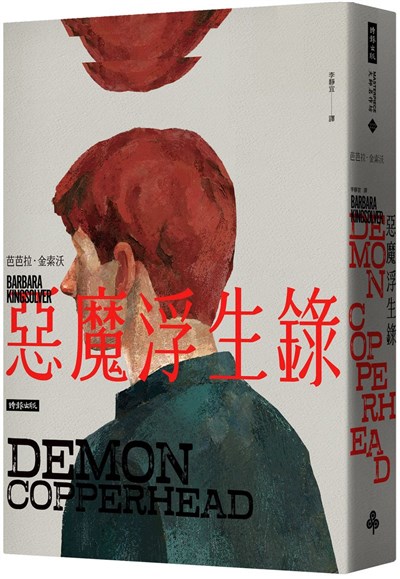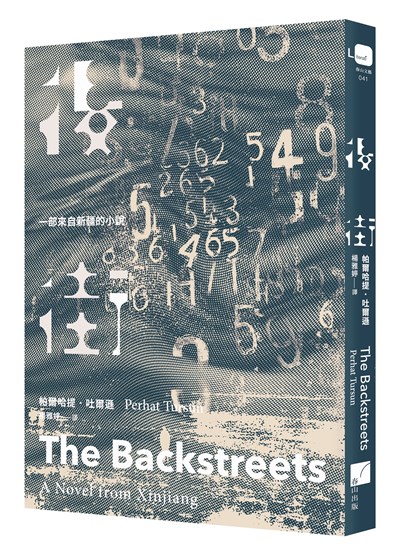
「在這座陌生城市裡,我不認識任何人,所以不可能與任何人為友或為敵。」這是小說當中不斷重複出現的句子,反映了主人公與城市疏離的關係,同時也像是一種宣告。
小說場景在烏魯木齊、北京、童年的農村間不斷切換,沒有一處是主人公的安身之所,到哪裡都格格不入,他就像城市中到處被驅趕的鼠輩──「牠們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進食、睡覺和生育,似乎也跟城裡人的生活差不多。那些我們甚至不願想像且令人作嘔的生物,正偷偷享受進食、睡覺和生育──犯下活著的神聖罪行。」
內容節錄
《後街:一部來自新疆的小說》
當我走在烏魯木齊的街道上,一切似乎都漂浮在濃霧中。感覺好像只有我自己的身體是有重量的東西。它不是從一處移動到另一處,而是陷入某處。汽車的聲音穿透我沉重的身軀,使我心煩意亂,走路時身體愈壓愈低。
一個額頭寬得離譜、下巴又極小的男人忽然從霧看起來更濃的地方冒出。那片濃霧彷彿混雜了其他無法清楚分辨的煙氣。
劈死六城的人,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劈……
他重複著「劈、劈」這個字,沒有添加任何變化,同時走了約一公里的距離。若有人在男子每次吐出「劈」字時看他的臉,會發現在其想像中,他正在砍人。每當他講這個字,旁觀者都會看見男子舉起又砸下的菜刀或斧頭閃現血光。他每次迸出此字,都極用力地發那閉唇的子音「p」,以致他憤然閉緊雙唇後,整顆頭都在顫抖。他每次說「劈」,腦中便有個男人的頭顱被砍下,滾落在地,鮮血淋漓。即便我非常仔細地觀察他,仍無法確定他究竟在跟誰說話。乍看之下他似乎自言自語,再瞄一眼他又像是對走在身旁的女子說話。我無法確定那黑衣女子是否與他同行。她離他時近時遠,因此我不知他是跟她一起走,抑或獨行。
他所說的那些城市至少有四百五十萬維吾爾居民。要將這四百五十萬人一一歸類為朋友或敵人,不僅他一輩子做不完,就算加上他孫子的壽命也不夠。因此,與其將時間浪費在區辨敵友上,他似乎甘願與六城的全體居民為敵。儘管如此,也要那六城的人來到他面前,排隊等他的大菜刀落到頭上,才有可能將他們全部消滅!
如果他太過衝動,沒把菜刀砍在頸部的正確位置,他們可能不會被殺死。因此他必須準確測量,確保菜刀不會卡在頸骨中。他還得計算將菜刀從每個人的脖子拔出需花費的額外時間。就四百五十萬人而言,這可能長達七萬五千小時。即使每天努力,也得花上一輩子才殺得了那麼多人。為了維護身體,他需要一日三餐,每隔一段時間讓疲累不堪的雙手休息一下。假如他因睡眠不足而縮短壽命,這六城的人要留給誰劈呢?排除這些時段後,我們可以假設菜刀實際斬首的時間為每日八小時。所以他需要九千三百七十五天。若換算成年,將是二十五年八個月又四天。但我可以想見,這個已陷入如此公然暴怒的男人,恐怕無法再活二十五年八個月又四天。從他臉上不難看出憤怒正在消磨他的靈魂。它看起來就像被風吹襲的茅草屋頂,或許也像在被蟲啃蝕。
此外,居民的平均年齡逐漸下降。我小時候,百歲以上的男女隨處可見,而今整座村莊找不到一個。有些人認為這是用化學肥料耕作的結果。我想居民的壽命縮短應歸因於心理壓力,尤其是殺戮欲望被現代文明壓抑而引發的偏執與歇斯底里的不滿。對城市的敵意也可能由此造成。
我之前從未見過他,這個額頭愈腫愈寬、下巴不斷後縮的男人。這會兒他消失在濃霧中。也許我過一陣子就會忘記見過他。即使下次遇到,我也不確定是否會認出他。也許我這輩子不會再有機會遇見他。但我始終-已經是他要劈的人,儘管我們互不相識。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