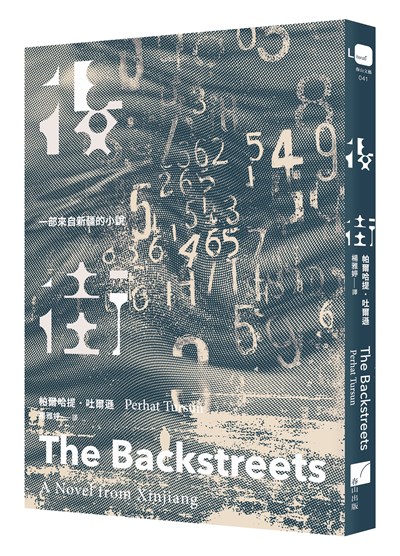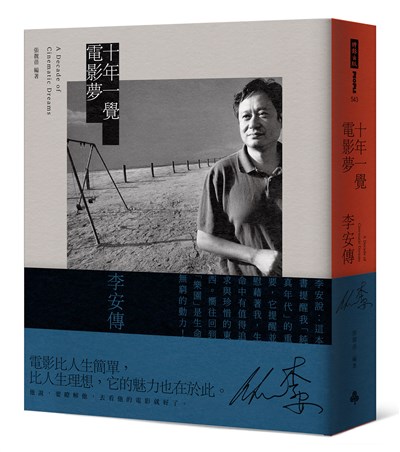他曾經是家喻戶曉的歌手,萬人空巷的歌星。如今,儘管那些往日的輝煌,逐漸成為台灣民歌史上的悠遠回音,但他留下的歌依舊膾炙人口。《最最遙遠的路程》是台灣民歌之父胡德夫最新的創作,這一次他用文字替代歌聲,向讀者分享他七十年來的創作歷程與生命經驗。
文章節錄
《最最遙遠的路程》
總裁獅子心
在我年輕的時候,曾與幾位朋友一起開了台灣第一家鐵板燒餐廳,起名洛詩地。由於我在那裡擔任店長,所以在不去哥倫比亞咖啡館唱歌的時候,我經常要守在那裡看店。每天關店以後,李雙澤、楊弦等幾位朋友經常來這裡找我,所以洛詩地也是我們幾個年輕人的聚點。就像在哥倫比亞咖啡館一樣,我在洛詩地也結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Stanley的年輕人。
Stanley有時候他會和女士一起來吃飯,有時也會自己一個人過來喝酒。我們兩個人很喜歡和對方聊天,時間一長也就慢慢熟悉了起來。只要他來店裡,我們經常聊到很晚,他總是我店裡最後一個離開的客人。那時我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叫嚴長壽,雖是美國運通公司的職員,但是職位很低,只是扮演著傳達小弟的角色。
所謂傳達小弟,每天要做的工作就是在公司裡事先準備一些資料,等到大家來上班的時候把這些資料分發到每個人的桌上,然後做一些檔方面的收發、拷貝等工作。到了晚上,公司還要賦予他另一項任務,如果來公司拜訪的客戶太多而沒有人手接待時,他就要在晚上帶著這些客戶外出消費,當作公司方面的招待。可見這並不是一個多麼高級的職位。
在與Stanley成為朋友以後,僅僅在我的店裡聊天已經不能滿足我們當初年輕而躁動的心,我當時已經因為歌唱而有了些名氣,跟台北幾家可以唱歌的地方比較熟,所以我就帶著嚴長壽去遍了當時台北可以喝酒唱歌的店。雖然現在的嚴長壽已經在生活習慣方面已經很自律了,但在年輕時候,我們也曾瘋狂地徹夜喝酒,他也會到我的演唱會上看我的演出。雖然是由客人變成朋友,但我和Stanley的友情卻不比我之前所認識的任何一個朋友差。
從七○年代中期開始,我逐步轉向原住民的各種權利運動,奔波於需要為同胞?喊發聲的地方。當時的台灣還沒有解嚴,我的行為顯然不會到當局的歡迎,他們甚至把我拉進了黑名單,不再允許我唱歌,就連我身邊的朋友也會受到無關的牽連。一九八四年年底,我頂著壓力正式成立了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在做這件事之前,我已經知道自己的處境將會如何,為了不給身邊的朋友帶來麻煩,我只好向朋友們一一告別,選擇不再聯絡。
一九九九年,台灣發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在地震之後,我組建了部落工作隊進入再去為那裡的同胞提供服務。那時我剛剛與我現在的太太姆娃相識,她提議我們到她的同學家去做客,正好緩解一下我精神的緊張與身體的疲勞。
在那位同學的家裡,我無意間發現了一本書,名字叫做《總裁獅子心》。只看書名就知道這是一本商業類的圖書,本來不是我所關注的領域,但這本書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卻是它的作者——嚴長壽。這是我所認識的那個Stanley嗎?還只是作者與他重名而已?
我翻開那本《總裁獅子心》讀了起來,讓我感到驚喜的是,這本書的作者真的就是我認識的Stanley,沒想到十幾年過去,他已經做了亞都麗致大飯店的總裁。草草看過那本書,我才知道Stanley從一個美國運通公司傳達小弟一路走來的經過。
真的是Stanley,真的是我的老朋友。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拿著那本書對我太太的同學說:「麻煩借你家電話用一下,我想打給寫書的這個人。」
那位同學聽完直接笑了出來:「開什麼玩笑?你怎麼可能認識他啊?」
雖然同學這樣說,但我還是拿起電話打給了亞都麗致大飯店,並說請接總裁,不久我便聽到了電話中Stanley的聲音。
「Stanley!」
「Kimbo!」沒想到那麼久不見,他聽依然聲音他就知道是我,「你躲到哪裡去了?朋友們都很擔心你。每次我聽到我一樓的pasley西餐廳有人在彈鋼琴就會想到你,你現在在哪裡?」我們以前是那麼的要好,現在心裡面依然會有彼此。
「我在南投山上的災區剛剛做完部落工作隊的事情,準備回去了。」
「你可不可以來台北?我們現在很多朋友經常聚在我樓下的pasley,蔣勳,林懷民,還有我太太育虹、羅門、羅門的太太蓉子這些人,我們聚在一起時都會講到你,都很想再聽到你唱歌。」雖然Stanley在商界做得很出色,同時也擔任著台灣觀光協會會長,但他一直非常喜歡藝文活動,平時與藝文界的朋友來往很多,他的太太陳育虹就是一位詩人。他要我一定去找他,至少也要請我吃頓飯,聊聊天。
當時我和太太姆娃還在台中,我跟她說要去台北找嚴長壽。她問我:「真的嗎?本來我是不相信你們認識的,既然你要去,能不能把書帶上請他簽個名?」我那時候的頭髮短短的像刺?一樣沒有整理,因為身上沒錢,只能穿著短褲和拖鞋去台北。在台北,從來不會有人穿著這樣的衣服進入亞都麗致大飯店,都要西裝革履才行。即使後來流行了便裝,也至少要穿著整齊才可以。沒辦法,當初我只能穿成那樣去見他。現在想起來,真是沒皮,沒模沒樣。
當我到達亞都麗致大飯店的時候,Stanley已經在門口等我了,見到我以後他上來就是熱情的擁抱。我對他說自己穿成這樣就不要進去了,但他偏要我進去,而且已經安排好飯了。那天他請了我們很多的老朋友過來和我見面,並把我們這些人安排在飯店裡的法國廳一起吃飯。吃飯的時候,他請我上台唱歌,林懷民等一些朋友都高興地坐在台下,那一瞬間,我好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自己二十幾歲的時候。
聚會以後,我向Stanley告辭。他說下下週要去日本,也邀請我一起去。但我心裡非常矛盾,沒有答應同行,最後他對我說:「Kimbo,我希望你能到我的飯店一樓繼續唱歌,如果你開心的話,一週來一次、兩次都可以,你就把這裡當作你的客廳,很多朋友都會來看望你。」聽到他這樣說,我的心裡有些動搖了。
雖然願意重新開始唱歌,但我在台北卻居無定所,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流浪者和一顆炸彈。剛好我有一位老朋友住在離亞都麗致大飯店不遠處的德惠街附近,雖然他的房子不大,但可以勻出一個小房間鋪上榻榻米讓我住上一段時間。我沒有像樣的衣服,僅有的三套衣服都是短褲一樣的打扮,於是我又找到另一位我十五歲就喊他為大哥、對我厚恩有加的趙爾文先生,請他幫我到迪化街做了一套西裝,這樣我的心裡才踏實了一些。困難的時候總會有朋友幫助我,不得不說這是一種人生當中莫大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