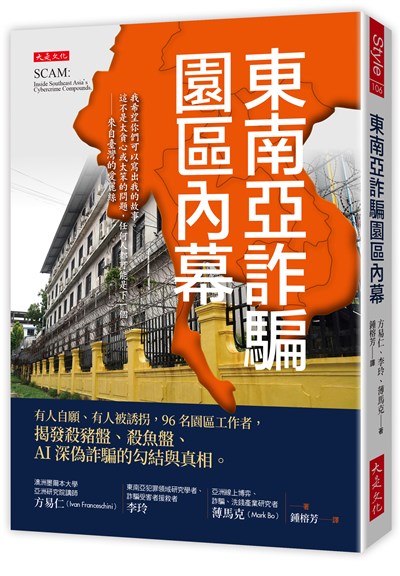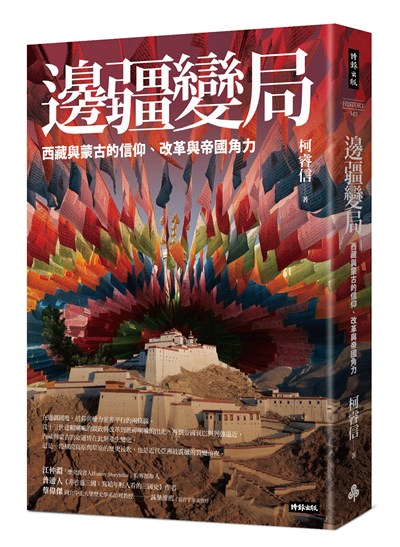這是一部輝煌、不朽、極具特色的作品,也是台灣罕見出版的整體分析和描述30年越戰的非虛構鉅著。英國著名記者、軍事歷史學家馬克斯‧黑斯廷斯於2018年寫成的一部以越南戰爭為題材的長篇歷史鉅著,記述自1945年二戰結束法軍重返印度支那至1975年西貢淪陷、美軍撤離,南北越歸於共產黨統治,兩次印度支那戰爭的宏大歷史。
本書不單是描述單一戰爭,而是關注整個越戰;除了關注越戰,對於越戰背後的越南、亞洲乃至於世界大局都有著墨。提供讀者完整理解越戰的視角,並反思其帶來的災難和影響。
文章節錄
《越南啟示錄1945-1975》
戰爭的結束為越南領導人帶來一個不快的驚訝:二十多年來一直盯著越南的東、西雙方的超級強國,已經不再重視越南事務。中國對越南越來越反感,到七十年代末期,北京官員辱罵一名河內政治局委員是「乞丐」,因為他總是跑來要援助。一九七九年,中國與越南爆發一場簡短但血腥的邊界戰爭。俄國的援助也大幅縮水,之後蘇聯垮台,所有俄援完全終止。到一九八○年,天然資源豐富的越南已經成為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之後十年,越南人民吃盡千辛萬苦,但那些老邁的領導人仍然不願放棄集體農耕,不願與非共產世界打交道,因為他們害怕這樣做會使越南純淨的意識形態遭到汙染。直到一九八六年第六屆黨代表大會召開,河內政治局才勉強修改一些政策,准許遠比北越人更有商業頭腦的南越人經商。
越南北部大部地區在一九八八年爆發大饑荒,九百多萬民眾受難,死者不計其數。但河內那些意識形態頑固派,加上一些軍人,特別是那些位高權重的情報頭子,仍不願向經濟理性妥協。直到一九八九年九月,阮文靈(Nguyen Van Linh)還在黨的意識形態訓練所發表演說稱,「資本主義一定會為社會主義取代,因為這是不容否認的人類歷史法則。」黎德壽在一九九○年死前不久寫了一首詩,歌詠一去不復返的那段患難與共的歲月:
「我們曾經慷慨激昂/同生共死,吃一碗飯,穿一件衣/但如今人們只認金錢/談到情緒與感覺標準的個性/同志意識已經蕩然」
黎筍於一九八六年死亡,但黎德壽與他本人的接班人依然緊抓黨權,不肯放寬個人自由:馬列理論仍是每一所中學的教材。河內的老人領導班子只肯承認容許個人賺錢、製造財富的必要,也確實有些人因此成為巨富。至於鄰國與盟國,河內的大多數軍隊在一九八八年撤出寮國,並於翌年離開高棉。越南於一九九五年恢復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同年加入政治與貿易組織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十年後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TO)。河內的領導進程仍然籠罩在團團迷霧中,但滿腦子越南意識形態優異論的老人,與家族在黨內擁有龐大勢力的男女,顯然仍把持著政權,繼續封殺自由主義,國家的經濟收益造就了不少驚人的個人財富。
針對龐大而且仍然有增無減的流亡社群,為因應一場來勢洶洶的人道危機,美國國會一九七五年通過了印度支那移民與難民援助法(Indochina Migration and Refugee Assistance Act)。無論如何,周發(Chau Phat,譯音)說,「沒有一個人對這場戰爭的結果感到快樂,但對於被安上失敗者標籤的人而言,日子當然比所謂勝利者難過得多。」許多流亡海外重建新生的越南人,在最初幾年都過得非常艱苦:「他們多年來一直蒙在鼓裡,以為美國人到越南為的是幫助越南人。事實上,美國人到越南,為的只是將越南做為一個平台對抗國際共產主義罷了。」周發本人現在人稱法蘭克.喬(Frank Jao),已經是個成功的商人與慈善家。
前南越空軍軍官嚴正也在南加州展開新生,先做時薪二點五○美元的體力活,後來接受訓練成為電腦技師。他在抵達美國後不久,有一次碰到一名男子從卡車駕駛座探出頭來,對他大叫「滾回去!」嚴正說,「那很傷人,但之後我也遇到許多好人。」越南裔美國人在美國成功的例子多得驚人,嚴正是其中之一。唐.葛拉漢聘了三十名越南難民在他的家族報紙《華盛頓郵報》工作:「事實證明他們是我們報社最忠誠、最勤勞的員工。」曾是南越海軍最年輕艦長的阮季後來成為橘郡公民,他說,「今天的我以身為美國人為榮,我不想活在過去,我要為未來而活。唯一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共產黨在征服南越之後,沒能像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北方表現得那樣慷慨。」
——
名為《全面勝利》(Total Victory),共八冊的越南官方越戰戰史,在總結中提出傷亡數字:幾近兩百萬平民遇害、另兩百萬傷殘、還有兩百萬受到化學毒劑傷害。根據河內的估計,在戰場上死亡與失蹤的人數為一百四十萬、六十萬人受傷。其中有關平民的數字似有誇大之嫌,但有關軍人傷亡的統計似乎可信──沒有人能說得準。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在越南統治者眼中,南越軍老兵──特別是那些殘障老兵──都不算人。《全面勝利》戰史作者最後指出,「我們全黨、全軍與越南南北兩地人民,已經成功貫徹了胡叔叔在一九六九年『春節祝詞』裡提出的戰略構想:『用戰鬥迫使美國人回去,用戰鬥推翻傀儡政權。』我們的國家統一了……越南人民打贏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時間最長、也最血腥的一場新殖民主義者侵略戰爭。」羅伯‧麥納瑪拉曾經問武元甲,誰是這場戰爭中最優秀的將領,武元甲以無懈可擊的意識形態正確性答道:「人民。」
相形之下,在西貢淪陷十年後,隆納‧雷根說,「時機已至,我們應該認識到,我們打的其實是一場崇高的戰爭。」美國保守派作者麥克‧林德(Michael Lind)儘管承認這場戰爭是「一場慘敗……發動戰爭的手段不僅錯誤百出,還往往有不道德之嫌」。但他與一些保守派直到今天,仍然認為越戰不過是「一場成功的世界大戰中的一次挫敗而已……是美國為維護國家軍事與外交聲譽而不得不打的一場戰事」。
胡志明與他的信徒為了將法國殖民主義趕出印度支那,先為北越,之後又為越南全境人民帶來如此慘重的經濟與社會悲劇──這樣做值不值得,仍將是後人爭辯的議題。許多在一九七五年以前一直贊同共產黨的南越人,在見識到河內的意識形態手段之後改變了初衷。
美國的干預能帶來不同結果嗎?許多美國人,如法蘭克‧史考登、道格‧蘭賽、席德‧貝里等等,懷抱崇高服務理念前往越南。史考登猶記得老友約翰‧保羅‧范恩說過一句話:「約翰說,我們用一部比空氣重的機器幫越南人攀上高空,必須盡可能幫他們慢慢下來,而不是讓他們墜落。」史考登問他會有什麼不同。范恩答道,「如果慢慢下來,會有更多人生存。」兩人曾經駕一架小型LOH直升機,在一處夜間遭攻陷的地區保安軍前哨據點著陸。他們想辦法將一名重傷士兵塞進艙內,然後盡速飛往百里居。那傷兵的血浸濕了史考登的大腿,在半途中死去。當他們抵達百里居時,范恩站起身,用拳頭在樹肢玻璃機艙上猛敲,一邊不斷叫道,「只要再二十分鐘!只要再二十分鐘他就有救了!」史考登心想,「這個傷兵與約翰夙眛生平,但約翰這麼關心他,只因為他是我們這邊的人。」
這段故事很感人,但美國介入越南有一個基本上的嚴重缺失:美國之所以介入越南,主要為的不是越南人民的利益,而是政客們心目中的美國國內與外交政策需求,特別是圍堵中國的需求。一連幾任美國政府竟然決定升高越戰,讓後人頗感不解,因為主要決策人都發現他們仰仗的西貢政權不適任,不能為美國介入提供適當理由。聯合參謀首長曾在一九六五年警告麥納瑪拉,指南越「缺乏一個可用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央政府不穩定、領導層士氣低落、公務員素質很差……能不能主要以政治面的手段解決這些問題,對最終能不能弭平越共叛亂非常重要。」但美國領導人還是自己騙自己,認為只要運用壓倒性軍事力量就能解決這一切問題,就像認為可以用火焰噴射器燒毀一整個花壇一樣。
儘管有些將領表現確實很差,但由於這是美國核心越南政策的失敗,所以把敗戰罪責完全歸咎於將領似乎並不適當。威廉‧魏摩蘭在一九六四年欣然出掌美軍自韓戰休戰以來最重要的野戰指揮任務。四年後當他返美時,他已經成為一項國恥的替罪羔羊。大衛‧艾利約說得好,「打仗從來沒有什麼明智之道。」詹姆斯‧賈文(James Gavin)將軍與其他一些將領從一開始就提出警告:「如果一個村落你爭我奪、先後易主五、六次,許多平民會死亡,生活方式會整個改變……戰爭繼續這樣拖下去,我們本身就會毀了我們當初決定一戰的目標。」
甚至在考慮戰爭後果以前,美國決策人士也沒有察覺巨型外國駐軍對一個亞洲農民社會造成的經濟與文化衝擊。在美國國際開發署工作的越南籍秘書,薪資比南越軍上校還高。甚至早在開火以前,推土機與施工裝備、天線與裝甲車、瞭望塔樓、沙包與鐵刺網已經將環境搗得滿目瘡痍,直升機在天空飛來飛去,巨型大漢向嬌小的婦女買春。這不是只有越南才有的咀咒,而是西方國家每在遙遠異域用兵時,無論用兵意旨多麼良善,都會出現的現象。
共產黨享有重要的宣傳優勢,讓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幾乎看不見他們在幹什麼。他們在越南四處亂竄卻不留足跡。反觀美國人卻像科幻電影中那些巨型怪獸一樣,拖著笨重的步伐在這片土地上踟躕而行,搗毀途經一切,以及越南社會的寧靜。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西方將領們仍然不了解派遣戴著墨鏡、頭盔與防彈背心的士兵,發動這種「人民的戰爭」有多愚蠢,就像專門殺人、不懂愛、毫無人性的機器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