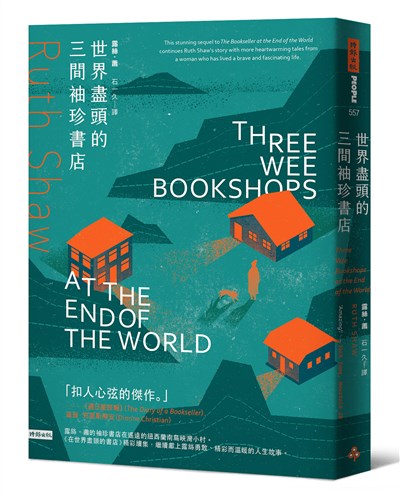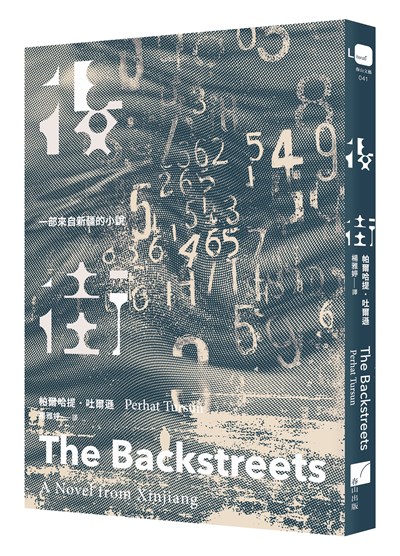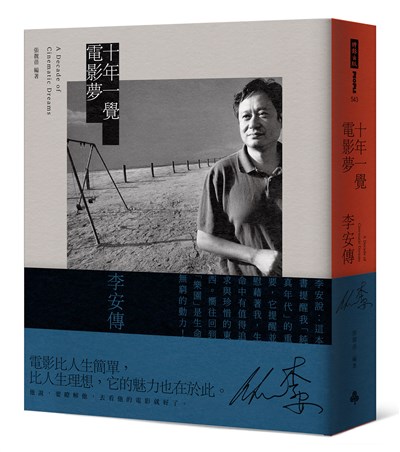十八歲,那個竹圍仔的少年離家遠行,告別了童年時代父母親守了半輩子的老家。少年還記得自己曾在葬禮上緊拽著父親的手臂,困惑地直視死亡。在本書中,作家透過同一雙少年的眼,深情回望那已自身後遠去的純真童年、求學的青春歲月與遠行返鄉的光景。
在那樣的年代,女孩們會去紡織廠上班,孩子們則光著腳在田埂間奔跑。少年的外婆總伸著一雙大腳丫踩在泥土上勞動;父親會徒手捉起水雞,交給母親煮湯;還有五伯母揉捏煨烤的「雞母狗仔」、六嬸熬的清糜、駛進村裡的爆米香攤販……離開故鄉再久,一幕幕零碎的記憶與氣味猶如生命的底色,總在不經意的時刻顯影,如風吹拂,溫暖而感傷。
內容節錄
《大風吹:台灣童年》
二月天,住家附近小公園裡櫻花盛開壓低了枝椏,花樹下,一名膚色黧黑年輕男人操持一具宛如大砲的器械,三兩名孩童隔幾步遠專注瞧著,要爆囉年輕男人出聲示警,孩童都用手遮耳朵,張大眼睛、咬緊牙關而有一張逗趣的臉。砰!地好大一聲,白煙噴發,米香瀰漫,空氣微微顫動,緋紅花瓣紛紛飄落,彷彿若有風。
大風吹。
吹什麼?
吹有記憶的人——
當我童少,每隔一段時間爆米香流動攤販便會駕柴油車駛進我們竹圍仔,一男一女大概是翁仔某搭檔,擇定姑婆家開闊稻埕女人擺開陣仗,男人在每一座大門前駐足,邊敲鑼邊喊叫爆米香、爆米香喔——我一聽,仰頭張望六嬸,眼神肯定流露了渴望,見六嬸點頭,我便自米缸中舀米,裝台糖鳳梨馬口鐵空罐裡,七分滿。
稻埕上陸陸續續已經集結了大人小孩,地上一罐罐白米排著隊,男人依序拿起,這是誰的他問,人群裡有人認領說我的我的,他便將米傾入砲管,片刻後大喝一聲要爆囉!年輕母親為襁褓中嬰幼掩緊耳朵,轟天巨響伴隨白煙大作,照例有誰家的囡仔還是被驚哭了,女人趨身向前拿一截米香哄哄他。米香、麥芽香,空氣甜甜的。
我提一塑料袋米香返家,六嬸問怎麼去了這麼久,我是著迷於那每一次巨響每一回雲繚霧繞。腹肚枵的時陣,六嬸說,才可以吃喔。
肚子餓的時候,還有麵茶,阿嬤還在時會自己用麵粉焙炒,加豬油、紅蔥頭;放學後,六嬸還沒下工,腹肚枵得咕嚕咕嚕叫,沖一碗麵茶止飢。
小時候我眼中的大人現在都已初老,年節聚在一起,同一團毛線織了又拆了又織地談的都是前塵往事,總有人提起,當我嬰幼時有人找我去拍奶粉廣告。後來呢?有人說:後來讓你老爸擋掉了。為什麼拒絕啊我看看六叔,六叔只是笑但不答話,六嬸開口把話題調轉了方向:以前真散赤,飲不起牛奶,這幾個囡仔攏是食麵茶、食米麩大漢的。
奶粉啊那是阿公阿嬤才喝得到的。遠地親戚前來探訪,總帶克寧奶粉、五爪蘋果當伴手禮,都讓阿嬤給收進五斗櫃裡;但是頻繁地,阿公自瀰漫金十字腸胃散氣味的裡屋拿出一罐奶粉幾顆蘋果問誰要呢。蘋果已經鬱出傷口,奶粉也早過了期,捨不得還是泡泡看,一杯子粉狀懸浮,味道也不對了。
自家灶腳產出的,除了麵茶還有鍋巴。幼時,家裡用的是灶、燒的是柴,看我們等在灶前,六嬸會讓飯多燜一會兒好使鼎底結一層鍋巴,剔起,輕輕握成一團,沾白糖吃,那美味!上台北後幾度和朋友在銀翼餐廳吃鍋巴蝦仁,醬汁淋下滋滋作響,色香味之外兼有音聲享受,但這已不是童年那款質樸滋味了;童年的滋味是最尖酸美食評論家也無能苛責的。
或是豬油粕。六嬸在菜市場買來的油脂蒼白滑膩,利刃切塊,入鼎煸炒,很快煸出一鼎豬油,油粕載浮載沉,撈起後瀝乾,我坐飯桌前專注挑著有肉販沒剔乾淨的瘦肉的油粕仔。油粕仔口感酥而有油香,六嬸拿它炒青菜。至於豬油,裝進鍋子冷卻後成乳白色。後來有了電鍋,鍋裡恆常有白飯,半夜裡腹肚枵就添一碗白飯舀一匙豬油,看著白色豬油緩緩融化把米飯浸潤得剔透晶瑩,一匙豬油可以扒下一碗飯。
池波正太郎也愛這樣吃。
池波正太郎是日本時代小說家也是美食家,他留下鄉間炒菜用的油脂,加入調味料後放一夜,凝凍,隔天置被爐裡片刻後再澆熱米飯上,池波說:美味極了!
我讀過一則報導,據「研究指出」,吃零食可以刺激大腦,產生心理上的慰藉感,成功轉移緊張焦慮的情緒。姑且不論所謂「研究」往往是企業主委託的研究,所謂「指出」則是公關公司的說辭,對我而言,米香、麵茶、鍋巴、豬油粕,乃至於熱白米飯上澆一小匙豬油,這些「零食」之所以好吃,原因再簡單不過,因為它們都是在「腹肚枵的時陣」吃的。
零食比正餐好吃,因為正餐是時候到了就要吃,而零食,是想吃的時候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