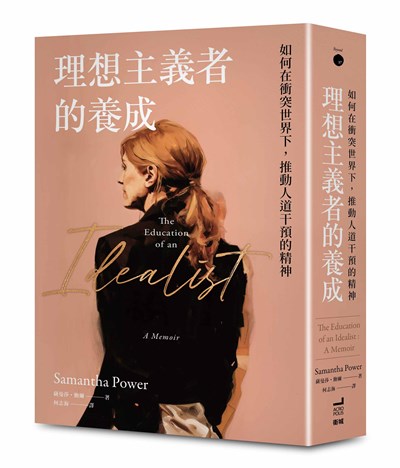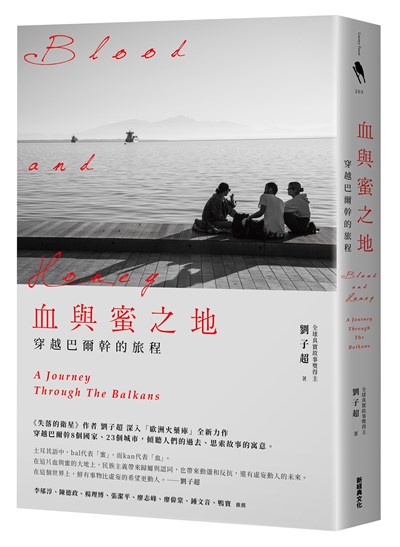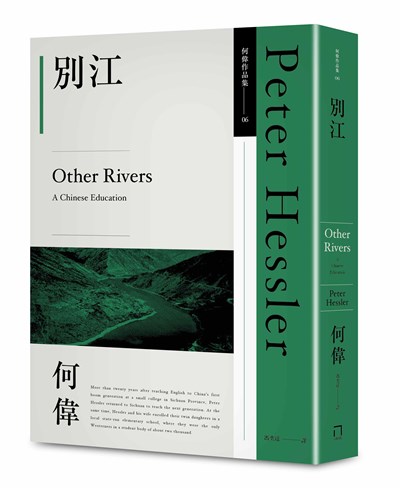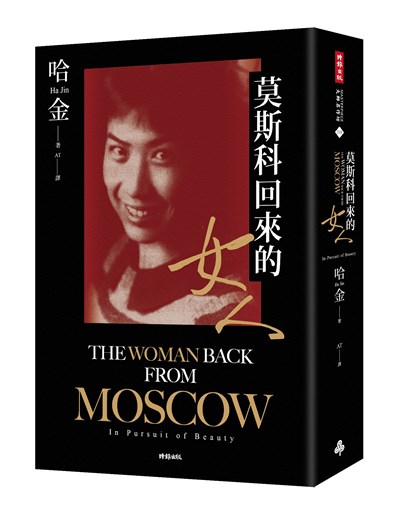「如同我愛著媽媽,媽媽也愛著我。她不過是途中走到岔路上,剛開始她也是打從心底愛著我的」無法自己決定命運的童年,在母親扭曲的愛下成行。放下母親的不愛後,才是全然自己可以努力的人生。主角「永遠」面對母親拋棄的事實後,開始她自己「真正的」人生。如何在艱難與崎嶇中重生?又如何從與世隔絕的「透明人」,緩緩進入社會?看不見的她,又要如何辨別這世界的紛擾與善惡?所謂「重新學習生活」,又是怎麼樣的樣態?「永遠」重生後的每一個挑戰,都讓人動容,也為之鼓舞。
文章節錄
《永遠的院子》
永遠是我的名字。
這是媽媽為我取的名字,很重要的名字。
有一天我問媽媽:「為什麼我叫永遠呢?」
那陣子我開始進入所謂的「為什麼期」,對於周遭的所有事物,不斷提出疑問,我想媽媽當時大概很頭疼吧。
可是她從來不曾流露出厭煩的語氣。
「因為你是媽媽『永遠的愛』,所以媽媽才給你取名叫『永遠』。」這是媽媽給我的答案。
「永遠的愛?」
「永遠就是沒有盡頭,一直持續下去的意思。寫成漢字是這樣寫。」
媽媽攤開我左手掌心,在掌心中央畫下複雜的線條。
「好癢喔――」
媽媽寫字時,我忍不住扭動身體,於是她又在我手上慢慢寫下「永」「遠」二字。我的左手掌心能隨時變身為迷你筆記本。
「可是這兩個漢字很難寫,所以媽媽選擇用相同意思的平假名『とわ(TOWA)』當你的名字。平假名是這樣寫。」
接下來媽媽又在我的掌心上寫下「と」「わ」。
「你也一起寫寫看吧!」
媽媽抓住我的右手,帶領我用食指寫下「と」「わ」,我又自己寫了一次。
「好棒喔!永遠真的好聰明喔!一次就記住自己名字怎麼寫了!」
聽到媽媽稱讚我,我高興到不知該如何是好。我於是進一步挑戰,希望聽到更多讚美。
「那媽媽的名字呢?我也想學媽媽的名字怎麼寫。」
「媽媽的名字是『愛』。」
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知道媽媽的名字。在此之前,我以為媽媽的名字就是「媽媽」。
「愛?」
「對啊,『永遠的愛』的愛。」
我聽了不禁抱住媽媽的脖子,開心得不得了。
「永遠的愛」就像一根施了魔法的線,把我和媽媽緊緊繫在一起。
「愛?」
「對啊!愛。」
「怎麼寫呢?」
媽媽這次在我左手上慢慢寫下自己的名字「あ」和「い」。
「い」我一下子就記起來了;「あ」轉來轉去的,有點複雜,我在腦中分析了一次,才寫在媽媽手掌心上。
「太棒了!永遠是天才!」
媽媽又讚美了我一次。
那陣子解決了一個為什麼,我的腦袋就會冒出下一個為什麼。於是我又開口問媽媽:「愛是什麼意思?」
媽媽想了一會兒才回答我:
「愛是想對人或物奉獻,可是不求回報;或是想把對方留在自己身邊等等傾慕、疼愛、珍惜的感情。國語字典是這樣解釋的。」
可是我聽不太懂這個解釋。
「那是好事嗎?」
媽媽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把我拉進懷裡,用力擁抱我。
她在我耳邊呢喃:「永遠跟媽媽是用『永遠的愛』繫在一起,所以什麼也不怕。就是這樣。」
「我愛媽媽。」
我也雙手用力環抱媽媽的背說:「永遠永遠愛媽媽。」
我想用用看剛剛學會的「永遠」二字。
「媽媽也永遠愛永遠喔!」
我和媽媽常常互相表達愛意。我們習慣用口頭確認對彼此的感情,這不是什麼丟臉的事情。
打從出生以來,我和媽媽總是形影不離,不曾分開。我們住在一棟兩層樓的小房子,二樓上方還有一個狹小的閣樓。寢室位於二樓,一樓廚房的下方是聊勝於無的地下室。房子前方是永遠的院子。
我的生活充滿媽媽的愛。每一頓飯都是媽媽親手烹飪,衣服則是媽媽用自己的舊衣服改的。裙子的口袋裡總有燙得平整的乾淨手帕。媽媽還在通往廁所的走廊天花板上懸掛毛線,好讓我知道怎麼走到廁所。
儘管我看不見,卻總能馬上知道媽媽在哪裡,因為媽媽有她專屬的氣味。我一直到很久以後才發現她身上的味道跟院子裡的某種植物相似――總之我能立刻就分辨得出媽媽的氣味。
歐德先生也有一點點氣味。每次媽媽打開他送來的箱子,總會散發出家裡原本沒有的氣味。
那個味道類似葉子的幽香,要全神貫注在鼻子上才聞得到。我長大之後聞到燃燒白鼠尾草葉子的氣味,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歐德先生。但是當時我年紀還小,沒有機會認識白鼠尾草這種植物。
不對,或許我曾經有機會認識。畢竟媽媽念了很多書給我聽,拓展我的世界。但是我不曾特別意識到白鼠尾草,所以無法用言語正確表達歐德先生的氣味。
白鼠尾草的氣味給人的印象絕非黯淡無光,而是近乎陽光的氣味。我覺得氣味也有專屬的色彩或光線,而我經常把氣味與顏色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