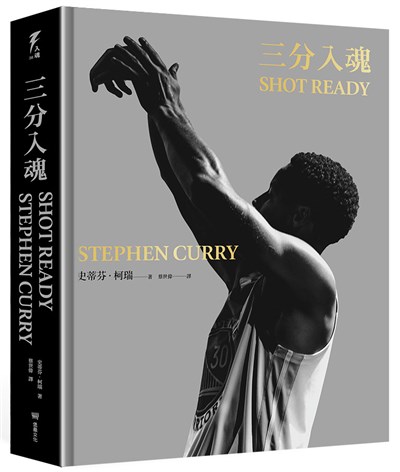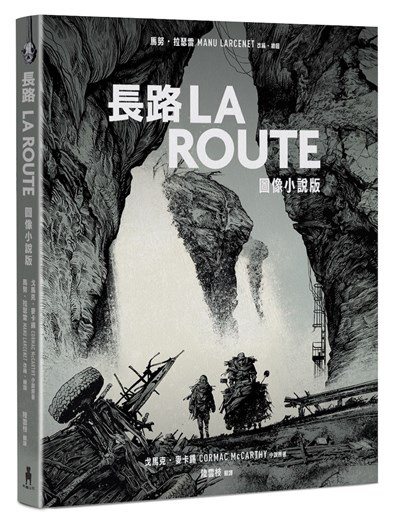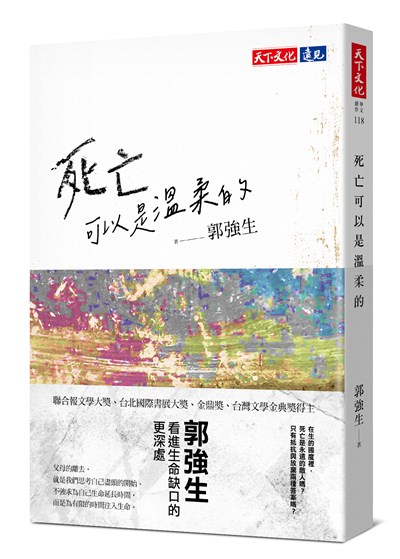穿踏死生欲念、空亡冥途的時光巨廈,小說家徘徊於虛實之間,迴旋繚繞。關於他的死亡早已被她心懷不軌地寫下了,時間過去,連書寫殺手都已遺忘,殊不知小說早被閻王挪作了生死簿。當死亡的碎片飛散,身心解離,她循著死的氣味、4的記號,尋索至愛之人每個烙印在記憶裡的身影,啟動未亡人的人間中陰之旅:施甘露、捨恩愛、掃落葉、覓滋味、想前塵、繞舊路、聽夏蟬。一個人,漫步街道,書寫開始。
內容節錄
《私輓歌》
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我非羅漢,一支筆墨擋不住愛河氾濫,愛苦大海即將狂襲的哀慟海嘯。
從此形單影隻,淋濕我眼睛的每一滴淚,冰涼如雪。理智上自是知曉所有的美好與明亮都不過如秋日草原的花,絢爛迷人但也極其短暫,難以持久。但生活習慣已長年被內化成另一組非我模式,十七年,內外身心如鬼針草,很細很小,沾黏很深。狼煙不再轉動,安靜下來細思才會感到已然被感情附身,少了萬事通先生,我感覺自己成了萬事癡小姐。往昔種種,日久積習,我已成為他的延伸。母親離開後,我靠著很多地理的覆轍緬懷親情。他離開後,我哪裡也不敢去,彷彿整座島嶼都是進不去的小鎮,都是雷區,覆蓋他的影子,影子拉長到世界盡頭,一路追迫著我,我要逃去哪裡呢?
冬天的街道和往年一樣,周邊的樹木光禿,街燈孤零地照著路口,在老牆上倒映出枯枝的物哀光影,塵埃在涼風中微微晃動,冷得使我哈了口氣。
夕霞陋巷燦麗得讓我誤以為天氣是暖的。
我在這個時刻想著和他竟一起走過這麼多年,一起跋涉的時光轉眼一瞬,經歷時代的各種印記。最後的印記是大疫,而大疫這些年的封鎖卻成了我們感情最好之際,彼此鎖在彼此的時光膠囊。
我早已搬離了靠海的母親病房居所,提筆者對時間的感慨多半來自於對空間遷徙的心境爬梳,地理移位,人事移往。
十七年,化為摩鐵床上的一顆顆紅色心跳。
他的心已不再跳,還在心跳的我,為不再心跳者繼續彈跳。無數個我,無數時刻,遭逢站在十字路口多年徬徨憂傷的我,等著我自己轉身狠狠去擁抱我自己。沿著呼吸的節律,我聽見自己的心跳和冬雨融合成一座森林。心靈暗語,密碼浮顯。他曾有天突然在等紅燈時轉頭對我說,我們下一輩子該如何指認彼此,遺忘彼此怎麼辦?啊,還有下輩子,彷彿聽見劫難似的心驚,又訝異他突然變得如此的詩意。我們的暗號?他一直想著我們之間只有彼此獨有的事情或笑話或有過的心有靈犀?而我想的卻是不想再來這娑婆世界。
來不及寫下遺願的人,我還來得及寫下,我該寫下什麼?不願再返人間,除非乘願再來,乘何願?千葉寶蓮花裡有祕辛?我想著讓自己止血的光明畫面,走著走著就來到了黃昏。小年夜的黃昏,市集街道滿是白日盛宴的殘痕,沿著路邊是尚未清走的腐爛葉菜瓜果與腥羶魚鱗內臟雜揉成新年獨有的又歡慶又孤寂的氣味。小時候總在圍爐除夕夜一個人走去市場找還在企圖將手上物品換成現金的母親,拉下鐵門的商店暗成一條黑色河流。我在市集路口一眼就見到疲憊的臉忽明忽滅,搖晃冷風的燈泡彷彿隨時會掉下來,我奔去母親身旁,一把抱住她。她卻把我推開,要我幫忙收拾東西。她一點也不要我的心疼,她也可能不懂什麼是心疼。她只是嘆著氣,我知道她嘆氣是因為生意壞。
一路一直忍著奪眶的淚水,穿過記憶,開門入屋,狹窄老屋客廳燈竟不亮。我想起童年市集母親頂上的那幾盞隨風搖曳的燈泡,還是母親厲害,她收拾好東西,利索地爬上凳子,一一熄滅燈火,然後我們母女就在黑暗中行路,聽得塑膠袋摩挲著腿,暗中辨物,那聲音成了母親在身旁的安全感。現在沒有母親也沒有他,我練習自己換燈泡,從一樓取出公用梯子,取出抽屜裡的備用燈泡。緩緩爬上頂端時,仰看著天花板,老公寓剝落的油漆裡躲著臉,我轉著轉著燈泡,不禁潸然淚下。
走到廚房,母親用過的瓶瓶罐罐,平底深鍋,切肉的刀切蔬果的刀與切麵包的刀如武林並列,後來他比我還經常用到,他是美食家。但此刻這些廚房用具彷彿不想看我似的全都鐵著臉的安靜,我是最少用廚具的人。廚具最熟悉的是母親與他,看到我像是看到很面生的情傷中人。我燒水,煮了碗阿舍客家粄條,看著水滾著,瞬間一股悲哀也翻滾著,從現在起,我要開始煮東西給自己吃了。無論我走到哪裡,都會有母親和他在廚房為我領路,讓我知道怎麼煮食。我得燦爛地笑著才行,至少裝出愛吃的樣子,即使內在彷彿已成一具白骨。
吃著粄條,愁眉深鎖,老想著何以真實事件朝小說的虛構情節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