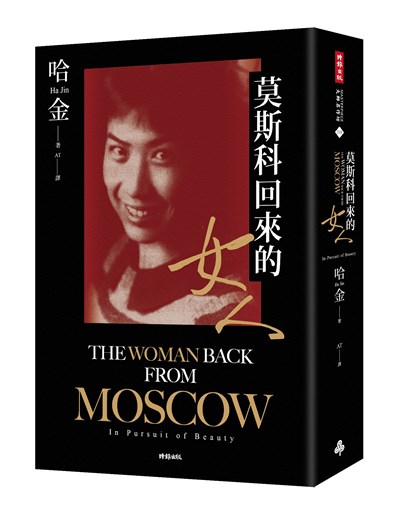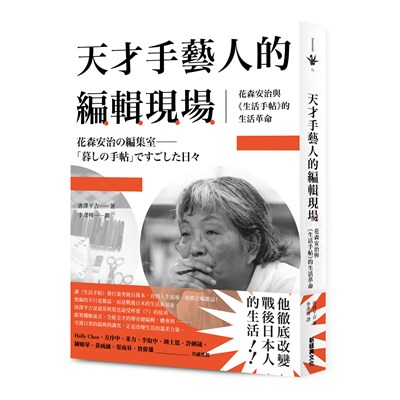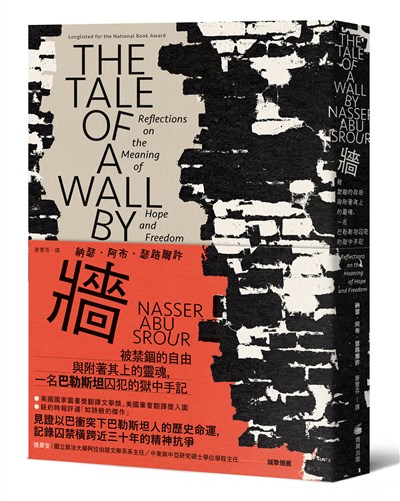六、七〇年代的臺灣,經歷流轉萬千的政權與社會動盪,這片土地籠罩緊繃氣氛,謝苦甘的下半生卻再次活躍了。某天,聖母安養院的修女與義工來訪,打開他塵封數載的話匣子。這位老先生的魅力和溫暖席捲安養院,讓義工們積極招攬他成為住客。但似乎有股力量牽絆著他,離不開這座美麗卻頹殘的山村。
然而,火災侵襲、身體不再強健、滿堂笑聲的餘韻……,動搖他的信仰與矛盾,最後如願搬進聖母安養院。沒想到的是,這個決定卻在他心中颳起一場風暴,喚回一頭深伏心林多年的三腳野豬。
內容節錄
《山爺》
一
經過二次大戰,隨著臺灣光復後的同時,日本人離臺,中國的軍隊和一些人員也陸續來臺,直到蔣介石帶著六十至八十萬軍隊,和跟著撒退的知識分子,還有大小官僚人員,到了臺灣執政的一連串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經濟等等的變遷;這對在臺灣土生土長的某個年代的人而言,真叫他們感到眼花瞭亂不打緊,連腦筋一時都轉不過來。居住在近山山村的謝苦甘就是這麼樣的一個人。
一九四九年臺灣進入戒嚴白色恐怖,令整個臺灣社會僵化,人民的生活空氣緊繃,到了六十年代,這種嚴峻氛圍,連山區的地方也罩著。
有一天下午,三月的春雨連綿,鄉公所的人員帶來一些人;他們有穿制服的警察,和幾個眼不看人,只板著臉東瞧西看,眼睛銳利地想穿鑿牆壁似的,當警察在詢問謝苦甘的同時,那些便衣人分頭,有的走進屋子裡偏廂或後頭,有的走出外頭,繞著屋外早前的豬圈或牛欄。
警察一邊翻閱公文夾,一邊問:
「謝苦甘,」他抬頭看了看對方的臉。謝苦甘有點難堪地回他笑臉。警察接著問,「你今年幾歲?」
他好像一下子被這麼一問,突然忘了自己的年紀,他笑了笑說:
「你問我幾歲?我、我、我快要死了,幾歲?」他笑起來,也想起來了,「連閏年也算,臺灣歲七十四歲了。」
「現在都在做什麼?」
「現在喔、」他被這種突如其來的問題,被問得傻愣。為舒緩自己自然地回笑說,「現在喔,呷飽閒閒等死啦,嘿嘿……」。
「我現在是在辦公事,不是在和你開玩笑。」警察雖然嚴肅,旁邊的人都笑起來;這使謝苦甘放鬆了不少,「我跟你講真,哪敢和警察先生講假的?又不是討雷公打死。你沒看到?我們整個山村二十七個竹圍仔戶,老的死了死,少年的……」他無視警察跟鄉公所來的人,低聲說話。苦甘反而較為嚴肅而順暢地說下去,「我們這裡五、六年前,你們官廳講,說我們住的,還有外口的山坡地,攏是國有地,又講什麼居家的地上物,不但不得再蓋,連修補攏通通不可!……」。謝苦甘由前面開始有一點語無倫次的暖身,現在終於從滿肚子的牢騷中,抽出一端緒頭;那要說的可能從早前,直到現在村子幾乎沒人,年輕的放下山村裡的耕地生活與工作,都跑到都市出賣廉價的勞力。竹圍裡的葺頂住屋,經過幾次的大颱風,差不多都不堪居住;就算可以居住,也沒人了。
當鄉公所的人,向警察說明問題,警察頻頻點頭之後,從公文夾的另一內夾,抽出幾張橫豎四六比的黑白照片。
警察抬起頭,向謝苦甘打了岔說:「我再問你,你一定要老實講,現在要問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問題。」說著抽出一張人頭像,「這個人你認識嗎?」
「這——個——人——??」
「對!這個人你認嗎?仔細看。」
其實話很簡單,就像是非題是與不是,苦甘卻又把它當著話題。「哎呀!我們住在山裡的人,能記住自己的庄頭的人已經算不壞了。外面的人,我伸出雙手的十支指頭仔來算也還有剩咧!我……」他的話又被打斷了。
「不認識喔。」警察瞪他一眼。
「我不是剛剛講過了嗎?我講我伸出雙手的……」話又被截止。本來覺得無奈有點慍怒的警察,差一點就笑起來。他再向苦甘確認:
「你真的不認識喔!」
謝苦甘這次沒開口,他冷冷地緩緩搖搖頭。
「好!那麼這個人呢?仔細看看再說。」警察又抽出另一張照片問。苦甘伸手過去把照片拿過來端詳一下,似乎受到輕微無形的撞擊,他把手上的照片稍拿遠一點再看。「認識是不是!」警察抽回照片,提高一點聲調問。
「無啦!我是看到照片這個人的臉,有一點像我們庄頭裡的福生,害我驚一下。」
「那現在他人呢?」
「人?早幾年前就作古了?」
「做什麼鼓?在哪裡?」警察太年輕了,有很多老人的話都聽不懂,笑話也會拿來認真。這時候在屋內裡搜尋的一個便衣人員,把一綑塵封已久的標槍,就在廳頭他們審問的身邊空地,碰一聲將它拋在地上,除了灰塵像水蒸氣往上飄浮,有幾隻蜘蛛和小蟲子跑了出來。所有的人都往地上看了看,然後再把目光集注在那位便衣。便衣為安撫大家的不安,終於以笑臉說:「沒事,等問完了再說。」
「哦!那些標槍喔,那是我們以前打山豬時用的,……」
「沒要緊,等我把話問完再來講。」
謝苦甘一看到地上那一綑標槍,他很高興,他覺得不但有話可說,他相信客人會聽到耳朵豎起來。
警察繼續一張一張問,謝苦甘真的都不認識他們。這時,在外頭巡迴查尋的兩個便衣人員也回來了。謝老看到後來的人沒凳子坐,他站起來彎腰要鑽進神明公媽桌底下,把蒙塵已久的長板凳椅條拖出來時,便衣人員謝了他,並表示沒事的話,他們很快就要走了。「真歹勢啦,你們要來也沒先通知,害我連茶水攏無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