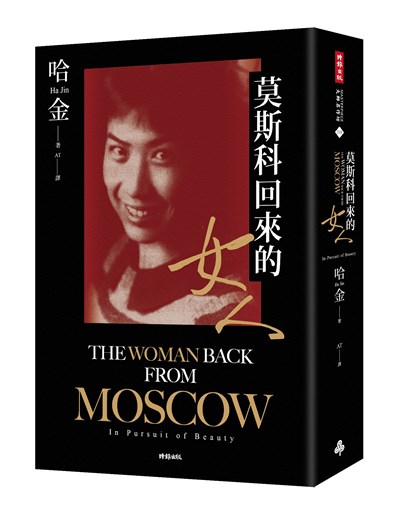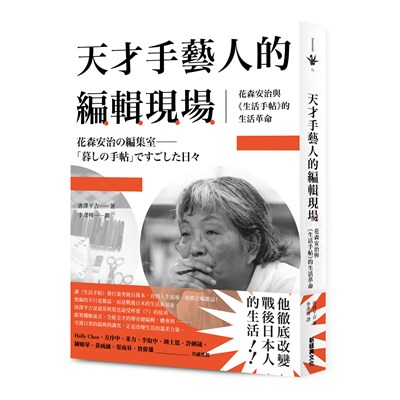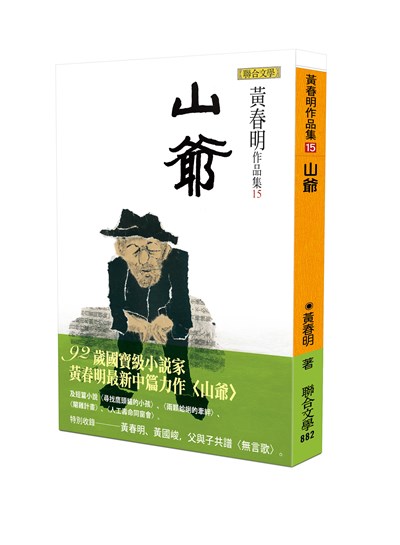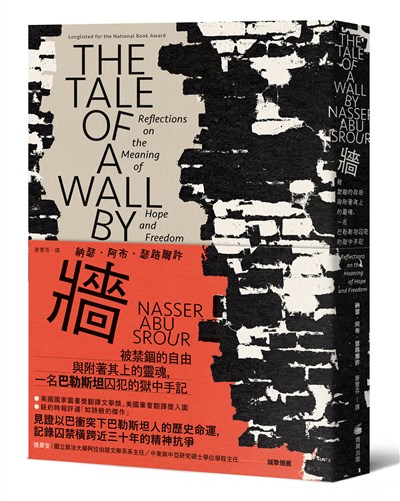駱以軍全新小說《六個抬棺人》,是他回望自我、召喚記憶與幻象交錯書寫的深層之作。書中以熾熱語言探問「故事是什麼」?以父喪為引,一具棺木由六位風格迥異的人物抬起,他們不只是虛構角色,更是作者人生不同時期的投影。故事穿梭現實與虛構、生命與死亡,如星際站般多維重構,顛覆敘事疆界。這不只是說故事的書,更是一場與失落搏鬥、以文字對抗遺忘的文學行動。房慧真、胡淑雯、連明偉、陳雪、陳栢青、童偉格齊聲推薦——
「駱以軍式浩瀚小說的起點,多維宇宙的心靈星圖。」
內容節錄
《六個抬棺人》
當故事中的主角,站到我的面前
有一次──就是無數次的其中一次──我在台中一個圖書館,像按下腦後一只播放錄音帶的按鈕,講了兩個小時,從沒有意外,人們會在我說到盧子玉的笑話時,我把他家馬桶拉爆時,整個觀眾席瘋狂的大笑,真的,我還去司法大廈對一演講廳的法官講過,去佛光山的一個超大的空間,下面應有上千個師兄師姐,開始時還集體莊嚴向我問訊,但講到盧子玉家馬桶爆炸,連第一排的住持師父都笑得痙攣;我去過一個五星飯店頂樓一間大會議室,跟一些什麼董事長夫人,穿著全是名牌,盛裝打扮的貴婦們講過;我也曾在那些高雄女中、竹中、竹女,甚至台大醫學院,那些超腦天才的週會,甚至是體育館裡數千個學生講過這《六個抬棺人》,沒有例外,絕對讓全場像投下一顆原子彈,會開起一朵蕈狀雲,我有時會有一種「這是在開演唱會嗎」的幻覺。因為它的表演效果,得到全場浪濤般的騷動、歡笑、掌聲,太讓我飄飄然了。當然我無例外的,都是在講完「第二個抬棺人──W的故事」,那演講限制的二小時就到點了,年輕學生會一改開始時散漫坐在各位子上滑手機、講話、冷淡的氣氛,變成超熱情、遺憾,希望我能接著講「第三個抬棺人」、「第四個抬棺人」、「第五個抬棺人」、「第六個抬棺人」的故事,而不是一個「說不完的故事」。
當然我還有其他四、五個不同版本的,應付這種二小時正式演講的「故事群結構檔」,但都沒有這「六個抬棺人」是必殺技。
據說後來有人稱我為「被小說耽誤的天才相聲演員」。也偶有一些死心眼的孩子,會來追問我:「結果後來您父親的葬禮,真了找了盧子玉、W、和其他四個鐵哥們,還幫你爸抬棺材嗎?」
其實我的演講收尾通常會說:「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只能說第一個抬棺人的故事、第二抬棺人的故事。但即使我真的有時間跟各位說完,第三個抬棺人、第四個抬棺人、第五個抬棺人、第六個抬棺人,他們的故事,我想是一樣的意思。圖窮匕見。作為當代的我們,說故事已經成為不可能的一件事,你們想,即使我把我父親的屍體,死亡時刻,搬到舞台的前景展示,我也無能說出他這一生經歷的,他內心祕密的歡愉,或痛苦。但也許我找到一種方式:找到六個抬棺人,他們幫我扛著父親的棺材,顛倒夢幻、搖頭晃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把那將一切故事吞食進去的黑洞,突圍衝出,運送到各位的面前。而事實上,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都是和我發生重疊的,不同時期的『我的年代的故事』。」
總會有一些人在演講結束後,到台前來要求簽書,或簽在小筆記本上,或拿手機合照,這都是年輕的孩子,或有一些媽媽帶著高中生的女兒,看得出那母親年輕時是文藝美少女,也有一些主辦方的主管、老師,會來致意,他們通常其中較年輕的一位,待會會開車送我去高鐵站,他們的眼睛其實還殘餘著被剛剛的故事灼燒過的殘燄,但或因拘謹或非純文學的讀者,所以很常攀談的是「如今我國的文學教育之困境」。也會有我年輕時,在大學兼課教過小說創作的學生,當然也都過了中年而經歷滄桑,提著一袋當地特產,「來跟老師打個招呼」,諸如此類。
我通常走出那演講廳、大樓、校園,在搭上載我離開的車之前,會站在馬路邊抽兩根菸,像是「事後菸」,讓兩小時賁張的腎上腺素,慢慢退潮。一種在這浮生中,這樣重複的,與創作並沒有關係,但確是十幾年來養家糊口很重要的一筆收入(說實話也很微薄),那種疲倦和孤單。
但那次,我以為我像之前數不清的許多次,從故事脫離出來,站在一個近乎日本禪僧在枯山水之前(其實是車陣喧囂的馬路邊),全然空寂的狀況,吞吐著菸,但這時有個中年男人走到我面前,那個笑臉似乎是舊識,我本能的擺出「啊怎麼你也來了」,無害的笑,他也掏出菸來點上,說:「你還沒認出我啊?」
是W。
如果我的大腦中有一組「人臉辨識系統」,那也是經過了相當繁瑣、跳躍不同對比階梯或樓層,才一層一層揭開眼前這張「被歲月浸泡的臉」,和記憶中年輕時的W秀氣的臉,那之間造成極大差異的多層膜。可能只剩那笑容,某些流動的波紋,而那個從極遠端,不斷細瑣換算,一路踩著記憶枯葉,恐怕也只有在我腦中,才祕密成立啊,「啊,你怎麼會跑來聽?」我說。
「嘿嘿,想不到吧?」
確實已變成一發胖、平庸的型態。穿著米黃 POLO 衫、黑西裝褲,剃平頭,但已灰白髮。其實這些年偶遇不同時期的老友,彼此都嘿然各自藏不住眼中所見那變形老態的訝異。雖然不像女人,皮膚、眼珠、脖子肉摺、肩背隆起、頭髮變粗變黯、腰弧消失、身形往圓柱、墩體發展的恐怖魔術;但男子舊識的老境重逢,真的像騎了二、三十年的老機車啊,別說一眼可見的支架、龍骨、機械細部的老舊過氣,要散架卻勉力撐鎖著的張力;主要是鼻子可聞見那周身洩出的機油,不再是年輕時鮮烈清澄之油,而是一般污濁、含雜質、發酸的油蒿味。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是才在我剛剛結束的演講,最後的故事中主角,現在站在我面前。他媽的他竟跑來聽我演講!早知道「第二個抬棺人」的故事,我就抽換成「第三個抬棺人」來講啊。
我生命中當然有太多這樣的經驗,對那些被我扭曲編織進小說裡的,傷心、驚駭、憤怒、羞辱的人們解釋:那寫的不是你啊。那只是我腦額葉開了個洞,一道黑光穿過,召喚那些地獄亡靈,人心裡最卑微痛苦的激流,它已經脫離了取材時的你,和寫小說的這個我,一起獻祭給那野牛群狂奔過峽谷,那個故事超出我力量的衝力啊。